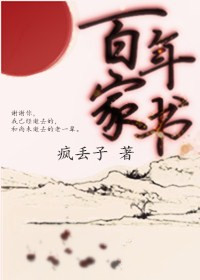百年记忆:中国百年历史的民间读本-第14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的小说,炒作得很凶,读过之后,感觉平平,我会狂妄地以为,写同类体裁,我可能写得更好。但也有时候,我读过一篇作品,心悦诚服,由我来写这部小说,肯定不会写得如此精彩。
1955年反胡风运动株连到我,这绝不标志我卷进了文学事业,1955年之前,我远没有进入文学,即使我已经发表过几篇小说,也发表了几首诗,只能算是习作,读者没有印象,我自己也羞于提及。
荒唐的政治运动总是制造荒唐的结局,1955年反胡风运动,把我株连到一桩与我无关的政治事件之中,这桩事件改变了我的生活轨迹,改变了我的命运,逼我走上了一条不归路。本来是不具备思考历史与时代的素质,这场政治运动逼我去认识时代、认识历史。本来我是一个狂热青年,我对领袖和学说无限信赖,这场运动让我看到了光明下的阴暗,看到了辉煌下的雾霭,经历了这一场长达25年的灾难,被摧残的是我,而被断送的,却是我理想中的一切。
第二部分八、人生不归路(1)
1955年的夏天,中国文坛一片肃杀之声。
关于《红楼梦》的讨论,引伸如何对待小人物革命新生力量,发展到对“贵族老爷”们的批评;胡风在一个座谈会上的即席发言,发展到30万言上书中央,直到“五把刀子”论,突然间公布了一批胡风的私人信件,学术讨论、思想批判膨胀为政治斗争,一时之间,一场以讨伐胡风文艺思想、清查七月派诗人、作家为突破口的政治运动铺天盖地而来,突然改变了许多人的生活道路。
此时,为了继续读书,我离开开滦煤矿回到天津,正在复习功课准备报考大学,外面关于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文章,我虽然每篇必读,但绝对没有想过这会导致一场怎样的灾难。我更不会想到这场批判最后会株连到我,使我从此陷入囹囫,几乎断送了一生。
1955年5月底,《人民日报》公布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这份材料的《按语》,以可怕的词语规定了这场斗争的规模、档次和斗争形式。《按语》中把胡风等人说成是一批叛徒、特务、国民党的残渣余孽和对共产党怀有刻骨仇恨的人。读到这份材料,我觉得事情严重了,对于将是一种怎样的遭遇等待胡风和他的朋友,我已经有些理喻了。
“胡风反革命集团”成员中有我的师长阿垅先生,我自然极是关心他的境遇。我是在《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第二批材料》公布的当天晚上,去新疆路天津文联宿舍看望阿垅先生的。说老实话,到此时,我虽然不懂得什么政治,但我也多少感到这场事件的不同一般了,直到此时,我还认为这场斗争与我无关。
我去新疆路文联宿舍看望阿垅先生,我觉得他此时最需要人们的关怀,也最需要信任。这些年来,阿垅先生对我的培养和引导,使我对他怀着极大的尊敬,我已经成了他在天津的一个小朋友,我想我去看望他,会给他带去一点点温暖。
这时的阿垅,已经早被点名批判了,《天津日报》早就发过天津文艺界揭发批判阿垅文艺思想的消息和文章,许多文章已经把阿垅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分子”,那些充满火药味的文章,早就把阿垅描绘成了一个疯狂反对共产党的社会公敌,甚至已经有人在报上联名发表呼吁,要求专政机关对阿垅逮捕法办、予以严惩。
阿垅先生的房间,多年来一直十分整洁,他一个人带着小陈沛生活,没有保姆,生活料理得极有条理,他的书橱非常整齐,房间里也是窗明几净,一尘不染。那时候没有暖气,冬天要点炉子,我记得阿垅先生续煤的时候,单独有一副手套,每次续煤之后,他都要出去洗手,可见他有着十分良好的生活习惯。今天到阿垅先生家来,觉得他房间里有些凌乱,他正在检查自己收存的信件、检查笔记,也可能是烧了一些,这或者就是后来揭发的那样,算是销毁罪证了。
对于我的突然来访,阿垅先生表现得十分惊讶,我看他的容貌,已是憔悴了许多,本来阿垅先生就已经是苍苍白发了,今天显得更是苍老。看到我,他还是笑了,声音也很爽朗,还没有大祸临头的感觉。我自然劝他不要过于担心,事情总会有个水落石出的时候,我对阿垅先生说,至少我不认为胡风先生是反革命。
阿垅先生那天的笑容,我至今记忆犹新,这可能是阿垅先生最后一次和外人接触,也是他最后一次自由的笑容了。我记得那笑容中似是没有多少苦涩,反而倒有一种终于逃脱不出劫难的安详。当然,他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几天之后,他就会被逮捕,至少在他那天的笑容里,我没有看出绝望。
谈话间,阿垅先生先询问了我考学的情况,劝我还是进大学读书完成高等教育为好;十几岁的孩子不要急于写作,尤其不要对理论问题过于热衷。我十分感激他的劝告,告诉他说我最近刚刚发表了一篇小说,若不形势紧张,我会带来给他看的。随之,我们说到了当前的这场运动,我不了解背景,只劝他要相信党,相信人民,相信正确和谬误总有澄清的一天。对于我的劝慰,他连连点头,既不为自己申辩,也不怨恨什么人,他只是感叹地对我说:“运动过去之后,我想集中精力搞创作,写些诗,写些小说,理论问题不好办。”
我知道,这个时候不应该再在他家里耽误他的时间,没有再说什么,我便告辞出来了,临别时,我还劝他保重身体,不必过于紧张,一切都会过去的。阿垅先生没有多说话,他只是紧紧地握着我的手,一双眼睛默默地望着我。我想,也许他有了一些什么预感,他也许知道无论什么人,他已是多凝望一些时间、多留下一些印象,便多沉积下一些记忆了。
无论如何我也不会想到这是我对阿垅先生最后的一次拜会。我当时想,不管形势发生什么变化,如果还有一个人不肯背离阿垅先生的话,这个人应该是我。因为阿垅先生喜欢我,他发现了我生命中的文学细胞,他从众多的来稿中发现了我的诗,由此才和我建立了师生关系,几年来他一直关心我,辅导我的文学习作。
即使我与阿垅先生的关系再亲近,即使这一场运动再残酷,按照正常的逻辑,反胡风运动也不应该株连到我的身上,这正如日后大家聚首时,绿原、牛汉、曾卓、冀汸、罗洛、罗飞等先辈师友所感叹的那样,“这场运动如何会牵连到你的头上呢?”
然而,终于还是牵连到我头上来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第三批材料公布后的第三天,我还和平时一样在家里复习功课,一位在天津的记者朋友半夜来到我家,万分紧张地拉起我就走,我问他何以如此惊慌,他当即就责骂我说:“你还蒙在鼓里了呢,我们报社刚刚传达了一个通知,说有一个叫侯红鹅的胡风分子潜伏在天津,各单位寻找没有找到,而且上边的传达说,估计这个侯红鹅是一个文化人,潜伏得很深,要各单位紧急动员起来,提供线索,一定要找到这个侯红鹅。”
这一下,把我吓坏了,我万万没有想到,就在我在家里读书的时候,全中国都已经动员起来寻找我了。而且据说还是下的全国通电,无论我潜藏在什么地方,也一定不能让我漏网。谢天谢地,幸亏我有个朋友在报社做记者,他听到了这个传达,如果不是他找到了我,再到最后我终于没能逃出法网的时候,那时候就要用手铐把我铐走了。
“去哪里?”我惊恐万分地向这位记者朋友问着。
“市委。”我的朋友回答着说。随之,我的这位朋友又向我说着,“我已经对报社说了,这个侯红鹅我认识,现在我就去把他带到市委去,到了市委,他自己坦白交代。”
“我坦白什么呢?”我还是不解地问着。
“到了市委再说吧。”就这样,我的这位朋友带着我匆匆地到市委去了。
天津市委机关,就是原来的开滦大楼,解放前我没有进过这幢大楼,解放后,以我一个中学生的身份,我也没有什么事情要到市委机关来,今天被人带进这幢大楼,我心里真是有点恐怖感。我也不知道我的这位朋友给警卫看了一个什么证件,没有登记,我们就往楼上走去了。走进文艺处,我的朋友向一位干部说了一些什么话,这时一位面容极和善的干部向我走了过来。
此时已经是入夜10点多钟了,接待我的,是当时文艺处的王处长。这位王处长的名字我听说过,他在解放区写过一个极好的剧本,我也看过这出戏的演出,印象极深。王处长人很和善,消除了我的紧张情绪,他没有对我板面孔,带着一种十足的文人气质。他看看我,笑了,笑得有点莫名其妙。也许他是笑我完全是一个孩子,也许是笑好不容易找到的这个潜伏极深的人,竟然只有19岁,好象是有点不带劲的样子。
第二部分八、人生不归路(2)
问过我的一些情况,话题就转到日前的这一场斗争上来了,王处长询问我和阿垅的认识过程,更询问了我和阿垅这些年的关系,然后他才对我说道:“你来得正好,我们正在找你。你不要害怕,只要你把情况说清楚就是了。你先回家把阿垅这些年写给你的信找出来,再把你和阿垅的关系写一份材料,尽快送到市委来,自己先在家里好好学习《人民日报》发表的文件,要和‘胡风反革命集团’划清界限,要认识到他们是一个反革命集团。”
还是我的记者朋友阅历深,他待王处长说过话过,抢在我前面向王处长说道:“是他自己主动要我带他到宣传部来的。”言外之意自然是表示对我要按投案自首对待了。
王处长笑了笑,仍然和善地对我说:“回家去吧,材料找齐了尽快送到市委来,把你的地址留下,有事我们好找你。”最后,王处长送我走出了他的办公室,在分手的时候,他似是无意地告诉我说:“昨天晚上阿垅已经被捕了。”
我被这个消息吓呆了。就算是胡风一些人有“错误”,就算他们的理论和马列主义“针锋相对”,可是总也不至于下大牢呀!这时,我才感到这件事太可怕了。这突发的事件,似是一枚重型炸弹将我炸得粉身碎骨。从市委大楼走出来,我变成一个呆子,大脑一片空白,眼前发生的一切我简直无法理解,而且一切也不需要我的理解,它只要我屈从。阿垅已经被捕了,“运动”才刚刚开始,如果一旦运动再有什么发展,等待我的又何尝不是铁窗和镣铐?我麻木了,麻木得顾不得恐惧,我觉得天都要塌下来了。
我不记得我的记者朋友是几时和我分手的,当我一个人走在回家路上时,心里空空荡荡,我总听见背后有人喊我的名字,只要耳际一响起这种喊声,我立即就打一个冷战,匆匆地回过头去张望,看到的只是匆匆的行人和陌生的面孔。
我只有19岁,这时候我正在准备高校的入学考试,而且我还是一个共青团员,共青团是共产党的后备军,我是把自己当做革命接班人看待的。无论我读书、工作,还有学习写作,我都以为自己是在从事神圣的革命事业,我总以为我是这个世界的主人,我为我们党,为我们社会的每一点成就感到欢欣鼓舞,我对落后、愚昧万分气愤,对于反革命分子,我更把他们视做是自己不共戴天的仇敌。我相信自己是新世界的创造者,我相信自己是旧世界的掘墓人,我认为自己是革命的一部份,我早就将自己的一切交给了革命、交给了党。
然而突然间发生了不可思议的变化,我一夜之间几乎成了一个在逃犯,而且我的老师已经下狱,我已经是大祸临头了。
我实在不理解他们何以把我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名重要成员,我根本就没有见过胡风先生,尽管我对胡风先生的理论很崇拜,我读过许多胡风先生的著作,我视阿垅先生是自己的老师;但是《人民日报》不是说胡风等人是一个“小集团”吗?我只认识这个“小集团”里的一个人,难道也算是这个“小集团”里的成员了吗?
直到最后天津市委下达了“对于胡风分子侯红鹅的处理决定”的红头文件,将我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成员的时候,我也是没有闹明白,我是为什么被打成“胡风分子”的。
就是这样,一场劫难终于落到了我的头上。
直到1980年,“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得到彻底平反,我才知道了一点我被打成“胡风分子”的原因,这还是罗洛先生告诉我的。
罗洛先生对我说,因为阿垅对我的过于欣赏,他曾在写给胡风先生的一封信中提到天津有一个叫侯红鹅的少年,很刻苦,读了些书,诗也写得还可以,对一些问题也有自己的看法,很可能有点希望。胡风先生有保存朋友来信的习惯,不料第三批材料公布之后,胡风先生被捕,公安部从胡风先生家里抄出了阿垅先生的信,对于信中提到的每一个人,公安部都要查出下落,这时几乎所有的“胡风分子”都已经“落网”了,只有一个侯红鹅还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于是连夜下通电,一定要找到这个隐藏极深的“胡风分子”,也算是“归案”吧,这样,从一开始,我就被“定”为是“胡风分子”了。
侯红鹅找到了,事情远没有结束。有人要在我身上制造一个大事件,以轰动全国。一个青年,读了胡风的书,受了胡风文艺思想的影响,学着七月派的风格写诗,按照胡风的文艺理论写文章,这不正是由受胡风思想影响到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卖命的典型吗?于是事件扩大化了、升格了,我已经被编织到一个怪圈里去了。
过了几天,我忙将有关材料送到了宣传部,这次王处长向我介绍了鲍昌同志,此时鲍昌同志已经借调到宣传部,专门负责搞这场运动,鲍昌说话很原则,并嘱咐我一定要提高认识,才能和“胡风反革命集团”划清界限。
第三次到市委宣传部去,王处长说方纪部长要见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