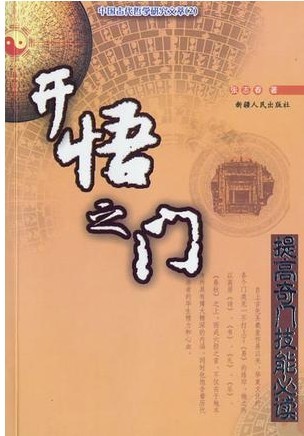暗穴(又名萤之痛) 作者:鬼古女 完结-第10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山下雅广又用日语说:“诸位同学、学长,何小姐有迫不得已的难处,并没有存心欺诈的意思,你们这么多堂堂丈夫,这样群殴一个女孩子,怎么也说不过去呀!”
果然,黑木胜脸色如铁:“山下君,你是我的好朋友,但你不能无视我的决定和我们群体的感受。你再多说一句,和她一样受苦。”
山下雅广胸口一阵憋闷,叫道:“这样也好……”刚一开口,就被一位柔道高明的男生重重地摔在地上。山下雅广心想:我没用,救不了她。
“啊”地一声惨叫,扳在何玲子右肩头的一只手被她低头狠狠咬了一口,何玲子挣脱开了那胳膊,从和服下抽出了一柄雪亮的短剑,很快抵住了左侧拽着她的学生的喉头。
“早料到要有这一天!好在我也不是第一次受这样的礼遇。”何玲子一字一字说着,“从现在起,你们的学长不再是黑木胜,而是我。”
黑木胜沉声道:“原来谣言是对的,你妈妈的确杀过人。”
“你有异议?”何玲子盯着黑木胜。黑木胜看一眼喉头顶着剑尖而龇牙咧嘴的属下,摇了摇头。“请你,黑木君,搀扶起山下君,向他道歉。”
黑木胜依言做了。
“你们都不准动……在我放了他之前,如果有人跑动,我一定会杀他。”何玲子推着那被制的学生,开始前行。山下雅广跟了上去。
走出了很远,健身馆后面没有一个人追出来。何玲子放开了人质,拔足飞奔。山下雅广快步追上,竟觉有些力不从心。
“玲子,原谅我没能……”
何玲子止步,蓦然转身:“山下君,你只给过我欢乐和友爱,有什么需要原谅?”
“玲子,我只希望……”
“希望总是有的,我只是很想知道,你需要多久把我忘记?”
“永远。”
“你不要跟着我了,明天见到我的时候,也要假装不认识……不管什么时候见到我,都要假装不认识。”
“难道那竟然就是两人的最后一面?”关键揉着发涨的太阳穴,起身踱步。安崎佐智子仍盯着那本山下雅广的诗集,抬头说:“当然是这样,你看那短短的几个月里,山下雅广有多少写给玲子或玉子的诗,我们才会对这段纯而又纯的初恋感受得如此生动。可在那首《无别离之离别》后,再没有提何玲子的只字片语。而且,她一旦被识出身份,就有很大可能牵连到她逃亡的母亲,她又怎么可能继续回来上学?”
“有道理,但如果何玲子再没有在山下雅广的生活中出现过,山下雅广又怎么会在七十年后,仍思念如此之深?两人当年毕竟只有十五岁,情窦初开而已,山下雅广后来又有了家小,怎么会极端到买下两个墓穴,和玲子共眠地下?”
安崎佐智子点点头,再次翻动那本诗词全集。翻到一半,叫了声“奇怪”,说:“这本诗集是按照时间顺序列出山下雅广所有诗作,他是位很多产的诗人,每年至少都有数篇诗作,偏偏一九三五年只有一篇,三六年和三七年则一首诗都没有。”
“也许恰好那阵他心情不好,没有创作热情?”
“诗人越心情不好的时候,越要用诗句倾诉。”
“你有什么假设?”
“是不是那个阶段的诗,被山下雅广‘藏’起来了,没有公开。”
关键在沉默中揉着太阳穴。安崎佐智子在沉默中,又翻了一下诗集,忽然紧紧盯着书,入了定一般。关键走上前,安崎佐智子抬起头,盯着他的双眼。
关键低下头去看那诗集,突然浑身一颤。一张图书馆免费可取的空白资料卡片,正嵌在1935年和1938年的诗页之间。卡片上没有字,只有一个大大的问号。“诗诗?!”
安崎佐智子让关键静坐了好一阵,才说:“也许,黄小姐……诗诗,也有我们同样的发现,和疑问。”
关键说:“如果这问号真是诗诗留下的,那么她有可能也已经知道了何玲子的存在。我真够傻,她当然知道了!”关键一拍脑袋,那对萤火虫耳丁下的产品标签上,一串数字,正是759632,何玲子的墓号!“她多半已走到和我们相似的进程。但接下来会怎么做……我没思路了。”
安崎佐智子又说:“山下雅广的夫人二十年前去世,是土生土长的日本人,据山下雄治博士说,他们的感情挺好的……”
“再次说明山下雅广对何玲子的强烈思念和感情,绝不可能仅仅建立在中学里那半年的接触……”
两人忽然几乎同时说了声:“啊!”
“一九三五年到一九三七年,山下雅广大致是十八岁到二十岁。”关键略有些激动地说,“假如何玲子在山下雅广步入青年时出现,两人之间的情感就会演变为热恋。”
“热烈到山下雅广要和她葬在一起……”
“墓里葬的真是她吗?何玲子的墓里没有骨灰盒?会不会有些不想公开的……”
安崎佐智子站了起来:“天哪,的认为山下雅广会将一些材料埋在何玲子的墓下?”
“也许被埋的,才是一段真正的爱情,一段很私人的爱情……诗诗将何玲子的墓穴号和萤火虫耳丁放在一起,是不是也在暗示,何玲子的墓下有线索?”
“不要,不要,我知道你在想什么……”安崎佐智子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一步。
月光照在并排的两座墓碑上,灰淡惨白。关键站在墓碑前,连打了几个冷战。他感觉冥冥之中,似乎有双眼睛注视着他,注视着他将要做的疯狂举动。
何玲子,无论你是谁,你有什么样的身世,请你原谅我的鲁莽。
他从包里取出一把短柄的铁锨,正准备破土,忽听安崎佐智子说:“等等!”
“我已经祷告过,请何女士原谅了。”
“不是阻拦你,是想让你看看,这墓前的花草,有没有些不同?”
关键仔细看了看,“哦”了一声:“真是的,何玲子墓前的花草,有些歪斜不齐。”
“墓园的园艺工,种这样的小花草,一定不会歪七扭八,很可能这些花草被人翻动过,又重新种上,因为不专业,所以会显得参差。”
“你是说,诗诗说不定也和我们有了同样的想法,也来……。”
安崎佐智子柔声说:“是啊,诗诗是个聪明的女孩子……”
关键点点头,不再说一句话,小心翼翼地将那些花草挖了起来。土不断地被挖起,坑越挖越深,越挖越大,直到铁锨忽然遭遇到阻力。
一个封着的皮袋。打开后,里面是和笔记本电脑大小相当的金属盒子,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盒面是浅浅的镌刻,似乎是山水。安崎佐智子轻轻“啊”了一声,说:“远山、古寺,这是典型的奈良山水。我怎么感觉,这盒子是纯金做的。”
说话间,关键已经打开了盒盖。
首先入眼的,是一只小小精致的玻璃罐。边上是一叠折得整整齐齐的微黄的宣纸。关键忍不住打开最上面的一笺,闪在电筒光下的又是一首词名《苏幕遮·萤之痛》。
苏幕遮·萤之痛
并枝莲,双宿燕,三载同心、心有千重眷。欲度朝夕拥帐暖,共画蛾眉、绘了平生愿。
怨琴殇,愁笔断,咫尺天涯、何处萤萤散。月映孤窗云过眼,梅子落时、烛泪痕零乱。
“这又是什么意思?”安崎佐智子问道。
关键半晌不语后,轻叹一声:“这恐怕不会是个快乐的故事。”
从第一天起,山下雅广就知道,东京永远不会成为自己的家。
成绩出类拔萃的他,对高等学校的选择几乎是无限的。可他,为什么选了东京帝国大学呢?东京和离奈良不远的京都,两所帝国大学都有日本国顶尖的医学院,不分轩轾。也许,他想证明自己这个“脆弱”的男孩其实也能坚强地适应漂泊的生活。
已经数月,他还是和东京格格不入,当那年东京的第一场雪飘下,他的心情沉入谷底。尤其冬至前的雪天,空中的阴云总是那么低那么厚,和工厂以及民用的煤烟融成灰蒙蒙一体,仿佛将整座城市吞没。
周末无聊,他走到了汤岛天满宫。这神社里的天神,保佑的是善男信女们的学业大成。也许是自己对东京迟缓的适应拖了学业的后腿,他在年级里的成绩勉强保持中游,这是他自小从未尝过的滋味,自尊心和自信心都在迅速地缩小。他拜过了天神,长叹一声,觉得自己可悲到了要靠祈求神灵帮忙学习的地步。他在神社院中那千姿百态的梅树前徘徊,心想,若是有梅花在雪中盛开,至少还有点鲜活的点缀。
“离梅花开还有两个月呢,看你痴呆呆的样子,就等不及了吗?”少女轻柔的声音。
山下雅广转过身,双眼几个月来头一次有了神采。千言万语,却凝在嘴边。
“你说,为什么要下雪呢,把东京不多的好处都掩盖了。”少女似问似答。
“同感,同感,那诸多本就呆板的建筑楼宇,如今在一片白色恐怖下,更显得无趣。”山下雅广的双腿在微微颤抖。
“最可怜的是旅人游子,错把异乡当故乡,只好在寒风中颤抖,心比手足更觉冷。”
“好在他乡遇故知,手足虽冻,心却澎湃,热到能化雪除冰。也只有此刻才发现,当初背井离乡,不在情理之中,现在看来,是来赴一个大概前世定的缘……”
“又是心血澎湃,又是奔赴前缘,哪像是个医学生的话,你更需要的是冷静,”少女忽然一笑,“我可以帮你!”
山下雅广一惊,眼前白光一闪,脸上一阵疼痛,一阵冰凉,一个雪团已经趴在了他的眼鼻之间。只不过这次,笑依旧挂在眼中,他可以看见,笑意也挂在何玲子的两腮。
“玲子!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山下雅广一把抱住了何玲子。
何玲子在他肩头靠了一阵,又低头说:“抱歉,当年不辞而别,实在有苦衷。”
山下雅广也意识到自己因忘情的鲁莽,点头致意:“你当时的境况,我了解。据说,你们走的那几天,奈良突然出现了大量兵士。”
“我不告而别,其实后来也受了惩罚的,一边希望你赶快忘了我,一边希望你永远不要忘了我,这感觉很不好受。”何玲子仰起脸,看着已经脱了稚气、更俊朗的山下雅广。
听了这话,山下雅广更是坚信,此番在东京没来由的受煎熬,真的都是命运安排。三年前那段纯纯的感情,原来就是真爱的萌芽。
何玲子说:“所以今天偶然遇见你,就不打算再和你擦肩而过。”
山下雅广看着出落得更清丽出尘的何玲子:“这次,我再不会让你从我身边离开。”
何玲子也笑道:“噢?真的由得了你吗?”忽然,一丝忧郁飘过她的双眼,她泱泱地说:“我也不知道,该不该告诉你,其实,你不该离我太近,你会受伤的。”
山下雅广一怔,随即温声道:“即便被你伤……我也喜欢你的短剑。”
何玲子莞尔一笑,虽在初冬,山下雅广的春天却翩然而至。
何玲子在东京文化学院修习西洋油画。山下雅广在繁重的医学院学习之余,终于有了一个他愿意留连之地。两人经常沿着校外的长街漫步,谈着童年和未来。何玲子幼年漂泊,颠沛于中日两地,见识很广,山下雅广则一直倾心于中国古典文化,两人间有无尽的话题。
当何玲子邀山下雅广和母亲渡边玲子会面的时候,山下雅广几乎可以听见自己的心跳。他知道这一步的意味。
渡边玲子跪坐在台前抚琴的样子,山下雅广一生难忘。那本身就是一件艺术品:长发如瀑,面容淡雅,玉箸般的手指在凝柔缓急间和琴弦殷殷对语,仪态和音乐融为一体。
虽然在山下雅广心目中,何玲子是世上最明艳的女子,但他还是惊诧于渡边玲子的容颜。已过中年,渡边玲子仍保持着一种让人不敢逼视的美。尤其她的双眼,纯净如水,亮如点漆,似乎还带着孩童的天真。虽然何玲子曾告诉过他,渡边玲子在当年海军大臣府里行刺后受伤,双眼再也无法视物。
寒暄过,渡边玲子静静地听山下雅广对她琴声的赞美,微笑说:“听玲子说你对各类艺术都有浓厚兴趣,如果你愿意,可以让玲子经常带你过来,我教你弹琴……”
山下雅广惊喜地看一眼何玲子,却见她眼带迷惑:“何夫人能赐教,幸何如之。”
“孺子是否可教,从学琴来说,主要是看一双手。能不能……让我看看你的手?”
山下雅广愣了一下,才明白渡边玲子所谓“看手”的意思,将双手伸了过去。渡边玲子掂起了山下雅广细长的双手,轻轻抚摸,直到摸得山下雅广有些不自然起来,她忽然用力一捏,山下雅广痛得轻轻叫出了声。
何玲子叫了声:“妈妈!”渡边玲子放开手,向他颔首:“山下君,请回吧。”
山下雅广顿时觉得仿佛失去了生存的空间,险些就要晕倒。
“妈妈!”何玲子厉声地叫着,显然也震惊地不知该说什么。
“山下君,你听不懂我的话吗?”渡边玲子却厉声喝问着山下雅广。
山下雅广拂袖而起,拉门而出。
“山下君!”何玲子追到门口,“你等等,好不好?”母女俩的争执声透过屏风和木门,传入山下雅广的耳中。
“我是为了你好,他会让你受苦。”渡边玲子的话音如同冷泉流过寒石。
“妈妈,您难道看不出来,他是我在芸芸众生里能找到的最善良的人……”
“善良,但柔弱,他的人,和他的手一样,骨力不够。你闯祸时,他救不了你。”
“我会对自己负责。难道,您当年遇到麻烦的时候,又有谁能救您?”
“放肆!”
笃笃的木屐声响过,何玲子出现在门口,挂了满脸的泪水。
“玲子,看到你和令堂这样争吵,我心里很不安宁。”山下雅广不知从何安慰。
何玲子静静地站了片刻,忽然冷冷地问:“那你要怎样?”



![(又!吴海英同人)[又!吴海英]爱我你怕了吗封面](http://www.baxi2.com/cover/22/22741.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