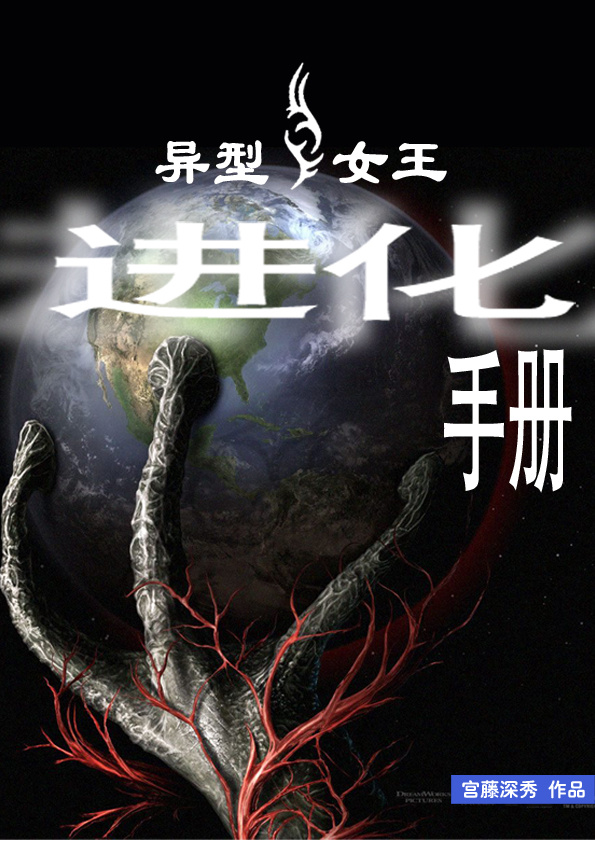五月女王-第25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陈队长收过了那一把钱,看了看,发现里面还有一张五十的,他就说:“快点收了!以后不准摆了!”
钟太婆连连说好,一边抖着手收摊子,袁青山帮她收着,岑仲伯看见那两个城管走了,就喊:“你们给老子回来,你们凭什么拿钱!”——黄元军狠狠扯了他一下,沉声说:“土狗!你娃不要发疯了!”
好不容易这团混乱安定下来,袁青山已经忘了妹妹的事情,她跟黄元军一起送岑仲伯婆孙回家。
岑仲伯家住在南门猪市坝里面,一进一出两间房,还有一个小院坝,伸出来的房檐下面缩着一个蜂窝煤灶台,屋子里面的东西都是很旧的了,发出一股陈味,岑仲伯的床在外面那间,上面乱七八糟丢了很多东西。他们把推车放在院坝里面,岑仲伯扶着钟太婆进去坐,又倒了一杯水给她。
钟太婆说:“狗娃儿,我给你说,这些人惹不起,你去惹他们干啥子嘛。”
“我知道了。”岑仲伯闷声说。
“你每次都说你知道了,你啥子时候才懂事哦。”钟太婆叹息。
老太太坐在那里,幽幽地叹着气,忽然落了眼泪下来,她说:“我怎么这么命苦哦,你爷爷死得就早,你妈生了你也走了,你爸更不像话,跟到那个女的说跑就跑了,这么多年没个音讯,你也是,这么大了,还不懂事,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
她嘤嘤得哭起来,缩在床边上,看起来像个孩子,她的眼睛已经变黄了,哭的时候,眼角全是眼屎。袁青山站在房间里面,心里面居然并不是非常惊讶,她早就隐隐约约想到的事情就被说出来了,她早就应该猜到了。她站在那里,看那个岑仲伯他们家的老房子上面那个高高的房梁。
岑仲伯手忙脚乱地从枕头下面抽了一张手纸给钟太婆擦眼泪,他说:“我知道了奶奶,你不要哭了,我错了,你不要哭了。”
他把老太太抱在怀里,拍着她的背,说:“我错了,奶奶,你不要哭了。”——袁青山发现,他露出了某种微妙而温柔的表情,这表情软化了他那张犯人一样丑陋而凶狠的脸。
袁青山看着他这样的脸,她忽然很想知道,岑仲伯的父亲是长了怎样的一张脸呢。
岑仲伯终于把他奶奶哄得睡下了,他带着黄元军和袁青山走到外面的那间屋子,他像被抽光了力气,刚刚像熊一样隆起的身体全萎缩了,他说:“今天谢谢你们了,你们走嘛,我要煮中午饭了。”
“你先去把眼睛看一下哦。”黄元军说。
袁青山这才看见岑仲伯眼睛旁边那块青的肿得很大了,她吓了一跳,说:“真的,肿好大了!”
“不看了,没啥看头。”岑仲伯说。
“你给老子爬!给老子去看了再说!”黄元军黑着脸把他拉出去了。
袁青山以为他们要去县医院,她就想到袁清江了,不知道她怎么样了。
谁知道他们没有走到南街上,反而顺着猪市坝那条巷子走到了里面,走了大概五十米,有一家小中药铺子,有一个老头坐在门口那石臼磨药。
“爷爷!”黄元军喊。
老头子一抬头,就说:“狗娃儿又打架了?”
“嗯。”岑仲伯哼了一声。
老头子站起来,把手在围裙上擦了擦,走进药店去了,一边走,一边说:“你过来你过来,我给你看一下,没啥子,不痛。”——他的语气像哄个小孩子。
岑仲伯说:“黄爷爷,我又不是小娃娃。”
“嘿!”黄爷爷说,“你还小得很!娃娃!”
他给岑仲伯处理伤口,黄元军和袁青山站着看,黄爷爷说:“军娃儿,你爸的药我配好了,等会拿回去给他喝。”
“嗯。”黄元军说。
黄爷爷又看见了袁青山,说:“你们同学啊?”
“嗯,”黄元军说,“都是我们北二仓库的,袁青山。”
“袁青山……”黄爷爷念着这个名字,“袁华的女哇?”
“嗯。”袁青山说,“你认得到我爸啊?”
“哎哟,”黄爷爷来来回回打量了袁青山和岑仲伯几眼,呢喃:“作孽啊!作孽啊!”——他一边说,一边动手,岑仲伯痛得哼了一声。
他们处理完了伤口,三个人一起往巷子门口走,岑仲伯说:“谢谢了,我先回去煮饭了。”
“回去嘛回去嘛,明天再出来耍。”黄元军摆摆手。
他们就要走了,岑仲伯忽然又叫:“袁青山。”
袁青山回过头去,看见他站在巷子门口,看着她,她知道他不知道说什么好,她就笑了笑,说:“没事。”
可能只有他们两个才知道,这两个字是在说什么,它们又是经历了多少千回百转,流离失所才终于被说了出来,而实际上,他们两个人没有人能够知道,是不是真的就没事了。
没有人知道。
平乐镇的人可能更习惯于心照不宣地活着,甚至在背后说别人的各种坏话。但是他们见面的时候,是什么也不会说的。
就剩下袁青山和黄元军两个人走回去,袁青山说:“你经常去岑仲伯那玩啊?”
“啊。”黄元军说,“他经常去我爷爷那嘛,后来就熟了,都是南门上的人嘛。”
他们走过整个南门,做为一个北街上长大的孩子,袁青山忽然觉得这一条街是那么神秘,那么充满了故事。
他们走到南门老城门口,黄元军说:“我先去找乔梦皎了,她爸妈今天走人户去了,这女子没人喊她吃饭就要自己饿死。”
他们告别了,袁青山看着黄元军的背影,实际上和她早上看见的那个是一样的。
她匆匆忙忙往西街走去了,她不知道袁清江怎么样了,她是不是回家了,但她还是想先去医院看看。
她跑过去,发现医院已经快下班了,她还是跑到肌注科去看了,袁清江根本不在那里,谢梨花正在脱护士服——袁青山正想走,她就看见了她。
“袁青山!”谢梨花说。
“谢阿姨。”袁青山只有走了进去。
“有事情啊?”谢梨花笑眯眯地说。
“啊。”袁青山应着,“你看到袁清江没?”
“袁清江?”谢梨花疑惑地说,“没有啊,她不舒服吗?来医院了?”
“没有,没有,”袁青山连忙否认,她说,“那我回去了。”
“哎,等等”谢梨花说,“跟我一起走嘛,不然我们一起吃饭嘛。”
“不了不了,袁清江可能回去了,我还要去煮饭。”袁青山猛然发现她说的话正是岑仲伯刚刚说过的。
“你好能干哦,还要煮饭。”谢梨花说,她穿好衣服了,拿着提包,和袁青山一起往医院门口走去。
“你小时候我就给你打过针,你记不得了吧?”谢梨花说。
“好像还记得。”袁青山说。
“你肯定不记得了,你还是个奶娃娃的时候,我就认识你!”谢梨花说,“你小时候好乖哦,我们整个医院的护士都好喜欢你!”
“那个时候你爸很帅,对你和你妈妈都很好,我都没想到我现在还能认识他。”谢梨花温柔地对袁青山讲着。
袁青山没有说话,谢梨花忽然意识到自己好像说错了话,她不敢说别的话了,两个人走了医院门口,谢梨花说:“我回去了。”
“好。”袁青山说。
和她说话让她觉得很疲惫,袁青山没有办法想象,是否真的有那么一天,她们要生活在一起。
她回了家,发现家里来了客人,是一个清秀的小男孩,长得有些女孩子气,和张沛算得上同一个类型。
袁清江和他坐在一起看电视,看见姐姐回来了,站起来,说:“姐姐,你去哪了?我从医院出来就找不到你了。”
“临时出了点事情,对不起啊,你们还没吃饭嘛?我给你们弄。”她麻利地走进了厨房。
“我们在外面吃了,”袁清江说,“江乐恒请我吃的抄手。”
袁青山听到了一个似曾相识的名字,她又探出口去看了那男孩一眼,他礼貌地对她笑着点头,她想起来自己见过他几次,他居然已经长成了这个样子。
“你们同学啊?”袁青山问袁清江。
“嗯。隔壁班的,小学同学。”袁清江说。
袁青山在里面弄自己的饭,她把早上的剩菜热了,还有一点稀饭和两个馒头,她一起热了。
她热好饭,端着出来,看见江乐恒站起来要走了,她说:“坐一会嘛。”
“走了走了,姐姐再见。”江乐恒客客气气地说。
两姐妹坐在一起,袁青山吃着馒头,她问袁清江:“你上午看见她没有?”
“嗯。”袁清江说。
“怎么样?”
“她给小娃娃打针,一个个地把小娃娃都打哭了。”袁清江皱着眉毛说。
袁青山有点哭笑不得,她没有办法让袁清江想起她小时候每次去打针是哭得如何惊天动地,让周围人都以为发生了什么巨大的惨案一样。
她忽然明白,就像自己面对谢梨花时候永远都有那种疲惫的感觉一样,袁清江面对她的时候,也永远充满着不能解释,无可逆转的厌恶。
她不说什么了,默默吃着饭。她想到母亲,想到她自己的母亲,她想到小时候一桩桩的事情,院子里面的人一个个看她的眼睛,直到此刻,她才明白她们在看的到底是什么,她忍不住出了一身冷汗。她又想起岑仲伯那天挥陈倩倩的一巴掌,现在她也明白了那原因——他和我一天生的,他和我一天生的——她心里不停地冒出来这句话,但是再没有了下文,她不能确知岑仲伯说的是不是真的,如果是真的,又到底意味着什么。
“我们今天认真跟爸爸说一下嘛,我真的好不喜欢那个人。”袁清江忽然坐过来拉她的手臂,她的眼睛像个烈士那样充满了坚定的关芒。
每次她的眼睛里面出现这样的神情的时候,袁青山就会觉得,这个世界上没有妹妹干不了的事情。
花疯子
很小的时候,我就认识花疯子了。那时候我还跟爷爷他们一起住在南门上临街的房子里,每天早上,我爷爷出去打豆浆,我还在床上迷迷糊糊地,就可以听见外面有一个嘹亮透彻的嗓子响起来了:“北京的金山上光芒照四方,毛主席就是那不落的太阳……”
整条街上的人一听,就知道花疯子出来了,他穿着一件掉了大半扣子的旧军服,背着一个箩筐,拿着一柄竹做的长钳子,看见他想要的垃圾就捡起来,熟练地反手丢到背篓里面去——他总是很早就出门了,在清洁工在每条街打扫干净以前,来收拾昨天晚上的残骸——他从西街转到南街,又从南街转到东街,最后是北街,一路走,一路唱着:“……我们迈步走在,社会主义金色的大道上……”
那个时候,我们镇上的人都起得很早,没有人会埋怨花疯子吵到他们睡觉,反而有些人就干脆起来了,抄着手靠在门上听花疯子唱歌,听到高兴处,就吆喝一声:“花疯子,唱个太阳出来喜洋洋嘛!”
花疯子立刻就开始唱:“太阳出来罗嘞,喜洋洋罗郎罗,挑起扁担郎郎采光采,上山岗罗郎罗!”——他的嗓音是那么洪亮,那样直冲云霄,好像这尘世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牵绊住了他。
还有一些日子,常常是星期天,太阳是少有的透亮的,花疯子一边走一边唱,后面就会跟着一群小孩,花疯子唱得兴高采烈了,就放下箩筐开始跳锅庄,孩子们看见花疯子又跳舞了,就叽叽喳喳扑上来跟他一起跳,他们就在路上围成一个圈子,一群人尖叫着,唱着:“北京的金山上……哟,巴扎嘿!”——那时候,就像是一个节日来了,半条街上的人都陷入了狂欢的愉悦之中。
因此,和我们镇上别的疯子和瓜娃子不同,花疯子得到了平乐镇大多数人的喜爱——虽然他穿得不是很干净,但长得高高大大,眉目俊朗,他的歌唱得好,锅庄也跳得好,在疯了以前,还是在藏区当兵的——人们对他甚至有了一种尊敬。
花疯子不姓花,我们之所以叫他花疯子,是因为据说他是为了和一个女的耍朋友的事疯了的。我爷爷说:“那个花疯子啊,被一个女娃娃甩了,就疯了!疯了就复员回来了嘛,造孽啊!为了个女娃娃!”——当然这只是男人们想法,女人对这样浪漫的故事总是充满了同情和向往,有时候,她们看见了花疯子,就会主动招呼他,把家里准备丢掉的一些比较好的东西给他,甚至给他一点东西吃,因此,花疯子可以说过得相当滋润。
在我小学五年级的时候,花疯子甚至成为了我的一个偶像。每天放学回家,我都会希望在街上看见他高大的身影,为了找到他,我从东街绕到西街,然后再穿过猪市坝的巷子回家,有时候我真的会听见他在唱歌,唱的是:“南方飞来的小鸿雁啊,不落长江不呀不起飞……”——我就背着书包追着歌跑,终于远远看见了花疯子背着箩筐在街上晃悠,我跑过去,跟在他后面,保持着五步的距离,觉得这样就能不被他发现,花疯子就继续唱歌:“天上的鸿雁从北往南飞,是为了躲避北海的寒冷,造反起义的嘎达梅林,是为了蒙古人民的利益……”——我看着他的背影,在年幼的我面前,显得更加高大了,他的肩膀很宽,有一种非凡的气度,我多么希望,就是他,就是这个人,他会带我远走高飞,到西藏去,到我没有去过的地方去。
我跟了花疯子几次,并没有被他发现过,但倒是被我妈发现了。
有天晚上,我妈从外面下班回来,问我说:“今天你是不是街上跟到花疯子跑?”
“你怎么知道?”我问。
“全镇人都知道了!”我妈说,“人家说你的女这么小就不学好,跟到要饭的跑。”
“花疯子没要过饭,他是捡渣渣的。”我低声争辩。
我妈黑了脸,说:“那还不是一样,总之以后我再听到人家说你跟到他,你看我打不打你!”——我妈妈说到做到,接下来好几天,她都来接我放学,我坐在我妈的自行车上回家了,生怕碰见花疯子,我不知道怎么面对他。
但我还是看见了花疯子——在我们镇上走一走,不可能不遇见花疯子——他背着箩筐弯着腰,在一个垃圾桶里面翻着,不时把东西丢到筐里面去,我觉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