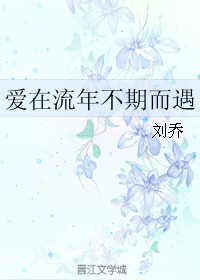流年碎影-第1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三、陈宇初。我们初上学时候他任训育主任,名启舜,房山县人。他中等身材,偏于瘦弱。特点是面无血色,而且永远没有笑容,所以学生上尊号为陈朽木。举止慢条斯理,讲话细声细语。可是学生都怕他。原因之一,他是负责训育的,有训人之权;之二,你面对他,看他的面色,听他的语音,会不耐烦到难以忍受,恨不得立即逃之夭夭;之三,“陈朽木来了”的威力常在,因而见到就有些胆战心惊。怕,对付的办法只有一个,是敬或不敬而远之。但这办法不能永远奏效,因为你总不能不上他的每周两(?)节的修身课。修身课是训育的道理化,要在课堂上实现之,执行者当然要是训育主任,即陈朽木。上这堂课,朽木的朽就表现得更为突出,无表情,声音细小照旧,新加的还有内容的干燥,构成总气氛的死气沉沉。想不到这种气氛却有另一种大力,是催眠,几乎是开讲不到几分钟,我们的睡意就袭来,表现为上眼睑下垂,说不定头还会点下去。我们当然不敢这样放任,于是挣扎,装作还有精神听。其结果是很苦。现在回想,在师范学校上课六年,课门类不少,教师不少,上课感到度分秒如年的也许不只一门,但考第一的必是陈朽木的修身课。也是随着政局变化,陈先生离职了。意外的是,若干年之后,确切时间和地点不记得了,总是在北京的某次会上,我遇见他一次。与过去不同,他和气,面上还浮着不少笑容。还记得听谁说,他熟悉陈先生,性格并不古板,常是说说笑笑的。如果竟是这样,那早年的表现为朽木,就是挑帘出来,表演给台下人看了。人要吃饭,有时就不得不把后台的本相藏起来,此亦人生之一苦也,偶一念及,不禁为之黯然。
四、王玉川。政局变化后,他曾任教务主任,名书薪,饶阳县人。只记得中上等身材,偏于丰满,风度是敞快加一些洒脱。他几乎没有什么善政、恶政可述,是否还兼任什么课也不记得了。这里说他,是因为有一次,片时间他成为了众矢之的,表现的高风使我终生不忘。是政局变化带来不少新事物,其中之一推到台前的是(国民)党。且夫有台前必有台后,这台后是为公益,也许竟是为私意,张三拉李四,李四拉王五,到某墙根,如此这般嘀咕一番,终于聚少成多,至于成群结队,手摇小旗,大喊拥护什么,打倒什么。且说这一次是为什么,如何联络,我都不知道,竟也尾随一群人,走往东南角四合院的南房(王玉川住在那里)窗外,齐声喊:“打倒王玉川!”其时是午饭之后,上课之前,喊声的间隙,听到屋里有答话,是“不用打,我早倒了”。这句答话泄了高呼口号的气,有的人有对证癖,挨近玻璃窗往里望,王先生果然躺在床上。已倒,用不着打了,来者只好如王子猷之雪夜访戴,乘兴而来,兴尽而返。是若干年之后,我攻乎异端,翻看禅宗语录,才恍然大悟,王先生这“早倒了”就是禅,可惜我尚无沙弥弟子之知,竟至交一臂而失之。
五、李星白。早期教我们国文,名锡庚,宝坻县人。身材高,不胖,却也不清秀。听说是个孝廉公,如果真是这样,那就是刘校长慕名请来的吧?但时代已经不是《儒林外史》的,孝廉公就不得不维新。办法是上课,立而不坐,间以走动,大声念课文,讲课文,说古人韩柳好,今人鲁迅、周作人等更好。他讲课的特点是声音特大,所以也荣获个外号,李大吵。这声音高,证明他很尽责;至于我们的所得,总当有些吧,所以政局变化之后,他随着刘校长去职,对于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做法,我们曾不以为然。
六、于赓虞。我在师范学校的后期他曾任国文教员,晏城县人。中等身材,面不白而清瘦。特点是披长发,总是沉思愁苦的样子。他像是任职不长,所以上课讲些什么也不记得了。他是文学革命后写长条豆腐干状的新诗的,词语离不开地狱、荒冢、死神、魔鬼等,所以有人称为魔鬼派(?)诗人。可是今昔一样,出奇就可以扬名,连《中国新文学大系》也给他一席地,说他看《晨曦之前》《魔鬼的舞蹈》《落花梦》等著作。以上三种,我是否读过,不记得了;但有一种,名《骷髅上的蔷薇》,我必读过,因为直到现在,它还卧在我的书橱里,也许还是作者送的吧。诗句都是“我将诗与剑在萧萧之白杨下做枕,让我在梦中杀死你无情之魔与神”之类。这样的新诗,我莫测高深,却对我有大影响,是畏而远之;万一有什么情意想用韵语表达,就投靠唐宋,学“画图省识春风面,环佩空归夜月魂”之类。
七、孙子书。我接近毕业的时候教我们国文,名楷第,沧县人。身细高而瘦弱,到通县教书是兼课,记得是师范大学毕业之后曾留校任助教,不久就到大辞典编纂处,住在中南海居仁堂西四所。他讲课声音不洪亮,可是清晰,有条理。不知道有何证据,我感到他有学有识,人也温厚可亲近。之后当然是交往渐多,关系就近起来。记得我有事到北京,不只一次到中南海去看他。他单身住在西四所院内的西厢,由室内古籍之多已经可以推想他将来要走什么路。其时他身体还可以,乐观,钻故纸之余也吟诗。对我,以相知款待,还记得曾同往西单西黔阳去吃饭。大概时间不久,他就不往通县,专力研究他的通俗小说目录了。他体弱,可是勤恳,不断有考证的论文问世,得到老人物如傅增湘、新人物如胡适等的赏识。其后,为了广泛涉览通俗小说版本,他曾往日本、大连等处图书馆,结果写成《中国通俗小说书目》等大著作。治学,他一循乾嘉学派旧规,走上“专”的路。出路呢,当然,只能登上大学讲台,或入研究所坐木板椅子。几十年间,他又写了不少,显著的有《沧州集》《沧州后集》等。可惜晚年不幸,碰上大革命,存书都丢了。书呆子,失掉书,何况其中还有不少手批本,如何受得了?他先是懊丧,终于发展为精神小失常,挨到1986年,作古了。他到北京以后,我同他来往不多,原因,他的一方是学业以外少余力,我的一方是经常自顾不暇。是“地”假良缘,1976年唐山大地震,他住的学部宿舍是国产的,不如北京大学继承的原燕京大学进口的房子坚固,他逃到北京大学,住在他甥女家的健斋。其时我住在北京大学女儿家,也逃,到健斋略西的红三楼。于是一下子我们成了近邻,又都干不了什么,就坐在未名湖边闲谈。其后自然又是分别。见面难了,一晃又是十年,他含恨走了。我有时想到他,又能怎样呢?也只是写几行不痛不痒的,收入《负暄续话》,以略表怀念之情而已。
《流年碎影》 前辈留影(2)
八、宁绍宸。他是英文教员,名世缙,宁河县人。个儿不高,体较丰满,头圆,两目有神,一望即知是个精干人物。讲课,口齿清朗而流利,并表现为随随便便的样子。也许因为我们被沉闷吓怕了吧,都愿意上他的课。可是不知为什么,有一年的暑中,传说他暑后不来了。我们都是脑子里没有一点世故的,未三思,也没有经过调查研究,就派代表找校当局,表示挽留。记得我是代表之一,在校当局面前述说理由和愿望之后,校当局(教务主任?)说:“只要宁先生答应来,我们就下聘书。”可叹,我们居然把这因果倒置的话看作诚意,还去找宁先生。结果自然是宁先生只能说不想来,我们落得个“可怜无补费精神”,受了玩弄而并未觉得。
九、胡星联。他是教师里年岁最大的,所以外号胡老头儿,教博物,名魁第,霸县人。个儿不高,体不胖,教我们时候年近半百,背已经有点驼。人和气,面对人,总是含笑的样子。讲课也如其人,温和细致。这样教,意在多灌输知识。也许就是因此,他期考看考卷,也喜欢多。同学们都洞悉此情况,所以,比如考题问语言是做什么的,就不只答是交流思想感情的,而要从语言的起源说起,说到语言的分类,直到滥用,说张家长、李家短,骂街,等等,总之要密密麻麻,写满考卷,才能得高分。若干年之后,我择术不慎,常常要看所谓文,其中有些颇像我们彼时的博物考卷,我皱眉之余,就不由得想到这位胡老师,为他的有超级耐心而叹息。
十、张玉书。他的职务是文书,其时名为书记,名瑞麟,宝坻县人。长身,清秀,文雅,有飘逸之气。同我们没有交往,我们知道他,是因为听道听途说,他很喜欢喝酒,喝要有好的下酒物,牛市口某家卖的熏鸡。同学中也有喜欢喝而不能常得的,也许出于由羡而嫉之情吧,有时就在背后评论,说:“张玉书,哪里是好喝酒,不过是借酒之名,多吃几次熏鸡罢了。”这是否是事实,我们没有去考证。多年之后,我想到师范学校大院内的人物,有兴趣评论甲乙,他的影子就浮到眼前,我想,如果我们还迷恋《世说新语》的六朝气,大概只有他还有一些吧?
十一、张腾霄。他是史地教员,名云鹤,束鹿县人。我没听过他的课,如果没有后来的交往,是一点印象也没有。是40年代初期,由于某种机缘,我们认识了。他身体、风度,属于所谓癯儒一类,枯瘦、苍老,肚子里却不寒俭。他有才,能写,还能编。他编过《晨报》,说其时办理编务的只他一个人。他住在西单以西,我去看过他,室内陈旧破烂,床头悬个横披,上只“忠恕”二字,是康有为写的。他常常失业,也就经常缺衣少食。40年代过去,时移世易,我就没有再看见他,想来早已往生西方净土了吧?
十二、许君远。他是英文教员,名汝骥,安国县人。我没听过他的课,可是印象却不浅。来由还不少。其一,他长得清秀,风度翩翩,一见必惊为罕有的才子。其二,据说他写过小说,出版,是鲁迅给他写的序。其三,他由南国北返,途经某地,与一妙龄比丘尼相悦,有情人竟成为眷属。还可以加个其四,是不久前听唐宝鑫同学说的,是他上课,不知怎么就扯到《西厢记》第四本第二折的“看时节只见鞋底尖儿瘦”,念完,他让台下同学想象这鞋底尖儿瘦的形状,然后写真式地画出来。更有意思的是他也不甘寂寞,拿起粉笔,在黑板上也画一对。这是讲课的浪漫主义,我幸或不幸,没有听到看到,如果听到看到,以后进京入红楼,上林公铎的唐诗课,听讲陶渊明,就不会感到奇怪了吧?
《流年碎影》 同窗忆旧(1)
上一个题目写了师范学校里的前辈,依顺流而下之理,还应该写写同辈,即同学。在学校蹲六年,我认识的同学总有几百名,不得不挑挑拣拣。取舍的标准容易定,是只收与自己关系比较深也就印象比较清楚的。但深和清楚还有程度之差,所以选就还要有个数目的限制。想了想,祖传的成规,说好说坏,都是凑足十项,干脆萧规曹随,也说到十名为止。十名的排列,以先亲后疏为序。
一、梁政平,附带说说他的胞弟梁政善。他是昌平县马池口村(在县城南略偏西八里)人,也考入师范学校的第十二班。其时的习惯,自负为有文因而超出农民的人都有名有字,梁政平的父亲是在县里从事教育行政工作的,不知为什么几个儿子(无女)都有名无字。有名,自署用字是以字行;无字,人直呼其名是以名代字。这是说,由相识的1925年起,到他病故的1951年止,我都叫他政平。他小于我两岁,身材不高,清秀,性情偏于柔弱,说话细声细语,与世无争,因为不敢争。不记得以何机缘(住同屋?),我们就好起来,感情还逐渐加深。单说我这方面,表现为愿意同他在一起,学期终了,握别,心情感到凄凉。其后若干年我读蔼理斯的书,知道同性间也会产生异性间的感情,我和他是不是这样?说是,嫌不够明确;说不是,自己也觉得,就说是友谊吧,总是超过一般的。这非一般,表现为二十几年,至少是心情上,我们能够形影不离;他回昌平教县立小学,我常去看他,去就在学校或家里住几天;他有时失业或到北京来,就住在我家里;40年代后期,他也来北京住,住处相距不很远,总是隔三天五天就见面。他很早就结婚,家里包办的,生了一个女儿。内,居室,不如意,外,职业,也经常不如意。大概是40年代中期,忘记由谁介绍,他到蒲松龄的老家淄川县城去教小学(还兼校长?),在他,这是一生中唯一的远征。只是一年就回来,我问他曾否到蒲松龄的家乡蒲家庄(距县城八里)去看看,他说没去。他就是这样柔弱、保守!可是与他同来的有个女的,姓王,说是在家乡腻了,想出来看看,找个工作。人不清秀,或说不漂亮。看形势,是政平很喜欢她;她跟着来北京,也不会无意吧?她不久就居然找到工作,在京北某镇教小学。又不久,传来消息,是她到那里又走向有情人成为眷属,可是这有情人不是政平。政平向来是寡言语的,对这件事更是这样,由山东回来,带着一个女的,怎么回事,他不说;意中人飞了,心情如何,他还是不说。但人,连藏眼泪的力量也是有限的,所以看得出来,他是痛心到万念俱灰了。我知道这不是劝说所能缓解的,又因为他沉默,我不好挑明了,也就不说。此后他忍,忍,忍,看表面,过去了,或淡薄了,其实不然。是40年代末易代之际,其时他在北新桥附近一个小学做事务工作,病了。先是好好坏坏,渐渐就不能上班了。他家在东直门内城楼下西南部的一个小院里,有妻女陪着。我们见面不多了,原因是他病加重,出门有困难;我呢,三反五反还没来,已经感到高压的空气过于沉重,如临如履了。记得是他弥留之际,我去看他,他躺在北房靠西的里间,不让我进去,说他是结核,晚期了,要防备传染。他没有提永别的事,只是嘱咐我,说门外有水,每天早晨要沿着湖滨走走,求身体能够健康。他的妻女催我走,当然是为我,身和心。果然就这样永别了,就在会面后的夜里,他走了,年岁刚及四十。幸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