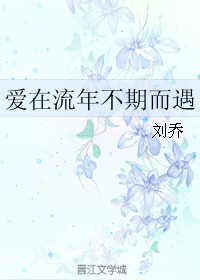流年碎影-第15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有诗意的联系,最难忘的一次是某年的秋日,一同往通县去温旧梦,吃小楼肉饼,在北城墙上晒太阳。解放以后,新风是少说私话,我们来往少了,但未断。大革命来了。都自顾不暇,断了;到70年代末,飓风渐杀,又恢复来往。他青中年时期写了不少新诗和散文,到老年锐气减了,安于在柴门小院里与鸡兔为伴,由于我的劝说和催促,才译了两本书,温源宁的《一知半解》和辜鸿铭的《清流传》。我,怀抱我的偏见看他,有拔高的一面,是诗意多,有下降的一面,是应该顾及的也不管不顾。这下降的影响,可举的例很多,只举大小两个:大是应该写得更多而没有写得更多;小是经手的书不少,单说自己写的十几种,竟也丢得片纸无存。近来他记忆力减退,证明脑力差了,如果差到不宜于看书,那就片纸无存也关系不大了。
八、荣在林。霸县人,字翰园,略长于我(?),是第十班同学。中等身材,结实型的丰满,精干,多才与艺。也就靠这样的外和内,1928年时移事异,男女由只许远观变为可以近谈的时候,男师范不少人厉兵秣马,奔向道署街(女师范所在地),追,他在内,居然就成了。女方名傅宝珍,是玲珑的丰满型,郎才女貌,毕业后载文君进京,筑香巢享希有(因为绝大多数空手而返)之福去了。记得他是在某中学任教,住在鼓楼以东,已经生儿育女,由岳母大人照看着。岳母也很精干,所以在有来往的同学的眼里,他的小家庭也是数一数二的。上面说他有才,这才表现为能写能画,还能篆刻。我当年诸事甘居下游,唯有揩油,至少是有时,不落人后,于是也就买价不高的寿山石一对,托他刻《论语》成句“多见而识(读zhì,记住)”和“不忘乎生”。总是托他的福吧,半个世纪以来,什物大半失散,这对图章却依然卧在抽屉里。索性再取出来看看,结体和刀法走齐白石的路子,只是苍劲不够;边款“仲衡仁兄属刊论语成句己卯(案为1939年)中秋在林”共字六行,却潇洒流利。这仍是以才胜。且说刻这佯的语句,是其时我还钻故纸,喜欢“多见而识”和“不忘乎生”这种境界。一瞬间五十多年过去了,像是应该检查一下。前者,“多见”没有做到,“识”就更没有做到。可告慰者是后一种,清夜自思,单说人,包括早已远去的,甚至化恩为怨的,我都没有把他或她请到心室以外。生,遇,总是不容易,还是以“不忘”为是。荣在林,傅宝珍,40年代以来,与我渐渐断了来往,如果今日还健在,白发对白发,想到燃灯塔下的昔日,也当“似梦里”了吧?
九、周信。我的香河县同乡,字子诚,第九班学生,推想要比我大三四岁,毕业以后回本县,到(国民党)党部工作,不久也考入北京大学,读史学系,与我同年级。身材不高,清秀,面和蔼而内严谨;这“谨”还与“慎”结伴,处事认真,总是小心翼翼的样子。事业心强,不甘居人下。这种种加在一起,给人的印象是,为人理胜于情。我们交往不多,听说解放后在北京某中学教书,住在崇文门外磁器口一带。其时他年逾不惑,想是因为有历史包袱,更要表现为恶旧乐新,争上游,没有人要求他同孩子们一起跳,他却带头跳,力不从心,腿骨折断,从此就再也不能行动自如了。残疾,听说近年来多受到照顾,希望他也不例外,不再为表现什么而做力不能及的。
十、王长义。也是我的香河县同乡,字子辉,入第十四班,年龄与我差不多。高个子,风度是体育健儿加阔少。生活也是五陵子弟式的,向往的是吃喝玩乐;行有余力,也未必亲近书本。混到毕业,到北京,理想的出路是找个门户开放的大学,再自在几年,于是入了中国大学(?)。我们几乎没有交往。记得在某处遇见一次,问他每天干些什么,他说“三打加一跳”,三打者,打球,打牌,打野鸡,一跳者,入夜回学校,已经闭门,则跳墙进去是也。若干年之后,又曾听到他的消息,是终于混不下去,转乎沟壑了。用常人的常识眼看,他的生活之道不足为训,这里拉他来做殿军,是想说明,出于我们师范学校之门的,虽然绝大多数懦弱无能,却也有能跳墙的。(附记:这一点旧事早已成为模糊的影子,写完,忽然想到,这能打能跳的同学也许名刘长庆,字子久,若然,以上的述说就是张冠李戴了。逝者如斯,可叹可叹!)
《流年碎影》 常态之外
用比喻解题,小家小户过日子,吃炒肉丝、熬白菜之类是常态,餐桌上忽然端上一盘烂扒鱼翅是常态之外。通县六年学校生活,我回想,由遐想、上课、读书直到吃喝拉撒睡,等等,几乎都属于常态之内。说几乎,是也有常态之外,虽然为数不多。这不多的一些,推想不会有几个人感兴趣,还想写,也可以说是来于个人迷信,即自己的疮疤比西施的笑靥还美;或者说来于小家子气,竹头木屑,都舍不得扔在垃圾堆上是也。不管来于什么吧,既然决定写,就写。计可以分作人事和天象两类:人事两种,1926年的军阀战争和1928年的小型易代;天象三种,大风、大雪和纯冰雹。
先说人事之一,1926年的军阀战争。军阀,指北洋军阀,派系,人头儿,盛衰,朝三暮四和朝四暮三,情况复杂得很。单说规模比较大的战争,有1922年的第一次直(以吴佩孚为代表)奉(张作霖)之战,以直胜奉败结束;有1924年的第二次直奉之战,以直败奉胜结束。1926年春天,交战的双方更加复杂,撮要说是以冯玉祥的代表的国民军在西北方,张作霖的奉军和张宗昌、李景林、褚玉璞的直鲁联军在东南方,争夺京、津、保一带。混战一个短时期,国民军败了,一段一段往西北撤,胜者当然是一步一步往西北进。于是而通县一带,也就有了国民军残部(查资料,属唐之道)往西逃、直鲁联军先头部队(属李景林)往西追之事。耳闻是有疏疏密密的枪声和间或一两响炮声。步枪声有时很近,像是就在北城墙以外。其时我们的好奇心胜过怕死心理,就约集几个人,记得是上午,登上城墙(东部有路),伏在上面看。就在城外不远,有零零星星的兵,西方的边射击边退,东方的边射击边西进。划空的枪弹声不断,可是没看见有人倒下。世间的战争不少,文字记载(包括小说)的战事更多,亲眼所见,一生也只有这不起眼的一次。与现代化的大战相比,这次的冲突确是微不足道,可是对我们的影响却不很小。先是一次怕。国民军以纪律好著名,我们不怕;怕的是直鲁联军进城,轻则抢财物,重呢,会不会打人杀人?果然有一些就进了校门,职教员,学生,有些已经回家,剩下的只好闭门室中坐。幸而入校的是胜利者,还要定时归队,抢,时间不能过长,取物不能过多,恐怖时期一会儿就过去。现在只记得,教体育的马骥德老师,右口袋的五块现洋被掏去,左口袋的一百多元钞票却保住了。更大的影响是课停了,复课无期,还担心战争的进退有反复,都认为不如趁战场西移,赶紧回家。可是离家一百多里,长途汽车没有了,怎么走法?形势是只有回家一条路,也就没有选择的余地,于是,记得是四月后半的某一日,与既同班又同乡的郭士敬商妥,第二天早起,只带一个小包,结伴步行回家。第二天赶上大风,路上情况,留到下面天象部分说。
再说人事的另一种,1928年的小型易代。大局面是南方以蒋介石为代表的挂国民党牌号的势力北上(所谓北伐),压低了北洋军阀的势力。说压低,不说消灭,是因为到北方,真枪实弹用得不多,原来的地方割据势力,看南风力大,表示归服,最突出的如东北原来的奉系,费了若干周折,才接受南京政府的官号,换为青天白日旗,也就过去了。这里只说小局面,是通县,尤其学校之内。记得是暑假之前,许多人感到空气已经是山雨欲来。征象有模棱的,是一些自视甚高的同学于原来的傲慢之外又加上不少得意,并且常常三三两两,在僻静的地方耳语。征象还有确实的,是有些人(或说就是那些自视甚高的)积极出动,拉一些圈外的人加入什么组织。我也曾受到这样的劝说,意思大概是年轻,应该有大志云云;至于行动,则说得吞吞吐吐。其时我对这些毫无所知,但感到必与争统治权有关,心情是怕加怀疑。就在此时,一个上班的同乡侯君也来劝说,意思是那些人鬼鬼祟祟,拉别人都是为自己的私利,要躲开他们。其时我还没有接近佛道,可是竟也以为一动不如一静,于是趁着放暑假,打点个小包,坐长途车回家了。
假期终了回来,情况真就变了。从上到下说,最高的统治机构由北京的北洋政府变为南京的国民政府;其次的统治机构由直隶省京兆变为河北省;学校的牌号当然要随着变,京兆师范学校寿终正寝,改为河北省立第十师范学校。然后是校内,语云,一朝天子一朝臣,无党无派的刘校长下台了,换为国民党员段喆人;其下的主任,以及一部分教师,也就不免有些变动。转为说我们学生,值得说说的变动主要是心理的,总的说是由原来的一贯平静变为一阵子狂热,也就由原来的不识不知变为自以为豁然开朗而实际是同样糊涂甚至更加糊涂。仍说心理方面的表现,是:一、相信自己真就认清了治平之道,即不少人高喊的三民主义;二、自己也应该以天下为己任。心理必表现为行动,是几乎是全体同学,都填表,加入国民党。都加入,热度不同,少数热得烫手的,出入党部,天长日久就有得,或挣得某种官衔,或相中个意中人,成为眷属。曾狂热而没有完全放弃冷静的,也许因为无所得吧,不很久就有些灰心,至少是疑心,觉得所谓革故鼎新,大概是换汤不换药。这灰心或疑心,也许在上者也有所察觉,于是而有党员重新登记之举。我是既灰心又疑心的,所以就放弃这个以天下为己任的“光荣”头衔,钻入小图书馆去念鲁迅和雨果去了。后来回想,经过这次小型易代,我也不是毫无所得,这所得,说最值得珍视的认识,是听到什么口号就头脑发热,结果常常是一场空。
再说天象。其一是大风,上面已经提到,是避战乱,回家的一天遇见的。从早起说起,是天刚亮,我和郭士敬就走出校门。已经起风,不很大。不到早饭时间,空腹出来,希望到街上买点吃的,没想到家家闭户,卖什么的都没有。只好怀着希望往前走。出新城南门,上了京津公路,风转大。路上一个人也没有,也没有兵。——也曾遇见一个,躺在公路右侧的田里,虽然风很大,还是臭得使人作呕。其后若干年读佛书,修持方法中有不净观,我曾想到这个屈死鬼,认为以不净设教,确是有一面之理,可惜事实是还有另一面,是生的红粉佳人不是臭,而是香。言归正传,约莫走出十几里,风更大了,幸而我们也是由西北往东南,顺风,记得一抬腿,这条腿就被风推得往前移;背自然更是这样,总像是有大力往前推。谢谢风神关照;只是神也各有所司,不能使我们把空的肚皮装满。又向前走一段路,实在饿得难过,迈步的力量也小了。我们商量,可否用讨饭的办法度过困难。路左侧二三里有个村庄,我们想试试。继而想到登门,张口讨饭吃的情况,觉得太难为情,只得仍往前走。幸而天无绝人之路,走到马头(位于通县与河西务的中间)以北四五里(已走出约四十里)的长林营,坐长途汽车常见的路东侧卖食品的那个小店里有人,我们进去,说明空腹回家的情况,问有什么现成吃的,如花生之类,先吃点。店主人说,他们逃兵乱,也是刚回来,屋里都空了。我们求他想想办法。他动了恻隐之心,到后面找找,说缸里还有些玉米面,柴还有,“给你们做一斤面的糊饼吧。”我们千谢万谢,等,好容易熟了,端来,我们狼吞虎咽,吃到所余无几的时候才相互问:“这面有发霉味,你没吃出来吗?”语云,饥者易为食,果然不错。饭后,我们继续赶路,仍是借风之助,到河西务,下公路,又走三十里,未入夜就到了家。这是我一生中走路最长的一次,大约一百二十里,如果不借风力,估计是办不到的。
其二是大雪。记得是易代前后的某一年寒假,同路往河西务的十几个同学共同包一辆汽车(其时车都不大),早晨约八时由校门口上车。其时天气阴沉,已经飞雪花。车东南行,雪越来越大,直到中午才到河西务,积雪已经深一尺上下。离河西务不远的同学分散回家,剩下几个还要走一段长路的,不记得由谁带领,到一个熟人家去吃午饭。记得主食是烙饼,莱是肉片熬白菜粉条,因为既冷又饿,觉得很好吃。雪还在下,主人留住下,待次日天晴再走。我们怕雪转大,那就更难走,决定冒雪回去。路看不见了,雪很深,只好一步一步往前挪。有如蜀道之难,直到天黑,也终于到了家。其后几十年,老天爷像是也泄了气,雪还有,却不能再见那样大气派的。
其三是纯冰雹。是一年暑假回到家里不久,记得刚过午,天气骤变,降了冰雹。块头不大,只有手指肚那样,奇怪是密集,不掺和一个雨点,只是片时就有两寸厚。想起来真是惟天为大,降冰雹也能清一色。但也只是这一次,后来若干年,若干次,就再也没有这样的了。
《流年碎影》 进京
在我的人生的道路上,进京是个比较大的变化,比喻说,出门散步,无目的,可以往东,也可以往西,不知怎么一来,向东走了。所见,所遇,就限定为东方这一路,不易变,或简直不能变。这就成为像是命定的路,指实说是书生的路。不好吗?知足常乐,既是上帝限定这样想的,又是圣贤勉励这样做的。这是说,我不只安之,有时回想,还觉得如此这般也不坏。飘飘然了,就宜于或乐得加细说。然而可惜,我的记忆力很坏;从1928年暑后起,本来可以借助日记,不幸辛辛苦苦十年,每晚记,总有十几本吧,都毁于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