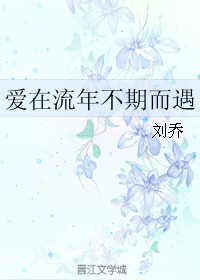流年碎影-第29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曾任山长。还可以欣赏其流风遗韵,如游廊壁上嵌有不少石刻,展厅里悬有不少名画,一般公园里就见不到。第一次入内看,印象至今还清楚的,有一副木刻的对联,邓石如所书,联语为“海为龙世界,云是鹤家乡”,草体,笔画龙飞凤舞,真可以说是见所未见。又一件是摆在展厅一端的一个龟甲,长二尺以上。旁边有个说明,是前若干年,传说城南大清河中某处有深潭,为龟巢,人不慎,在水中走近了,就会被龟曳入巢中吃掉。某年(估计是民初),驻军一旅长的儿子下河游水,近深潭,果然就失踪了。旅长有武力,当然要报仇,于是用小炮对准深潭打,几发之后,居然浮出一个大龟,已经丧命,因为物罕见,事也罕见,就陈列在这里。
大清河有一段紧靠南城墙,辟为城南人民公园,也可以游。水由西向东缓缓流,果然很清。岸上有宽阔的空地,树不少,与莲池比,多有野趣。水流到城东,有码头,我也到过。船不少,搭乘下行,可以到白洋淀、胜芳和杨柳青。几个地方都是北地的水乡,风景好,人秀丽,总想得机会沿途去看看,至今也没有如愿。时乎时乎不再来,听说千里同风,也都现代化了,那村头渔网,桥畔罗裙,也就不再有了吧?
游,还有市井的。由城中心北行,有个城隍庙,性质同于北京的天桥,如果也不弃下里巴人,就可以进去,看看各种杂耍,如果更下,如今日有些所谓作家之走火入魔,也可以破费一角两角,算算流年,批批八字。可惜我多疑少信,所以走到门口、总是望望然去之。何以还要到门口?是因为东行数十步转南有一条窄小的街名紫河套,是旧书旧字画的集中地,旧习难改,愿意常去看看。街不长,两旁的铺面破破烂烂,货不多,同样是破破烂烂。但正如佳人之喜欢游服装店,我是并不因残旧而兴趣少减。语云,既在江边站,就有望海心,有时也就买一点点。记得书曾买《徐氏三种》(三百千加注),画曾买王莲心(名宸,清朝乾嘉时期画家,居小四王之首)的山水屏。书毁于七七战火;画带回北京,之后看多了,知道是伪品,扔了。
游还有远途的,是1937年春天,清明节后,学校组织往易县去看西陵。坐火车北行到高碑店,换车西行到梁各庄。也许在那里住一夜吧,那就第二天入山,游西陵。地势不像东陵那样空旷,树多,苍松翠柏包围着几处陵墓,像是兼有园林之美。是否看到易水,不记得了,但脚踏的是易县,也就不能不想到“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壮事迹。易县产一种绿色的石砚,我早有所闻,路上注意找,未见有卖的。原路回保定,遇见凄风冷雨,至今还记得,恨不得立时钻入某间屋,围着火炉暖一会儿。
《流年碎影》 保定一年(2)
游说完,转为说口腹之欲。上面说保定多有古气,因而也就会反映到食品方面,老字号,有些品种,不离家常而味道好。城中心稍偏西路南有个商场,很像北京的东安市场,名马号,里面有些饭馆。一个最有名的是白运章,回教,卖蒸包子(饺子形),保定人呼为白运章包子,都爱吃,价不贵。我当然要尝尝,羊肉馅,肉多而肥,如天津包子之油腻,只能说是各有所好吧。我喜欢吃的是一种名为饴饹条的,用荞麦面掺白面,放在有漏孔的饴饹床子上压成条,或炒,或用炸酱拌,味道很美。据说城中心穿行楼附近有一家名藤萝春(?),以卖饸饹条出名,我未去品尝,我吃,是就近往马号内的两益馆。是1956年的春天,我与同事郭翼舟兄结伴,为考察教材使用情况又到保定,当然想重温吃美味之梦,去找,连卖的店铺也没有了。以上说的是就餐,还有买回家吃的两种名产,店铺名马家老鸡铺和槐茂,也要说说。马家老鸡铺在督署街偏东路南,回教,门面不大,自产的鸡(忘记制法)和酱牛肉、酱牛杂碎很有名,物美价廉,物美不好说,价廉则好说,酱牛肉是两角五分一斤,酱牛杂碎是两角一斤,我在拙作《物价》(收入《负暄续话》)一文中曾谈及,心情是逝者真就一去不复返了。槐茂是个酱菜铺,在西街偏东路北,以店铺门口有一棵古槐而得名。所制酱八宝菜,用篓装,远销外地。只是我吃过,觉得偏于咸,不如北京后门桥大葫芦的小甜酱萝卜。此外,保定的名吃还有二道口子(西门内路南第二条街的街口,记得在路东)的罩火烧,我路过,看是用深锅煮猪肠子之类,锅边煮火烧,没有兴趣尝,以致交一臂而失之。由名吃又想到保定的名产,当地谚语说的,保定倒有三宗宝,铁球、面酱、春不老(雪里蕻)。三种我都尝试过,果然名不虚传。春不老比北京街头卖的几乎长一倍,却比北京的嫩。甜面酱,天津也习惯吃(北京习惯吃用黄豆做的,名黄酱),味道确是不如保定产的。铁球的用途是锻炼手力,一般是一只手揉两个。保定用手工做,球内装大小不等的一个小球,揉时可以发出不同的金属的清脆声音。我手头还有一对中号或小号的,为一个学生所赠,近年恢复大量生产,改为用机器,手工让位,我这一对也就成为希有了。
保定一年所经历,或说所得,还有一桩必须表一表的,是学开汽车。是到校之后不很久,学校从什么地方请来一个人,还带来一辆旧轿车,说办汽车训练班,时间用下午下课后,一周三次(?),三个月毕业,学费若干,教师参加,学校代交。其时我行有余力,又考虑生活技能,可以备而不用,不可用而不备,还有,学会了,在大路上奔驰,也会比坐教室有意思,就参加了。教师男性,三十多岁,细高个子,精明和气。先入课堂,听讲机件之理,接着跳过学修理,就上车手握方向盘,学开。大部分时间是在操场,接近末尾到城外的公路上,都是由停到动,跑一段路,停止。考核,我的体会,重点是手脚的应变能力,要求速度快而不生硬。据教师非正式评定,我竟考了第一。如果教师的评定不错,我不拿方向盘,而走眼看书、手拿笔的路,也许是最大的失策吧?可怜的补救之道是这里记一笔,以期我的相知以及未谋面的相知都能知道,我年轻时候,是也曾有到阳关大道上驰骋的大志的,有志而事未竟成,终于不得不局促于书桌前,涂涂抹抹,乃“天也”,“非战之罪也”。
最后说人。保定一年,实际只住了不足十个月,其时还没有“人多力量大”的高论,人也遍地皆是,连学生在内,新认识的自然不会少,其中并有一些至今还有明晰影像的,可是交往程度深而想说说的只有一个,是在那里教高中国文的和培元(名泰)。他是邢台附近内丘县的人,燕京大学毕业,大概中学上的是育德,校友回校教课不见外,显得很活跃。他小个头儿,穿考究的长袍,有名士气。也许因为好交吧,有时也就同我谈谈。我觉得他为人敞快,思想开明,可交,谈话就推心置腹,总之,关系就越来越近。其时他正恋爱,对方姓陈名玫,住在北京,如一切陷入情网的人一样,身远则以信多补之,来信不只情意缠绵,而且文笔优美,这秘诸自己抽屉就有如“衣锦夜行”,于是常常就让我也赏识一下。我的怀疑主义的老病又犯了一次,但疏不间亲,也就没有表示。后事如何?代笔非代笔的事乃他人瓦上霜,以不管为是,只说关系重大的,是不久人来保定,变隔数百里兮为共朝夕,也就用不着写信了。这说的是和君的小布尔乔亚的一面。还有布尔什维克的一面,是这个时期他写了一篇不短的文章,题目以及发表在何处都不记得了,只记得是介绍马恩列斯中某一人的伟大的,连我这一向坚信人各有见的人看到也感到惊讶。学年结束,我们都回北京,未结邻而来往未断。七七战火燃起之后,他说他决定离开北京,陈玫女士怀孕,想托我照顾。无论为公为私,我都义不容辞。他路费不足,我从羞涩的阮囊中挤出三十元给他,并把陈女士接到我住的地方同住。他匆匆地走了,此后渐渐就断了音信。其后是陈女士生了孩子,内丘县来人接到乡下去住。是抗战八年的中期,不记得听谁说,和君到延安,任高级领导人的秘书之职,因游泳死于水中。这消息推想必不假,因为解放战争胜利之后,始终未见他衣锦荣归。
适才说想说的人只有一个,其实是还可以、或说“应该”加说一个的,那是其时念初一的学生张兆麟。说来很惭愧,保定一年,教过的学生过百,我却一个也没记住。是一年以前,我接到一封长信,说看我的某本拙作,疑惑是当年教他国文的我写的,问是不是这样,署名张兆麟。我复信证实。他健康情况不佳,过很久才来看我。谈及他的经历,是1957年加了右派之冠,发往塞外,二十年后才回到北京。他记忆力好,说到我当年讲课的情形,有如昨日。我很感奋,因为:一,我的门下也有像他这样敢直言的,是我的荣幸;二,保定一年面对的学生,还有记得我的,我感到安慰。
保定也一年,原因与天津的未能延续不同,也要交代一下。记得是一学年的近尾声,1937年的6月前半,学校发给我下学期的聘书。我对保定的生活印象不坏,又找新饭碗不容易,知道未遭白眼,当然高兴。其后是打如意算盘,暑中无事,带着室中人到北京逛逛,看看亲友,开学前回来,照常上课。主意已定,先写信通知住在沙滩一带的北大同学王云鹤(名恩川),托他给租一间住房,然后是收拾什物,家具之类不动,其余运往学校,存在教师宿舍楼的那间房里,随身只带一些日用的和替换衣服。6月底起程,坐火车到前门西车站下车,王云鹤来接,始知住房尚未租定。暂下榻于王云鹤处,不久就租得中老胡同(由东斋西行不远)21号(在街南,二房东姓蔡)院内北房东端的一间。这是民房,室内却有用具。进去只三五天吧,是7月8日的后半夜,院里人都被由西南方传来的繁密的枪声惊醒。到白日得到消息,是住在南苑的日军挑衅,攻打卢沟桥,我二十九军还击,冲突仍未平息云云。其后若干日,形势越来越紧张,通往保定的铁路断了,想到存于学校的那一点点财物,想托住在保定的一个亲戚取出来,写信,未能如愿,终于挨到9月下旬,得确信,保定陷落,育德中学毁于战火。存物一扫光,因为其时住在北京,只有随身的几件单衣,就成为天大的损失。说如天大,因为如存书,有些是新文学作品的初版本,就无论如何也补不上了。现在想,最大的损失还是由1928年暑后起近十年的日记的不再能见到,以致清晰明确、也许一生中最为重要的身心活动都成为恍恍惚惚的影子。应该旷达吗?可惜有时还是舍不得,也就只能含泪默诵一次“逝者如斯夫”了。人间的事常常就是这样缠夹,就说保定的饭碗吧,如果收到的不是聘书而是解聘书,我同样可以写“保定一年”,而许多珍贵的旧迹却依旧可以在身边。这又是“天也”,与之相撞,人毕竟是太微弱了。
附记:学习史部“纪事本末”的写法,写天津和保定的一段生活,故意把有关男女离合的不少事迹剔出去。这是因为下面还有“婚事”一个题目,如此处理,求分之则两便也。刘雪梅录入
《流年碎影》 婚事(1)
《礼记·礼运》:“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这是由“人生而有欲”方面看,吃吃喝喝与男女结合,地位是等同的。“生而有欲”是“天”,及至降到“人”的身上或手里,情况就变为一言难尽。在道人(用汉魏人的称谓)的心目中,两者都价值不高,如必欲去取,则所取是饮食而不是男女。常人或俗人就不同,两者都不能舍,可是表现为心情,常常是男女比饮食更急。可是心情的急又不愿意表现为言谈举止,这是说,都认为这是后台的事,不宜于推到前台。后台的事不好说,可是,又是人生而有之欲,就说是不美妙吧,却强烈而明显,是把己身的隐蔽起来之后,偏偏希望看看别人的。此描述什么什么星正恋、邪恋、结婚、离婚以及附带的欢笑、啼哭的妙文之所以能尽快刊出并换得高稿酬也。现在,我也写流年了,已经写到将及而立之年,仍是只见饮食而未见男女,推想有“索隐”之兴的诸公诸婆诸才子诸佳人早已等得大着其急了吧?为热心的读者,主要还是追述自己的昔日,不当不以真面目见人,决定标个专题写。但泄气的话要说在前头,这里准备的是家常便饭,您想吃本土的传奇加进口的浪漫主义,是注定要大失所望的。
叙事之前,想先说说我对婚事的看法。这看法来于对人生的一点领悟,可以分为高低或玄想和实际两个层次:高是可无,其理据是什么;低是应有,其情况是什么。先说高层次的。以“我执”为本位,我们可以问,或应该问:“不要男女,即无婚姻之事,难道就不可以吗?”有人认为不只可以,而且是“应该”。何以应该?一种理论是由辨析男女之欲的原因来,说我们所以有男女之欲,是因为天命(或说自然)限定我们要延续种族;而延续种族,我们并不知道也就更不能证明有什么宇宙论的或道德学的意义(个人的或全体的)。我们所能感受的只是这种欲给我们带来的拘束和压迫(到月下老人祠或娘娘庙烧香许愿就是好例),所以为了取得“万物皆备于我”的自由,我们应该不接受这样的拘束和压迫(如你要我传种,我偏偏不传种)。另一种理论(也可以说是兼实行),可以举佛家为代表。佛家看人生,多看到“苦”的一面。人生有多种苦,不假,有就想灭,至少是减轻。佛家自负为大雄,对于苦,是想以“道”灭之。灭之道是先求明苦因,他们找到一个力最大的是情欲。情欲由多种渠道来,其中一个最重大的是男女之欲,所以想灭苦,就要扔掉这种情欲。而这偏偏不容易,于是制戒,其中一个重大的是“淫”戒,对优婆塞和优婆夷宽容些,是只许正,不许邪,出了家则严格要求,不许男女,婚姻也就无立足之地了。以上两种想法都言之成理,后者并有人人都曾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