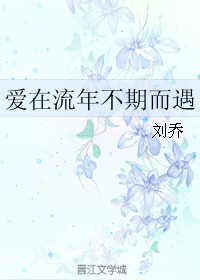流年碎影-第66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西跨院卖与文物专家张效彬,就不劳更换门牌了。张是河南固始人,名玮,父亲在清朝是显官,做到户部侍郎。他以父亲余荫,上了英国剑桥大学,学经济。估计头脑还是“中学为体”,所以回国以后,教过大学,所讲不是亚当斯密《原富》,而是曾国藩的《经史百家杂钞》。他还做过外交官,驻帝俄远东伯力的领事,卸任回国,带来公家欠的两万元的债和一位通英、法、德多种外语的白俄小姐,嫁他之后入中国籍,名张玛丽,解放后任外贸学院教授。他学习郑板桥,摘掉纱帽之后就优游林下。也是父亲余荫,玩古董。主要是书画碑帖,也有铜器、玉器等。据说眼力不坏,尤其对于碑帖。收藏古物,精品不少。推想仍是传统的匹夫无罪,怀璧其罪,他,以及说过的唐家,尚未说的房东李家,都抄了。不知以何因由,抄张家是在夜里。因为与我的住屋只是一墙之隔,又其时我的耳之官还未怠工,所以不少嘈杂的声音都听得清清楚楚。像是未动武,只记得张老先生答:“我确是没有枪。我一生手没沾过枪。”抄张家,目的明确,是要文物。据其后的传说,是张老先生态度坦然,说原来就准备交国家的,希望细心包裹,慢慢装车,上交,千万别碰坏了。就这样,一直忙到早晨,听说装了两卡车,运走了。怀璧其罪,璧交了,想不到还有后话,是几个月之后吧,老夫妇二人同一天被捕,男从家里,女从街上,一去就没有回来。
推论是星期天,因为我也在家,上午,红卫英雄,总有十个八个吧,来了。先到正院,进了房东李家的门。我们当然不敢出去看,只屏息听着。声音嘈杂而不很响。只一段对话最清楚,“这是什么?”是红卫兵问,“是字帖,练字用的,不是我的,是别人存的。”是李先生的声音。大概是红卫兵举起皮带吧,紧接着听李先生说,“是我的,是我的。”以后时间不很长,后来知道,只装了两箱,抬到大门外去。是查完正院之后,也许是另几个红卫兵,最后进了后院。人类的心情也真怪,气极发笑,乐极生悲,就在那红色暴力已经入目,近在咫尺的时候,我的心里反而像是空荡荡,不怕了。等待开门迎入,却一直走进东房。东房住的是由保定一带来的吴家的老太太,摘帽子地主(已有选举权),同住的是她的尚未成婚的儿子。隔着窗看,是把老太太赶到院里,未打骂,检查屋里东西,运走两个箱子。时间不长,可是有余韵,是留下勒令,老太太须还乡。这其间,有一两个红卫兵曾巡视院子,见西北部空地挂两个西屋祝家的鸟笼,拿走了。对于我们住的几间,连看也没看。
《流年碎影》 抄风西来(2)
嘈杂一阵过去,我们才恢复清醒,推想是不在抄的名单之内,但仍不免于后怕。李家呢,尤其吴家,老太太年近古稀,小脚,没有独立生活能力,要还乡,有投奔之处吗?难免关心,可是不敢表示,怕万一传到红卫英雄的耳朵里。其后是看着吴老太太垂头丧气地走了,儿子去送她。想不到过了半年左右,吴老太太民复原位,又到东屋过起柴米油盐的日子。据说是走农村包围城市的老路,村干部把她送回来,交与派出所,只说这样一句,“你们愿意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反正我们不要!”就成了。由这件事我想到河北大学写《古书虚字集释》的裴学海,学校被驱逐还乡的有三五个人,其他都是乡里不收,不久就回天津,只有他,家乡表示欢迎,就不能作《归去来兮辞》了。有人说,人生如戏,其实在大动荡时期,是人生难得如戏,因为戏中情节的发展,有脚本为依据,至于现实人生,就只能任机遇摆布了。
话扯远了,在那个人人朝不保夕的时代,还是以自扫门前雪为是。于是闭门,却扫之后,面对未离我远去的旧书,不由得思绪万千。曾经想到道家的“无”,佛家的“空”,痛感自己真如陶渊明所慨叹:“总角闻道,白首无成。”但究竟本性难移,这望道之光只是一闪,心就逃离老庄和释迦之门,回到世俗。于是又是一闪,不再是望道之光,而是爱染之光,觉得未被抄家,究竟是大喜事。书呆子习气,喜,还想找个说辞,而一想就想到王羲之的七少爷王献之,《晋书》记他的轶事有这样一件:
夜卧斋中,而有人入其室,盗物都尽。献之徐曰:“偷儿,青毡我家旧物,可特置之。”
一领青毡,因为乃家中旧物,后官至中书令的王献之尚且舍不得,况微末如我乎?所以多年之后,有时闷坐斗室,举目,看见半生相伴的旧书等还在,就不由得想到刮抄家风时的机遇,真会有上天保佑之事吗?管他有没有,还是循旧俗,说声谢天谢地吧。
《流年碎影》 割爱种种(1)
这是想说说,由1966年8月起,除四旧之风刮起,我这小门小户之内,都有什么大小的举动。记得几年以前,曾有读者致书《读书》,说我的拙作都是废话。其后我虽未能焚笔砚,却一拿笔就想到这位读者的箴规,努力争取少说废话。不幸是本性难移,只是完篇之后我自己检阅,废话(或岔出去的话)还是不少。现在写三十年前的除,忽而思路跑了野马,即又要说废话,怎么办?想了想,干脆破罐子破摔,顺着思路,即使成为大说,也不管了。大说,有来由,是提起除旧的旧事,最先浮上心头的是其时的心态,可“二”言以蔽之,曰迷和悟。除的结果是失,而迷(不知为不知)和悟却都是得。决定还是先说得。
所谓迷,是始终不知道,讲革讲反,用批用斗,任打任除,总之分所谓正确、错误,作为口号,喊,声音清晰,写,形体有定,可是具体到现实生活,简而明地说吧,怎么样就对了,怎么样就错了,却连个模模糊糊的轮廓也看不到。这是迷,不知,而要行,以何为指导?先是推想有决定之权的,如上上下下的红卫兵,是怎么想的。但这必没有如意的结果,因为,最根本的,是那些人就未必能想到,口号还有应该填充什么具体内容的问题。推想,外向,行不通,只得反求诸己,比如说,缩小范围,限定除自己的,案上有个瓷笔筒,能插笔,实用,像是与反无关,可是上面有人物画,而人物是旧时代的,砸不砸?答话只能是,光临的红卫兵说应该砸就砸,说可以不砸就不砸。总之自己是迷。因而我有时就想,就说是宗教吧,要求做什么或不做什么,最好能够说得明明白白。如佛门就是这样,要求以灭情欲之法脱离苦海,制戒律,如果你信受,弃家往山林精舍去修行,还思凡,想下山,就错了。至于要求不修就不然,常人的某些生活方式,某些事物,可要可不要,究竟要不要,经常是谁也说不清楚。不清楚,在平时,关系不大,除四旧时就关系重大,因为除是行,依照王阳明的理论,行之前先要知,而不能知,动手时就会左右为难。不得已,只好用秦始皇的办法,一群人,难于决定哪一个是冒犯至尊的,就一扫光。所以说起迷,带来的麻烦是双重的,一是想明白而不能明白,二是因为不明白,除就不免于扩大化。再说悟,正是来于除的扩大化。所悟是什么?是人,或扩大为生物,所有,身内身外,为数不少,不得已则忍痛舍一部分,但最后总要尽全力保留一种,是生命。人愿意活着,我当然很早就知道,但是,也许头脑里还藏有儒家舍生取义的理想吧,并没有觉得想活的力量竟有这样大。是除己之四旧,不是为“慈悲”而竟“喜舍”,使我进一步了解人生,恕我说句泄大家之气的,是大话谁都能说,一动自己的小命,就现了原形。原形何形?“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是也。
废话完,改为说具体的除。事杂,想以时间先后为序。大风起兮“除”飞扬,今语所谓信息,可分为入耳和入目两类:入耳是红卫兵入某家之门,检查,属于四旧者或拿走代毁,或命令自毁;入目是贴于各处的红卫兵的“勒令”,一般是限三天自己除尽,过期不除,查出,后果由自己负责云云。“后果”无具体说明,也就可大可小,可轻可重。猜测也要从重,所以又是怕。为了躲避后果,要先下手为强,动手除。排在首位的是书,因为摆在明面,数量较大。除的原则是,估计内容会有问题,或人有问题,就驱逐出境。前者如不少英文本讲性心理的,后者如张东荪、潘光旦等人著作,都清出来,由孩子装在自行车上送往废品站。计送去两车,孩子回来说,废品站不收,问能不能扔在那里,答随意,就扔在那里。书清得差不多了,检查属于装饰品一类的东西,如花瓶、挂镜、手镯、戒指等。这类东西,我们很少,但是语云,破家值万贯,东寻西找,也凑了一些件。当机立断,可砸的先砸后扔,难于砸碎的,趁天黑人不见,扔到后海里。
除书和花瓶之类是风卷残云式。接着对付书画就不想照方吃药。原因有大小两种:大是多年心所爱,费足力、眼力和财力所集,一霎时付之丙丁,实在舍不得;小是如张廷济写的一副集前人成句的对联,其与反的关系,究竟与潘光旦一流人有别。可是见诸勒令,书画确是应该算作四旧,怎么办?恰在此时(记得是9月),不知由谁发明,有了上交之法。单位已成立敌对的战斗队组织,吾从编辑室之众,加入一个,名为红旗联队吧,上交,就交到联队指定的一间房里,有人负责收,并放在架子上保管。这种情况就容许我采用兼顾的战略:为了表示有除四旧的决心,隔两三天就用自行车运去几件,上交,听候处理;又为了心所爱尽量不离开寒斋,先交可有可无的。就这样,交了几次,除四旧的热风大降温,像是都不再提这件事,我也就不再交。且说这些上交的书画之轴,记得是过了一年,不知道又根据什么教义,说是与反与修都无关,应该发还。我表示遵命,领回。
扔,砸,上交,用的都是驱逐出境之法,比较费力,也就难得除恶务尽。是除之风刮得最猛的时候,街道有发令之权的人通知,除四旧可以自己做(意思是不必等红卫兵),应该烧的可以在院里烧。我未再思,就觉得以积极响应为是。于是检寻应该烧的,标准是推想红卫兵看到会怒而言曰:“这个,你怎么还保存着!”这个标准,也是抽象的时候像是合用,移到具体就嫌过于模棱;模棱而不得不用,到执行的时候也就难免从重从快。许多质地为纸的,如旧报纸,旧杂志,旧书,书画轴册,等等,检出来了,利用星期日在家之暇,借房东一个尺把高的铁锅圈,掷于其内,点着,眼看着化为灰烟,送走了。计一次烧一个多钟头,大概烧两次吧,除降温,就不再烧。又是已然者不可改,事过回想,这“纸灰飞作白蝴蝶”,也有不少可以算作家之敝帚,值得怀念,甚至看做社会财富,值得保存的。当然,“值得”是俗见,会引来烦恼,不如转投佛门,求烦恼化为菩提,即少想用周公瑾火攻之法的损失,多念“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也。
但念完,也还要谈“减”,因为,就算作大革命的遗爱吧,主要是书,还有两次减。先说第一次,是1969年8月,我到凤阳干校接受改造之后不久,留在北京的住房必须扔掉(情况以后说),人(妻和岳母)和物迁北京大学二女儿处。二女儿的住房只有大小两间,我的书就成为过重的负担。我不在家,只能写信告诉他们一个甄别的原则,是笨重且估计用处不大的都不要,以便新处所还能容纳。其时我身心负担都很重(劳动很累,且没有改造好,无垢荣归的希望),为了照顾家属,信里大概说了“都扔了我也无怨言”的意思。他们也是多想照顾,又有建基于希望的乐观主义(我还能回去,坐在屋里看书),所以奉行的还是可留则留主义。但就是这样,当做废品处理,八分钱一斤,还卖得人民币二三十元,第九版《大英百科全书》就这样走了。连带的还清除了两种,由爱染的角度出发应该保留的。一种是一个旧煤火炉上的旧报刊,记得有二三尺高,都是因为有我的文章才留下的,家里人误认为废品,处理了。这里边虽然没有什么值得藏之名山的,但想到也曾费不少心血,留有昔日的足迹,一旦泯灭,也不免于有些感伤。另一种是书桌之下的一捆书画轴,可能是因为无处安置,堆在那里,家里人未打开看,也当作废品处理了。记得其中有扬州八怪之一黄慎的《东方朔偷桃图》,画已不新,草书的题却很好。最可惜的是熊十力师写的字条,他寓银锭桥时挂在屋里,50年代他移住上海,我帮他整理行装,给我留作纪念的,想不到竟随着十力师本人,也走了。
《流年碎影》 割爱种种(2)
再说第二次,是1970年的秋冬之际,在凤阳干校,想不到像我这样须大力改造的人也有探亲假,我回北京探亲了。进屋,看移来的书还未开包,总有二十几包吧,堆在墙角。我同于街头巷尾的常人,只要还有一口气,就愿意过得好一些。这包括化杂乱为整齐,于是其他都不管,先整理书,大致分类,上架。确知必装不下,就一面清除还可以割爱的,一面上架。大致用了将近两天的时间,存的都给了安身的地方,割爱的,装入麻袋,不很满的两袋,送往校东门外成府街的废品收购站,卖了。卖之时,不由得想到逛书店书摊时的痴迷,而又一跳就跳到佛门的万法皆空,“顿悟”人都是被置于俗和道的两端之间,绝大多数,滑向俗容易,滑向道就太难了。
那就坚守俗人的阵地,谈一点俗情俗理,即关于除,事后回想,是怎么看的。这方面也有大小之分,大是群体的得失,小是个人的得失。先说大,是确知有关群体的事,尤其不可发疯,因为发疯容易,因发疯而毁的一切就“黄鹤一去不复返”,悔之晚矣。何以还有悔?是恢复为清醒的时候,或下一代变为清醒,思念不复返的黄鹤,会写入历史,痛哭流涕。写入历史,会不会问,何以会有发疯之事?这是将来的事,现在还不好说。再说小,流为细碎,就不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