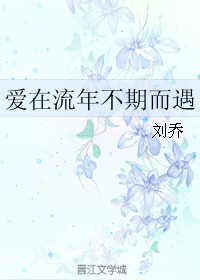流年碎影-第87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章,书末尾还收了两篇附录,一篇是“古籍笺注举例”,一篇是“文言阅读参考书目”。总名为《文言文选读》。每一课,选文前有“解说”,目的有近,是介绍本篇的情况,有远,是介绍可读的古籍的情况。选文中间有“段落大意”,末尾有“研读参考”,都是为帮助深入理解。词句的注求详尽,为的是自学也不会有困难。这样编,主观愿望是:认真读完这三册,就会获得阅读一般文言作品的能力,这是发挥了饮食的作用;读完这三册,有了读文言典籍的兴趣,还想多读,就会知道读什么,如何读,这是发挥了引线的作用。设想成熟,领导编辑室工作的人没有不同意见,以后的工作就由我全权处理。先组班,约三个人参加:我的大学同班李耀宗(年岁略小于我,原在某中学教语文,已退休),我的知交张铁铮(小于我近二十岁,在北京师范学院教书),我的同事潘仲茗(女,小于我超过二十岁,曾助我编《古代散文选》下册,还在编高中语文课本)。人选定,编的工作开始。排在最前的是选篇目,原拟用民主的方式,都推荐,然后协商。试行,迟迟不能进展。不得已,改为我选定,由他们三位复核的办法。显然,这选定,之前就要翻大量的书。翻检,有难易,大致是习见(义为选本上常见)的人(如苏轼)和习见的书(如《论语》)容易,不习见的人(如李慈铭)和不习见的书(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不容易,因为要到大海里去捞针。还想兼顾自己(对文章好坏)的看法和传统所谓名篇,比如选“笑话”是求选材面广,选诗话、词话、笔记之类是觉得比重气势、内容平庸的古文好,选王荆公的《读孟尝君传》,只因为它是传统的名篇,而在“解说”中点明,文章有严重的缺点。如此,我选定篇目,交他们三位复核,他们,也许是乐得坐享其成吧,很少表示修改意见。其后是分篇目去做。有编散文选的经验,“解说”,与其分别起草,交我统一整理,反而不如我一个人写省事,于是由我一个人包。不久,觉得“段落大意”和“研读参考”也以走这条路为好,于是也由我一个人包,结果他们三位就只管注解,注完交回来,由我修补定稿。工作程序上了轨道,按部就班往前走,计由1980年晚期上路,到1984年中期第三册完成,用了将近四年,这项工作才算结束。三本书,由效果方面看,应如何评价呢?内举不避亲,当仁不让,视同药方,自信开得不坏,是用作学习文言的课外读物,或扩大,用作学习文言的自学读本,至少在当时,是最合用的。但计算效果,又不能不管服用后的情况,而这后,之前,还有肯服用不肯服用的问题。有多少人,甚至有没有人,照方吃药,结果就治好了病呢?也许只有天知道。但不问天而问人,我是怀疑主义者加悲观主义者,自己推想,恐怕情况是“可怜无补费精神”吧?
《流年碎影》 有关文言的工作(2)
记得这《文言文选读》第三册完稿是1984年5月,我命定不能享清福,又没有兴趣加入编语文课本的行列,就想还是单干,对付文言,已编的散文选,选读,所供应都是感性的,无妨再编一种,供应理性的,即讲文言的字、词、句等方面的知识,以求化偏为全。有了设想,立即施行,先定名为《文言常识》,然后考虑包括哪些内容,某一项内容请什么人执笔。正在考虑,想举步而尚未举步的时候,即5月之后的一个月,吕叔湘先生来找我,问我手头有什么工作。我说《文言文选读》刚编完,还想编《文言常识》。他说选读完了就好,他有编书的打算,考虑的结果,以为我合适,希望我帮他先编这一本。以吕先生同我和社里的关系,只要力所能及,我只能照办。工作是编《文言读本续编》。很明显,称为“续”,是前面还有《文言读本》。而《文言读本》还有前身,是40年代朱自清、叶圣陶、吕叔湘合编的《开明文言读本》。这读本,“原来计划编成六册一套,供高中三年教学之用,但是只编了三册,没有完成计划。”(《文言读本》前言)这三册,应上海教育出版社的要求,于1978年改编为一册,名《文言读本》,于1980年出版。因为前言里提到原计划是六册,于是有人,以及出版社,就愿意把有名无实的后三册也合并为一册出版,以完成三十年前六册一套的计划。推想叶圣陶先生和吕叔湘先生(朱自清先生早已作古)是有兴趣完成开明书店的未竟之业的,“可是圣陶先生年高体弱,我(吕叔湘先生)又杂务缠身,踌躇许久,终于征得张中行同志的同意,担任这个续编的编辑工作。”(《文言读本续编》前言)我同意了,之后是着手编。规格照《文言读本》,有不少项目,如选文之外都包括什么花样,排印用繁体字,等等,就不必考虑。选篇目是大计,主要由吕先生决定。选编的目光与常见不同,比如选《大唐西域记》和《汉书·食货志》之类,以及有些篇不加标点,一般选本就决不会这样;连我这喜欢“攻乎异端”的也担心过于难,怕读者没兴趣。我向吕先生表示了我的担心,吕先生像是未思索,就说了一句使我深受教益、终身不忘的话:“学文言就不该怕难、只图兴趣。”所谓受教益,是这一句的“文言”可以换为“什么”,照做,就必不会一事无成。但吕先生还是尊重我的意见,把原定不加标点的篇目减去一些。以后就动手起草。考虑全书用繁体字,竖排,如果还要抄清,一则找人不容易(青壮年不行),二则还要校,费事,不如起草时谨慎一些,一次就成稿。这样一篇一篇往下写,选文一般要加标点,分段,其后有三项,是“作者及篇题”、“音义”和“讨论”,当然也要一点一滴地拼凑;不加标点的,我的私心是也分段,音义略详些,以减少困难。有的篇目,如诗、词、骈文,后面还讲了些有关文体的知识,如“骈体略说”、“词体略说”之类。总的说,工作不容易,连写字都要时时注意,以防不小心就会出现简体。最大的困难仍是“音义”(即注解)部分,因为吕先生古典方面底子厚,见识高,专说选篇目就不同于常,也就是选了些向来没有人注过的。我旧学底子不厚加荒疏,自然,有时就会遇见典实之类,应注明出处而不知其出处(都是《辞源》《辞海》之类辞书不收的)。这就要到大海中去捞针,捞而不得就不能不起急。仅举一次的起急为例,第三十四课选了苏轼的《国学秋试策问》,其中说到“隋文之传餐”,依注解体例应注明出处,可是查《隋书·文帝本纪》,查《隋唐嘉话》之类笔记,都没有,不得已,翻最大的类书《古今图书集成》,看帝王的勤政部分,还是没有。怎么办?这条空着,交吕先生?那就太惭愧了。算我走运,正在对书兴叹,无意中往下翻两页,居然就竟日寻不得,有时还自来,原来见于《唐书·太宗本纪》,唐太宗问房玄龄等“隋文帝何等主”,房玄龄等答话中有“传飧而食”。计起草这本书共费时九个月,单是这一条就用了两天半。完稿,交,吕先生修整一遍,发稿,可能已是1985年的年底。排印也是如老牛车,直到1988年才出版。也应该说说效果,有理想和实际两个方面。就理想一个方面说,专说篇目,看看就可以开阔眼界,知道学文言,可读应读的不只《捕蛇者说》《项脊轩志》那样寥寥几篇。更重要的是学的方法,是可以认知甚至学会,不怕碰硬的。行文方面也值得借鉴,以注解为例,我看是可以说句狂妄的话,已经到了“文不加(添字)点(减字)”的地步。但转而看实际的一面,情况就会由如意变为不如意,因为单是看印数,5000册,不再印,就可以知道,也许竟没有人有兴趣,至少是有胆量,拿起这根硬骨头,啃而又啃的。
《文言读本续编》是岔出去的一笔,交稿之后,当然要回到正文,编心中略已有成竹的《文言常识》。编这本书,目的有二:一是介绍一些有关文言的各方面的知识,以帮助学文言的人加深对文言的认识;二是扫除学文言的路上会碰到的障碍。要求比较奢,内容就不能少,又准备讲的知识,性质都近于专,编写,就宜于用集腋成裘的方式,即某一方面的知识,请这一方面的专家执笔介绍。而专家,几乎都忙,有的还难求,所以内容以目录的形式确定之后,约稿就成为繁重的工作。为了表示尊重,常常要登门,有的人还不只一次。最后,章章节节,找的人都点头了,还有两个困难,一小一大,不能躲。一个小的,人之惯于抓紧与放松,亦如其面,有的答应了,可是迟迟不交稿,就既要催,又要等。另一个大的,稿交来,也许与要求不尽合,甚至大不合,就不得不动手改,甚至改约人写。举实例说,约陈遵妫老先生及其助手湛穗丰女士写的“天文历法”,陈起草、湛修改之后交来,四万多字,内容过于繁,有些地方还过于深,超过常识,我只得动笔,改为两万字出头,化难为易。又如讲文体的“时尚”,要求介绍历代文体兴衰的情况,原由隋树森先生执笔,稿交来,内容过于单薄,不合用,只好改约冯钟芸女士写。稿齐了,内容,行文风格,还有化多歧为大体一致的问题,总之都要费心思和精力。但心思和精力不白费,书稿终于完成,发出去,于1988年由本社出版。这本书,以戏剧为喻,戏码硬,字、词、句、篇等之外,还包括文言的历史、典籍、文体、辞章以及天文、地理、职官、称谓等方面的内容;名角多,如吕叔湘、周祖谟、周振甫、陈遵妫、王泗原等都出场了。反应像是也不坏,出版不很久,香港和台湾就印了繁体字本。
最后还要说一种也可以算作有关文言的书,是《文言和白话》。如书名所示,是想画两者的形貌以及讲讲其分别和关系。何以要写这样一本?是友人吕冀平(其时在黑龙江大学中文系任教)应黑龙江人民出版社之约,主编一套《汉语知识丛书》。人所共知,丛书主编的地位有如坐轿,选题确定之后,诸友人就要自告奋勇(或应召)去抬。我收到选题,来信说希望我写文言部分的“词汇”。我生性不愿走熟路,抄现成的,看文言部分的选题,第一名是“文言和白话”,觉得其中可谈的不少,问题不少且不小,无妨试试,就认购了这个。记得认购相当早,因为手头工作多而杂,直到1985年后期才动手写,1986年中期完稿。丛书原定一册十万字上下,我把想谈的都谈了,结果字数超出约一倍。事有凑巧,丛书出一些,销路冷淡,出版社化积极为消极,我这一本干脆不入丛书,单行,于1988年出版。写这本书,借了几年来与文言多有交往的光,借了语言研究所吕叔湘先生和刘坚先生都碰过白话问题的光,但用的力也不少。还费过大力,是写“文白的界限”那一章,应注意的材料很多,而结论呢,说有界限,会看到不少骑墙派,说无界限,连这个书名也就无立足之地了。这一章写了五节,问题未必能圆满解决,却得了些与难问题沙场上周旋的快乐。自认为还有一得,是讲白话部分的末尾,我不避自大之嫌,提出现在执笔,应该用什么样的语言的问题,并表明自己的态度是“依傍口语”。在许多事情上,我常常苦于自信心不足,惟有在这方面是例外,过去是,现在是,推想将来还是,在书面语言的“像话”与“不像话”之间,我是坚决站在像话一边的。
《流年碎影》 有关文言的工作(3)
此外,谈有关文言的工作,还要提及一篇文章,是《关于学文言》。建国以后,语文课大体上还是继承传统,中学语文教材里既有白话,又有文言。学文言,要求是,比如高中毕业,能够读浅近的文言作品。事实是没有做到,又因为写现代文也是大多不通,于是有的人(而且多数是语文工作者)就把怨恨之箭射向文言,具体主张是中学生不再读文言。可是也有人主张应该读一些文言,又传统的力量太大,所以尽管有人喊,语文课本里还是编入文言教材。多数学生也头疼,实况又确是学不好,而仍在学,显然就成为问题。语文报刊上谈论这问题的不少,我的私见,都不免片面。于是想用由英国薛知微教授那里学来的“分析”的方法,谈谈这个问题。计由“文言典籍的长短”到“为个人想想”,共谈了十四个方面(1984年8月写完,刊于1985年7月出版的《语文论集》〔一〕)。分析,结果必是讲理多而主张少。但也可以看做有主张,那是文章末尾总结性的几句话:
有关学文言的话说了不少,可以总结一下了。这很简单,是:(1)文言是很有用但不是非用不可的工具。(2)就国家说,应该使任何人都有学会文言的机会,但同时容许任何人有不学的自由。(3)就个人说,学不学要看各种条件,这是说可以不学,但有学会的机会而不利用,总是个不小的损失。
到目前,事已过去十几年,想了想,有关学文言的问题,我的意见还是没有变。
明眼的读者可以看到,对于文言,我是倾向于学会有好处的。因为有此倾向性,十几年来,上班业余,为了供应读物,我费的精力不算少。可是,也许可以算作遗憾吧,想做的并没有做完。那是想再编两本,只是因为自知已无此精力,不得不忍痛放弃。一本是《文言文选读》第四册,性质是“高级”的文言读本,收《易经·系辞》《庄子·天下》《史记·货殖列传》之类的文章,以备学文言的人食欲增强,啃完一般选本不饱,可以尝尝这一本,而如果也啃了,就可以说是如游五岳归来,见大山也不以为高了吧?另一本是《历代骈体文选读》。我一直认为,文由散而骈,是汉语求美的自然趋势,有流弊是弊,但求美并不错。而所求得,成为骈体(指通篇对仗),或只是骈句,我们读,确是有散句所不具有的美。学文言,单是为欣赏,也应该念念骈体。过去骈体选本,大多取中古而舍近代,其实,如清代,作骈体的名家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