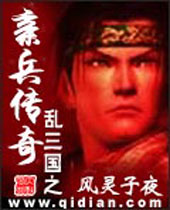花间辞倾国之折桂令-第5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给各殿的公主和皇子。前些时日,太子殿下唤了我去交我保管这苦儿草,曾言道,此物是要送给一个朋友。如今已深冬了,殿下目前的朋友也止太傅一人,青艾私下揣测,怕是殿下知道太傅畏寒,又不好意思直接给您,就故意让我保管着以备太傅不时之需,所以青艾今日私下做主,将苦儿草拿出来了。这手炉原是殿下幼时用的,多年不使,我料便给太傅使使,殿下也不会在意的。”景之听了,心下感激,对了青艾作了个揖,笑道:“如此,多谢青艾妹妹了!”说完,欢欢喜喜地走开。望着景之的背影,青艾涨红了脸,心中又羞又喜,暗忖道:“这杜太傅年纪轻轻便已身居高位,难得的是不骄不躁,温文而雅,人又生的俊俏,若哪个女子可嫁得他,真真是三世修来的福气呢。”又忖道:“只可惜自己容姿平庸,又只是一个小小的宫女,虽然聪明伶俐,总不会入他的眼的。便若能得一个像他一样的哥哥,就是即时死了,也无憾了。”想到此,青艾叹了口气,转身回屋了。
“杜太傅!”刚行到坡脚,景之便见崇义远远地从亭中跑来。崇义穿了件大红的金丝绣龙的雪氅,氅边围着一圈雪鹅绒,更显得崇义小脸齿白唇红,映着漫天飞雪,煞是好看。崇义奔至景之身前,执起景之的手笑道:“太傅,许久不见了,近日在四哥宫中住得可好?”景之点头,心中却浮起梦境中的事,不觉又羞又惭,又不便说与人知,只得含糊答应。崇义见了,心中暗笑,并不表露出来,执着景之的手边走边问道:“太傅,今日雪下得好大,你自小住在江南,可曾见过雪么?”景之答:“见是见过的,江南虽暖,每年总会有一二场,只不过不比北方声势,便是下了,也是细细微微,着地即化,纵积得少许,看上去也是脏脏的,不及这里好看。”“喔——”崇义眼珠转了转,忽又问道:“自你搬入紫辰宫后,我四哥对你可有越礼之处?”景之羞红了脸,待要不答又觉不妥,只得结结巴巴地回道:“并、并无。”“哦?”崇义挑起眉望着景之说道:“这可奇了,原来四哥不是粘你粘得紧吗?怎的就转性了,莫不是他对你不感兴趣了?”景之心中怦怦乱跳,挣脱了崇义的手,嗔道:“我又如何知晓。只盼着太子殿下莫再兴什么怪念头才好。”“怪吗?可是我觉得四哥是真心喜欢你的呀!”崇义皱了皱眉。“殿、殿下!”景之急道:“太子是千金之躯,日后担负国家大任,幼读孔孟当知礼廉耻,怎可有龙阳之癖,岂不让天下万民耻笑。”崇义撇撇嘴,心中大不以为然。景之激愤之余,脚下一个趔趄,差点摔倒,幸有崇义扶着。崇义细看景之脸色,不由问道:“太傅近来身体不适吗?怎的脸色如此难看?”景之手抚心口,皱眉道:“并无大碍,只是近日睡得不好。”“喔?怎么说?”“不知怎么,这几日夜夜做梦,梦醒总是四肢无力,睡眠不足,所以身体有些困乏。”“做梦?什么梦?”景之哑然,忽涨红了脸,半天不答。崇义眼中精光一闪,心念急转,笑道:“太傅莫忧,我有良方可治你的多梦,只要你照我说的做,包你药到病除。”景之大喜,忙作了个揖道:“微臣在此先谢过殿下。”崇义心中大笑,暗道:四哥呀四哥,你这回可又撞到我手了。
这能行吗?杜景之满腹狐疑,看着手中的玉枕,想起崇义的嘱咐。且试试吧。叹了口气,杜景之吹熄灯火,枕将上去。玉枕散发出一股清香之气,让人神思清明,躺在床上许久,竟无一丝困意。景之暗暗称奇,崇义只说此枕可医多梦之症,却不料枕了上去竟了无睡意。景之苦笑着想,若不睡,便无梦,这样说来,此枕倒也的确有效。未几,闻得钟楼打了三更,景之闭上双目以养神。忽然,一阵异香传来,景之微睁双目,借着月光,见到一缕清烟从窗缝里飘来。刚想叫,却赫然发现,四肢无法活动,话也说不出来了,只有头脑还异常清楚,眼睛也可微微张开。景之吓得魂不附身,急切之中,眼泪又流了出来。只听得门栓轻动,一个白影施施然走了进来。借着月光,景之勉力将眼睛睁开一条细缝,见崇恩身披棉袍,走到床前。崇恩在床前的火盆前加了几块木炭,火苗窜起,给房中凭添几许暖意。立起身,崇恩定定地望着景之。借着月光,可以清晰地看到景之苍白清丽的面容,乌黑的长发解开,披散在床沿,淡色的双唇微微开启,星眸半闭,只有胸前的棉被随着呼吸上下微伏,模样儿极是诱人。崇恩神魂俱荡,将手伸入被中,开始解景之身着的中衣。景之苦于无法开口,又动弹不得,连发抖都成了奢侈之事,只好眼睁睁地见崇恩胡来。不多时,景之身上的衣物已尽褪,崇恩也除去身上衣物,钻入被中。二人身体赤裸裸地相触,细致的肌肤相触的感觉让崇恩发出一声叹息,让景之羞得恨不得立时撞墙死去。崇恩的手游走于景之全身光洁的肌肤上,炽热的唇吻向景之,强烈的男子气息直入景之鼻翼,温暖湿润的唇舌在他脸上逡巡,以手扳开他的下巴,灵巧的舌钻入景之口中,舔遍所有内壁。景之又羞又气,直想昏死过去,却偏偏意识更加清明,又因看不见崇恩动作,而感觉益加敏锐。崇恩唇舌渐行渐下,张口含住了景之白皙的喉结。一阵酥麻的感觉让景之心神一荡,心跳不禁急促起来。崇恩舔遍景之的每一寸肌肤,在每个薄弱之处狠狠进攻,景之虽不能动,但欲望的热流已渐渐汇集,四处流窜。崇恩张口咬住景之胸前的诱人茱萸,舔咬磨转,使尽浑身解数。一只手向下握住已抬头的敏感之处,另一只手揉捏胸前的另一处。景之此时羞愤之情已不见踪影,只余全身热望喧嚣的呐喊,本发不出声的口中竟逸出柔媚的娇吟,两腿之间也益渐胀大。崇恩见此情景,心中大喜,反身跨在景之身上,将景之檀口扳开,把自己早已勃然欲发的巨大阳物塞入他口中。柔湿软暖的口腔内壁让崇恩兴奋得浑身发抖,就着这个姿势,他将景之的勃起也纳入口中,以舌勾勒描绘,舔舐含转,同时腰间使力,就在景之口中抽插起来。景之心中戚苦,泪如泉涌,只得紧闭双眼,任强烈的膻腥气味充斥鼻间。崇恩的阳物极大,将景之小口塞得满满的,每抽送一下都磨着景之的舌面,直抵他的喉口,让景之痛苦万状。上面的小嘴虽饱受折磨,下面却受到崇恩的温柔呵护,痛苦与快乐在景之身内交战,真叫人生不如死。崇恩的阳物还在嘴中动着,越动越快,越动越激烈,阳物下面垂着的两颗不停打在景之的脸上,发出啪啪的淫靡之音,浓密的阴毛磨擦着下颌及柔颈,让景之觉得有些刺痛。突然,崇恩将阳物拔出,一阵剧烈的颤动之后,一股股灼热喷洒在景之的胸前。景之正羞愤之时,身体里的欲望随之喷射而出,全进了崇恩嘴里。崇恩将热液一饮而下,又细细地舔尽了每一处地方,从柔嫩的前端小口,到疲软的玉茎,又舔了舔下垂的两颗圆袋,最后竟来到最隐密的花园口,景之吓得心几欲从口中跳出,手脚冰冷,身体却只能任崇恩摆弄。舌尖在花口旋转刺探了半天,崇恩的手指悄悄爬了上来,指尖抵在花口上半天却迟疑着不肯入内。良久,崇恩叹息了一声,自语道:“若是真做了,只怕明日你必会察觉了,罢了,且放过你罢,每日如此,对我真是煎熬啊。”说着,将早已重振旗鼓的巨物放在景之两腿之间,叹道:“也只有此聊慰我心罢了!”言毕,将景之双腿并拢举起,置阳物于腿根柔嫩的内侧之间开始大动。动得三四百下,精液四溅,洒在了景之的胸腹之上。喘息片刻,崇恩穿上衣物,步出房门。只听得门外低语几声,不多时,崇恩端了一个面盆进来,温暖湿润的感觉覆上了景之的身体,原来是崇恩拿了面巾,用温水在给他擦拭身体。身体拭净后,崇恩又给景之着衣,盖上棉被,“你真是爱哭啊,梦中也要流泪么?”崇恩吻了吻满面泪痕的景之,收拾妥当后悄悄离去。这一夜,景之动也不能动,流着泪等到了天晓。
“杜太傅!”一大早,崇义就诡笑着来到景之房中,看着呆呆坐在床上的景之一眼,崇义笑得好不开心,大眼睛闪动着算计的光芒眨啊眨的,问道:“怎么样,我的美人儿太傅,你的病治好了吧!”景之看着窗外,泪水爬满两腮,呜咽了半晌,突然开口:“殿下,帮我!”“帮什么?”崇义好整以暇在桌旁,自己倒了一杯茶。景之咬了咬牙,一头拜倒在地:“殿下,我想离开,离开皇宫,离开京城!”崇义啜了一口茶,笑得眼都要眯起来了,扶起景之道:“太傅要走么?那我就帮帮你吧!”
折桂令 6清夜帐暖
水调数声持酒听。午醉醒来愁未醒。送春春去几时回,临晚镜。伤流景。往事后期空记省。
沙上并禽池上暝。云破月来花弄影。重重帘幕密遮镫,风不定。人初静。明日落红应满径。
偏僻的宫门侧角,门“吱呀”一声启了半扇。门外早候了一辆马车,蓝布围遮,与平日街上所行并无二致。景之布衣素冠,伸头见宫外无人,举脚迈了出来。“如此,不远送了!”门内响起清朗的笑声。景之回转身形,向门内深深一揖道:“殿下此恩此德,景之没齿难忘。今生无缘再见,等来世变牛作马,当报殿下万一。”崇义吃吃一笑,掂起脚来,在景之耳边轻语道:“变牛作马要它作甚,来世我还是要你如此这般,方可报我。”景之红了脸,忙后退半步,躬身道:“殿下真爱拿景之开玩笑。时已不早,景之就此别过,宫内之事有劳殿下打点,景之自会在外自求夜祈,祝殿下身体康泰,福寿安康的。”再拜了拜,便转身上了车。崇义见马车远去,自笑了笑,双手抱胸道:“摩诃勒,你出来罢。”顿了顿,见无人应声,不觉皱了皱眉,大声道:“摩诃勒——”,耳边传来一丝微声:“殿下,时正白昼,臣不便现身。”“叫你出来你就出来,罗皂什么!”崇义嘴角微下,心中有些不快。沉寂一会儿,树叶微动,一个黑衣人便伏身在崇义身前。此人通体着墨,面上罩着一个白色面具,只余一对墨漆明瞳在外,其余再见不到半点肌肤。背后斜背着一把长剑,剑身微弯,约有四尺来长,形状极为古怪,腰侧佩着一把三寸短匕,身形纤长得体,长长的乌发只在脑后束成一束,在阳光下微微泛出幽蓝之光。崇义转怒为喜,伸身要去扶他,摩诃勒身形姿式未变,身体却突然向后飘了半尺。崇义呆了一呆,笑道:“如此见外做什么?我不过想扶你起来,又不是要去揭你面具。我可不想死在你的剑下哩。”摩诃勒依旧半伏于地,沉声道:“殿下何出此言,殿下既是主人的公子,倘若殿下真将臣面具除下,臣也不能伤殿下半分。”“真得?”崇义目现精光,正欲雀跃一试,又闻得摩诃勒淡淡道:“只不过臣必自毁容貌后自戕以完承诺。”崇义瞪目结舌,半晌方笑道:“罢了,我收了此心便是。唤你现身,是有要事需托你完成,你且附耳过来。”崇义在摩诃勒耳边叽叽咕咕了半天方才住嘴。摩诃勒惊道:“殿下,此事不可!岂不是要害了太傅!”崇义道:“有何不可,我既让你去做,自有我的道理,你只管照我说的去做就是。”摩诃勒沉吟半晌摇头道:“此事臣做不出来,殿下另派人罢!”崇义佯怒道:“大胆,你竟敢不听我的吩咐。既如此,我也不敢要你,明日我自去与母妃说,把你还给了她,让你回到长川秀一先生那里去好了。”摩诃勒听了,身体一颤,后退了两步,低下头来颤声道:“殿下莫恼,臣即刻便去就是了。”言未尽,身体已在数丈之外。崇义转身掩上宫门,不觉大笑数声,扬长而去。行到紫辰宫附近,缓下脚步,对了,四哥自今日起,随父皇拜谒太庙去了,十日之内必无法回来,摸了摸怀中的奏折,崇义诡笑了几声。冷眼瞧见走过一名小太监,便挥手招他过来,那小太监也就十二三岁,与崇义年纪相当,见崇义唤,吓得体似筛糠,话也说不出半句。上下瞧了瞧,崇义问:“你是哪个宫里的?”小太监张了张嘴,却半个字也说不上来。崇义不觉皱了眉头,问道:“是紫辰宫的吗?”小太监忙点头。“太子身边的?”小太监摇了摇头。“洒扫的?”又摇头。“有伺候的主子?”点头。“不是太子?”点头。“但在紫辰宫?”点头。“名字!”“太、太、太、太傅。”崇义叹了口气,从怀中取出景之留下的辞官奏章,塞入小太监怀里道:“去,放到太子书房,不许任何人看到,不许跟任何人讲,如有半点差池,我就把你调我宫里。滚罢!”小太监如蒙大赦,连滚带爬地去了。崇义伸了伸腰道:“好累!母妃现下没有父皇陪伴,想是无聊得紧,反正我现在也没人陪了,便去找母妃吧,说不定还可抱上一抱。”一思及此,崇义不觉心中大乐,足下生风,往雪樱阁去了。
时过正午,景之悠悠醒转,听见屋外鸟鸣虫啼,便披衣下床,步出房门。自出得宫来,算算已有三月光景,寒冬已过,如今早已是春暖花开的时节了。因怕崇恩来寻,景之听了崇义的安排,住进了崇义在京郊外的别馆。想来崇恩见自己辞官不见,必是以为南下回归故土,一路找下去了,谁会想到实则自己就在京城脚下隐居呢。崇义言道:“危伏于安。”果不其然,真是最危险的地方其实最安全。只是崇恩也未见得便真会寻自己,说不定又找见了新人玩弄了吧。想着,景之心头一缩,既酸又痛,眼中湿润起来。我这是怎么啦?景之心中一惊,离开崇恩应是欢喜之事,却为何心中如此难过?莫非……。别馆内,黄花遍地,白柳横坡。枝头绿叶葱葱,疏林如画。西风乍紧,暖日当暄。景之心如鹿撞,神思俱废,手抚着胸口竟呆住了。
“先生、先生!”声声娇啼让景之恍然回神,见女侍绿萼向自己跑来。绿萼年纪也就十五六岁,容颜娇憨,一派天真烂漫,景之是极喜爱她的。见她跑来,不觉笑道:“萼儿慢些,当心摔着了。”“不妨事的,只是先生身上衣衫单薄,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