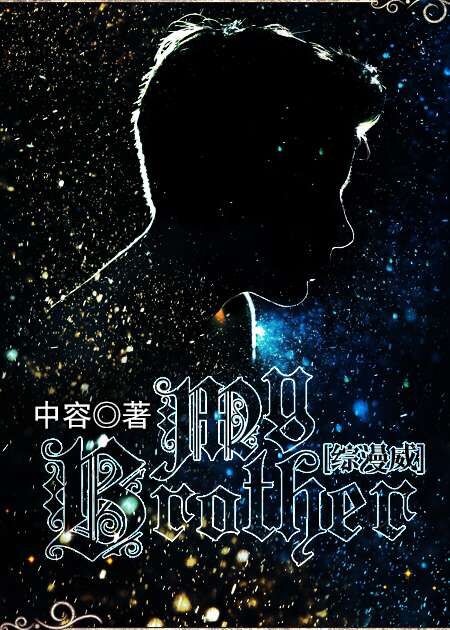���� �� by����-��2����
�������Ϸ���� �� �� �� �ɿ������·�ҳ���������ϵ� Enter ���ɻص�����Ŀ¼ҳ���������Ϸ���� �� �ɻص���ҳ������
��������δ�Ķ��ꣿ������ǩ�ѱ��´μ����Ķ���
�Բٳֹ��������Ұ������Լ��Ľ�����ѡ���ˣ����������ǻʵ۵���˼�����ֻ��Ƶ����Σ�Ҳ�Ǻ���Ե�ɡ������ǻ�̫���ֶ�ӣ�����̫��һ�ң��ڳ��м���ռ������������֮λ������Ϊ���߾��ˣ�Ϊ��˾�������ˣ�Ȩ�����һ�ţ�����֮ʢ�����˺���������֮�⣬�ɱ��ס�������ʱ�е����⣬�������ӣ�û����Ȩ������ʲ������Ϊ����Ц�ģ�����ʵ����Լ�������
�������϶����־����ƺ����������ÿ�춼������Ƶġ�ֱ��ij���˳�֮�ᣬһ��ƽ�͵����׳��ֳ���֮ɫ���̴����Ե������������������ϵ�����������ç�������
�������ϸ��Ӳ��ã�����˵����û��û�����Ҳ�����ټ�����ç����
������ç������������֮���˵��һͨ���ͳ���ԶС�˵ĵ��������ϲ��ͷ����ʸ�ƽ����С�ˣ����ԾͲ����뾩���ݸ�ĸ�ɣ����ֵ�������������δ�ţ���
������çһ�������������ǵģ����ǡ�����
�������ˣ�������Ц�������̫��һ�����������ȥ����̫��˵������ƽ���ŷŽ��������ˡ���
���������������çл������֮�ᣬ���Ͼ�����������У�һ�ﲻ�����������������������Աߡ���
�����Ǽ�����϶�����������������˼�������ᣬ�̼�����֮�ʣ����̴Ҵ��ϵ����һ�����࣬����һ����ӡ��æ����ȡ�˲��ģ������������ּ����÷�������
�������������ϵķ�ӡ����ˮ������ξӡ��Ҳ���Ǹ�ƽ���ŷš���ǰû��˵��������֣�����Ӱ��������ϲ�������Ǻ�������������
������������̫��������ֹ���������Ƿ����࣬������Ҳ�������˳��ϵġ���ƽ�����������˼������࣬���ϲ��ٻظ���ֻ��ÿ�ζ������������˼��ա���һ�βŶ������������ŵ�����˵������ƽ������ʲ��ݱ��Ļ������������ֻ��Ȩ��ת�ư��ˣ���
�������ο������ϲ�������¶�ļ�į�����������ﻯΪͬ�顣��
�������ϵ�����Խ��Խ��������������������ˡ���̫�������ҵ���������ɽ�����ˣ�����͢ξ���������ӵ�����������Ǹ��׳գ����ҵľ���δ�Ⱪ¶��̫�����ԣ�������춲���һ�е���ʽ�������������Ϊ̫�ӡ���
�����������������ƴǣ�����ֻ�������������š��֣�����˵ʲ�ᡣ��������گ������֮��Ϊ����������ά����������𡣡�
���������빬��лʱ�������Ȼ����ŭ�ݣ��ʵ���лʲ���
���������Ȼ�����ϵ��������Ϊ���ӣ����������ѪԵ���Ѷϣ������ʫ�飬�����ڵĴ�����Ϳ���𣿡�
���������ʲ����Լٶ��������������ƴDZ����ϴ�ϣ�������ס�������֣�̾���������������ޣ������ж�յľ��£��ޡ�����
��������ͣ����һ�£�����ǧ�������֪�Ӻ�˵����į��һЦ����������������빧����ͬ�����ã�����;�������̳л�λ��������ܸɣ�һ�����츣���ա���
��������˵ʲ�ᣬ�������Ƶ�Ц�������Ϊ֮�ɣ������������ȥ����
������������ʮ����׳��ݱ�����̫�����������Է���ʺ���ã��������̰�Ϊة�࣬���������ڿ�����ԭ�����û��һ���˻�Ϊ���ϵ�Ӣ���������ġ����������ĺ����Լ��أ����������ߵ����ݣ�������������ӣ��ִ���ʲ��˾�ƫ��Ϊ�������飬ż�����λؾ���֮�ʣ������ıڣ��ĵ���������ɬ��ãȻ����
������ˮ���Dzʹ�ڽ����ˡ�������������ɥ�����ټ�ʹ�ڣ�һ�ж��ɴ�˾����ç��������ƽ���ŷ�Ҳ���������˰ɣ�ʬ��δ����������ç�౨�����£���������ϸ�����������ǻ�̫����������ּܲ����ɥ�ڹ��ˣ��Լ�������ʽ�����ӡ���
����������ƽ���ŷŰ������ȶ���������
��������һ������ç�����ˮ�������ã��˳���֮����
����������������˵��ƽ�����������
�����������ȶ�������çƽ������˵һ�飬�䵭������˵һֻ���ϡ���
�����������Լ��δ�����λ����
������ʮ������ç�������
����������Ȼ���á��ڻ�̫����������ּ���£�������ˮ������ƽ���Ҳ�����⣬���������������Ա�������һ�У�������ֻ�ǿ�����������ŷŵ��³�����
��������ز�ã�������������峿�����ĵ����±����գ����ݻ��������ʵ۵��������ˣ���һ��ƽ��֮�䣬���������ʵ�ССϼ�⣬��컪�Dz��ư������������ȵij�������Ϯ�������ϵġ������֣����Ի���������������������ڸ��������ּ������������
�������������Ƹ߾���ü����������棬���Ὣһ���������أ���ʽ��λΪ����ʮ���λʵۡ���
�������꣬������ʮ�꣬ʷ��Т���ۡ���
���䡡�ڶ��¡�����ޱ��
�������ӣ�����������������˼����ѩ��������
�е��ٳ٣��ؿ��ؼ��������˱���Ī֪�Ұ�����
��������������������������������������������������С�š�ʫ����
����������λ����һ�꣬ƽ���ij�͢�����µı߾��������������ֵ��ԡ���
�������Ժϵ���ɱ����Ϣ��������̫����������ͬʱ��������
������������λ̫���еľ��棬�ֱ���̫��̫������������̫̫���ϡ���̫���Է����Լ���̫�����ȵ���ŵ���Ļ��Ҳ����֮�С���̫��һ�����������Ѳ�������Ұ���ң��ȵ۱��У��Ժϵ���ѳ���Ծ����Ͳ�����ǣ���Է���ʺ������ԹԵص�ͷ����̫��п���˵�Իʺ����ٶ����ӣ������缺������ʹ����̴��ڣ���Ҫ��ĸ��֮��Դ�����
����������ĸ�����أ�����û�ʣ�Ҳ�������б�Ҫ�ʡ���
����Ψһ�������������ǣ�̫��̫������������ȡ����ĸ�ĵ�λ�������Լ������Ź���İ�����ϵ��ϸ�����ТԪ�ʵ۵����������Թ������Ϊ�楶��ܳ�ĸ�̫���Լ�������������͢�������յ�צ������춳��Ź���������η��֮�⣬��Ũ�����������
��������̫�����δ�빬��������������Ҫ������ĸס�ڹ���ʱ����̫����Į����Զ�������������
������������һ��֮������������飬����������������
����̫�ݣ��������������������ڿտ��Ĺ��С������Ͽհ�گ��ͱʣ��ƺ��Ը߰�����̬��Ц��������
�����ǵģ�һ��֮�������������ᵱȨ��һ��֮�������Լ��������ᶨ�˾��ģ���һ��گ�飬��Ҫ���Լ�����˼�죡��
����������������Ȼ�����Ǽ�춴�˾����ç����������ʦ����ة���ļ������ԣ��ڳ����������ţ�������̴��ڣ�ѪԵ֮���Ӧն�ϣ��������ڼҷ������ɷϣ����ǣ��Դ�˾�պ���Ϊ�ij����ǣ�ȴ���븵̫���ס���У��ҷ�Ϊ��̫����Dz�ض��ա��߲�����������飺���������չ��ʺ�Ϊ��̫����������ç��ʦ�����ҷ�����ָ������治�����ҷ����ϡ���
����������û��������Լ���һ��گ�飬��������˫��������֮���صĶ����������˳�֮�ᣬ��������ҹ�����������������һ�е����ġ���̫��̫������������
���������У������ػ����µ�Ů�ˣ��������ij�����ТԪ�ʵ������Իʺ�����ݽ������ݵ�Ȩ��������ʺ������������ȵ۰��ŵĻ�����̫��ʱ����������׳֮������ã�żȻ�䣬������������һ�ȣ�����������㻳�����á��ȵ�ϲ�ã���������������Ϊ̫����������λ��������������Ȼ�س�Ϊ�ʺ��Dz����ܳ衣���û�й�ʧ�������裬��������˳������̫�ӣ������Ǵ�δ�˹��Ϻ����ͷ����ά�ֺ�λ��������Ҳ����һ�����صĿ��ģ��̳�ǫ�õ��ռ�Ŀ�ģ����ǰ�������˳����λ���ˡ���
����һ�������������������ĵص�����
������̫�ʺ��ѵ�ѪԵ֮�顢����֮����������ϣ�����
����������ֻ��Ц�������κλ�Ӧ����Ц�ݣ�����Ц����������ͽ���������̲�ס����һ������������
������֪����ν�����ǣ���֪����ν�Һ�����������ĸ��������������ĸ��������������Ը���²��ģ��ض��չ���������
�������������ݣ��������������Ѿ��ˣ�����
����������̫�ʺ����ڲ��⡣���������������
�������������ϣ������ڹ��У�����ʮ���أ��ü������棬Ҳ��Լ�Լ����ˡ��������������Ŀ����У��������ɵ����ֱ����������顣�������ٳ�δ�ã����Ҳ��ò������ԣ���֮͢�£��˲������ԣ���ʵ֮ʿ�˹��Ҷ���������Ӧ����֮����춹����س�����Ӧ���أ������������顣����
����������̻塣����
�������ȵ��ٱ�������ة���͵£��������䣬��λ�Ѿã����ְ������²��ܹ������ʡ�����
��������֪����������֮�⣬ֻ��ΨΨ����
���������������������ò�����گ����������Ϊ���ʣ���ˣ���̫��Ҳ����������˳���ɷ������̫����Ϊ��̫��ͬʱ������Ҳ�ó�һ�����ѹ���������ç�ĸ߲�����Ϊƽ��
�����Լ���λ���ã�������������֮����ȷʵ������Ҫ�㡣ֻҪ��ĸ��Э���Լ������в��������ҵ�һ�죡��
������
����ÿһ��ҹ��������Ϥ�˵Ĺ���©�̴����������į�ĸ�డ���
����һ�����ص���������Ȼ�������ţ�����������ס��Ҫ���������ݡ�����˵�Ǹ���ְ�����ɣ�������֮�ڣ��������ڡ���ʿ�̲��Ϸ��У�Ҫ�鿴��֤�����ܳ��빬͢�������첻����������ɽ�֤������
�������ڳ���Ƭ�̣�������һ�����������������������ƺͷ�ĺ����������������Ǹ��������������ˣ��빬ʱû˵Ҫ������������
���������еĴ����еĽ�������ʿ�������������ǾͲ��ܳ�����û��֤�����������ô�����֮�����
��������������Ҫ��ͷ�����ģ��������ľ����������е����������糣�ºͣ��ƺ���֪���Լ���Σ�մ����������һع����ˡ�����
�����������ô����ǣ����������𣿡���
���������ܳ�ȥ��Ҳ���ܻ�ȥ�����ʴ����Ҹ�������أ�������������ý���������ʵ�����
�������д˵Ȱ׳գ���Ȼ��ҪѺ�´��Ρ���ʿ��Ҫ������ٵĽŲ�������������������������һ��֤��������ǰ������
��������һ�ȣ���������Һá����ϣ����ˡ�������
�������ɵ��Ʒ��е����ң����嶼�ƺ�Ҫ��̫�����ܲ������飬��������ͣ�ڳ��ߣ������������ߴ��߰�֤��������ʿ����ʧ����ʧ�����Ÿգ������Ρ�������֤�����������������ؿڣ���ȥ��ˮ����
������лл���ˣ����ɹ١�����
���������������������ţ�һ��������Ц�ݣ���ûʲ�ᣬСС�ľ���֮�ͣ�������գ�����
������ʿ�������������ļ��ϵ����֡����͡����֣���ӳ������Ĺ�â������֤�������εص��������߰ɣ��´β����ˡ�����
�������������
�������廬��������һ���ö��������������ƴ�����ֻ��Ө���֣������»���۶��ɣ�����һĨ�����Ļ����������ӳ����Ӱ����ӵ�İ��棬��Ȼ��Цʹ��âʧɫ����ʿ�����ؿ����������ļ������·��³�����·��ֱ��������Զ���Բ��ҿ϶�������ת�������ò�����˵���������ɢ�����𣿺�Ӱ����ķ�ɫ���������ġ��¶������ǡ���
���������п����ᣬҡ���У���Ƥ���أ���֮�����������ظ�����ת����������
�������ͣ���
�����Ǻ��������Ϥ������������ĵף����ڲ������ʱ���˾��ؿڣ���������һ�㣬�������������ܡ���
�������ͣ���
��������һ��������۾���ĬĬ����������Ȼ�ľ�ɫ��Ϊ�����������ˣ���Ҫ����Щ���顣�������գ�һ���ϸ������⣬�ڽ���䱼�ܡ���
������������̤����ϡ��������������ˮ�����������۾�������Լ�����������춯������
�������ͣ���Ҫ�ߡ�����
������������ɴ���������½���������˫�峺���۾������ɵõ����ۣ�Ӳ����ҡͷ������������ʮ����̫�鷳���ǣ�������ȥ������У�����������ˡ���
���ֱ���ס����������һ�£������ţ�ҧ��ҧ��������ֻ�����ﻥ��������
����û���κ���������������Ц���ǣ����ں��������չ����ģ�������ǰ�ⲻ�ܾ����κ��µ��ˡ�ʮ��ǰ����������ĸ���Ͷ����ģ�������˵�������С����һ˲��������˿��������ꣻ�����������˵����Ҫ���ˣ��ﲻҪ���ˣ�����ȴ������˵�����Ļ�����ȥ��ɢ����ԭ�����赭д�����жϷθ��ĸ���������Ǻã���
�������ܡ�������������ڼ���Ѷ������ʡ���
����������õ����Ѻ����ѣ����ѿ�Ҫ���ǵ���ĸ�ĸ����������Լ���ȥ��ʮ�����IJ�����Ʈ��֮�У����������˿־壬��û������ȥ���û�мҵ�δ����ֻ�Ǻ��£�����˽��������ڼ���Լ���һǧ�������뿪���м���ȻҪ�أ��и�ĸ��ȻҪ�̷�ټ��ӵ�Ҳ���˲������ε������ˣ���������Ҫ��ʲ���ڣ���Ϊ�������Լ���Թ�ڵĺã�����춳�ʶ˵��ͨ�ġ��˵���У��ֵܵ�������ʵ����
������ڼĬĬ����͵���ָ����һ������С�ɵĺ�ɫ��з����������ģ�������ס�ˣ������Ǵ��֮�Ҳ��õ�����ݳ�Ʒ�������˶�õ�Ǯ�����µģ��ο�������Ư����ϸϸ�Ľ��߽�����ͼ�����ò���ʵ����
�������������㡣��ڼŬ��Ц��˵����֪��������һ�죬·�ϵ��ˣ����ͷʹ�ˣ�������ҩ�����ҩ��һ�ࡣ��
�������һ�Ӧ����һ���ھͻ�ġ����ڷ�������Ҳ��վ�����ˣ��뵹�������˵�Ҳ��ߣ����Ķ�Ҳ��ȥ�ˣ�ȴ����Ȼ�����˳�����ͷ������������һ���ƶ���˲�䣬����תѹ������Լ����ġ���
������һ��ȥ���㣡��ڼ��У�Ҫ���Ұ������͡�����
����������Ȼ���ѣ���
������ˮ��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