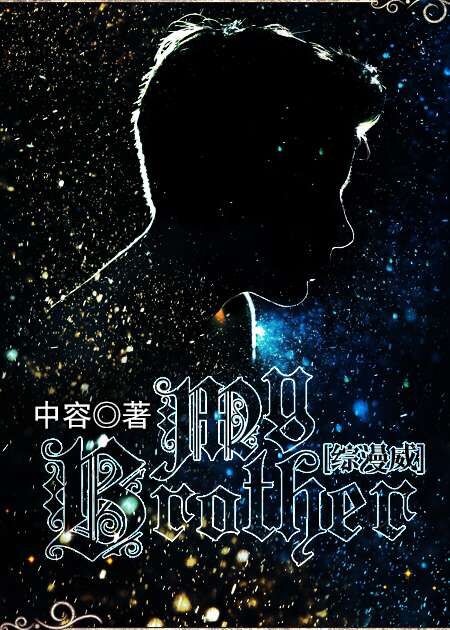丁香花 by devillived-第1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母亲是个第三者,自己是个私生子。
可笑,这么时髦的名词,居然会加在自己身上。从没有想过,这么白烂的桥段,会加诸在自己的身上!
小时候,在心中偷偷想过不下千遍,自己的父亲是一个大英雄,为了拯救世界或者别的什么伟大原因献出生命,或是伟大的船长,在世界边缘航海冒险;长大了,虽已不再拥有瑰丽的幻想,可无论如何都不曾想到会有今天这样的答案。
父亲并没有回来,甚至连母亲的形象也……
插在口袋里的右手紧紧拽着一张发黄的老照片,是那个男人,那个雨天曾经出现在教室里的男人,没错的,是他。
陈邱凌,他的父亲。
该怎么办呢,该怎么办呢?
君凌要自己去见他一面——他的父亲,在他死前。
胃癌是一种异常痛苦的疾病,它消磨人类的意志,却不让人轻易得到解脱。
而且不能告诉母亲。
不能告诉任何人。
三番五次的逃避,搬家,母亲一直都在躲避着,躲避着这段不应该存在的往事,躲避着陈邱凌。她那永远孤独的身影,原来一直以来都背负着这个沉重的十字架。
可是自己还是想要去见一见他。
纷乱的心中里不出任何头绪,唯一清晰的就是这个愿望。真是想要见一面,也许,现在犹豫一下,以后就再也没有这个机会了。
“怎么了?”
将丁翔带进屋内,李梓封觉得自己好像只是搬进了一件人形的雕塑,耐着性子询问半天,却什么回音都没有。
直觉告诉他一定有什么事发生了,就在今天的“同学会”上。
以及度人的第一反应,李梓封迅速扯开丁翔衬衫的领口——还好,没有看到任何不应该有的痕迹。
“你今天,不是去了同学会吧……”
缓缓地开口,用一种阴沉不悦的语调,李梓封讨厌欺骗,也从来没有人尝试过在他的面前欺瞒些什么。
这一次,终于有所反应,丁翔摇头。
果然不是。
在欺瞒着自己的情况下受到了伤害的话,并不值得同情吧。
李梓封自负地这样想道,在开始的某个瞬间甚至有一种扭曲的快意。
“告诉我,发生了什么。”
凝固了的少年,如同一株攀援植物, 紧紧依附在李梓封身边,同时也静默如同植物,始终没有吐出只言片语。紧紧拽着李梓封衣袖的那只手,已经完全失去了血色而变成淡青与苍白,那薄薄的表皮下显现出的淡蓝色血管中,流动着成分不再不明的血液。
“还是不说么?”
“……”
李梓封终于感受到了一点挫折。
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唯一可以肯定的就是,丁翔受到了极大的打击。而这件事,他不愿告诉自己,甚至不愿意告诉任何人。
李梓封第一次感觉到丁翔是个独立的个体。
无论自己如何让想要征服他,如何在心中将他当成自己的附属品,而实际上,丁翔的自我并没有被抹杀。虽然两人已经是如此亲密的关系,但是他依旧保留着自己的世界,秘密,也许就是他内心中最最坚强的那部分,也许自己永远都打不开的核心。至少用现在的方法不行。
他会在迷惘的时候寻求安慰,可是不会轻易将最后的心防交给任何人。
可就是这样,更加引起了李梓封的征服欲。
他看见了新的目标,无论那里面装的是什么,与自己有没有关系,他都想要突破看看,就算辛苦到手的东西自己其实一点都不感兴趣,也必须尝试一下,满足满足自己的好奇。
可是李梓封从不曾考虑过,突破那最后一道心防,会对一个人造成多大的打击。
在心中制定了新的目标,李梓封表面上的声情反而温和了下来,轻抚着丁翔的背,泛泛地说着“不要紧”。感觉像是在哄一个孩子,没有多久就发觉疲累了人沉沉睡倒在了自己怀中。
做了一夜噩梦的丁翔醒来的时候,是睡在李梓封那张舒适大床上的,放下的窗帘只隐隐筛来几缕阳光。
李梓封已经出去了,早餐的桌子上放着一把钥匙,还有一张纸条:
“the key to my alice”
那是李梓封留给丁翔的家门钥匙。
“thanks to my Queen of Hearts”
这样回复留言。亲吻了一下闪着银光的钥匙,丁翔露出今天的第一个微笑。
李梓封给了自己继续下去的勇气。虽然不能将这件事告诉别人知道,但是有一个人却是例外。
洛可可,少年侍应先在正以客人的身份坐在角落里。
他的名字叫做狄招袂,不要笑,当初他的父母是很严肃地想要他再招来一个妹妹的。
招袂是君凌的“好朋友”,这种“好”,好到足以知道丁翔的这点小秘密。昨天君凌让他回避其实只是不希望丁翔过于难堪。
“你应该去看看陈老先生的。”
招袂的声音很清脆,但是并不轻浮,一字一句很诚恳。
“就当满足一个老人的最后心愿。”
“……可是我怕去了,一切都会改变。”
“……其实改变也未必不是好事啊。”
“我只是有点舍不得现在的一些东西。”
“虽然不太明白,可是真正属于你的东西,是不会这么轻易离开你的。”
“也许犹豫不决是我的天性吧……”
想笑,牵动嘴角的肌肉,却凝固成一个惨兮兮的表情。
“那就去吧,虽然我希望这一切都只是一场梦。”
二十八章
见面的日子被定在了五月的第三天。
赶上了劳动节的公立假日,S城里来来往往的人也比平时多了不少。上午9点,丁翔等在了事先约好的地点。
对于自己五一期间的怪异安排,李梓封破天荒地没有任何极端反应,没有过多的询问,不满,或者是怀疑的言语——这反而让丁翔有些不安起来。
不过无论如何,现在已经来不及去仔细思考这些。因为君凌的黑色轿车稳稳地停靠在了他的面前。
车窗摇下来,让丁翔稍觉安慰的是,在君凌那座万年冰山的边上,是招袂阳光的笑脸。
陈邱凌先生现在正在s城外的风景区疗养。那里有一家不对外开放的温泉疗养院,是很多政治人物和商业人士休假和休养的好去处。
节假日的风景区,交通因为大批的客流而显得分外涌堵。不过在岔开了几个主要的景点,拐上了疗养院所在的偏僻路面时,四周又恢复了山中独特的宁静优雅。
“待会见到父亲,希望你能体谅一下他的身体情况,不要说出太伤人的话。”
自己驾车的君凌头也不回地说道,山区的冷风从开着的车窗中闯进来将他说的话一字一句冻结起来。
自己会说什么伤人的话呢?
丁翔苦笑了一下。
君凌一定以为,自己此刻是怀着满心的怨恨和不满而来的吧!带着整整二十三年的愤懑和失望,来这里讨回应得的不应得的一切?
天知道,此刻的丁翔,只是想要守住现在拥有的东西而已。
可是也许,今天之后,就连这点小小的心愿都不能实现。
轿车在山路上转了个弯,消失在了掩映的一片翠绿之中,而刚刚行过的山路上又来开一辆故意隐去了牌照的车,以不紧不慢的暧昧速度悄悄跟随在后面。
这条路,只通向一个目的地。
的确是很高级的疗养院。
虽然从大门和外部装饰看来颇为古老,甚至还残留着解放初期糅合着俄罗斯和希腊风格的立柱装饰,而高高在上的那颗现在几乎被常春藤覆盖了去的红星也暗示着它曾经的重要身份。
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之前这里还一直都是政府内部的机构,后来虽然转型为私有制,但是没有特殊的身份或者地位依旧是难以进入。
在门卫的敬礼中,黑色的轿车缓缓开进了院中。
陈老先生住的地方是南部第13幢。
没有想到在拥挤熙攘的风景区中还有这样宽敞的空间。被精心修剪成各种几何形状的树篱在眼前不断地铺陈开,而在那道路的尽头,是一个人工的湖泊。
生长在湖岸边的,是无数奇异的植物,延枝拓叶,高高低低地在这湖边临水而照。
湖西边那些漫过堤岸的小水洼,缀缀连连形成了一串银色的湿地,乳黄色的水芋正在水中迅速地蔓延着;湿地边有一片合欢树林,隐约可以看见前来疗养的人们惬意的身影。
就在丁翔以为自己是冲着那湖水而去的时候,车子灵巧地一个拐弯停靠在了幢式样古老的洋房前。
南部13幢。
红砖黑瓦,青色格子木窗,屋顶上开着两个对称的鸽窗——如同积木世界般经典的设计。让丁翔有种与外部时间脱节的错觉。
下了车,君凌在前面带路,他们的目的地确切来说是这栋洋房一楼最右侧的房间。也是陈邱凌的病房。
屋子内部与外部形成鲜明的反差。
除了依旧保留风格的暗红色镶嵌木地板,内部的其他陈设几乎可以用超现代化来形容。吸顶感应灯,塑钢有机玻璃的隔音门,柔软的长绒地毯,防盗的防火的监控器,有些重要的门前还安装着类似于刷卡和语音识别系统。
“那是父亲以前休息的地方,不过已经很久没有用到了。”
看来陈邱凌已经住进来很长一段时间了。
在右手走廊的尽头,有四名高大男人职守在摩砂玻璃门前,看到君凌走了过来,便微微点头致意。
“陈总。”
他的父亲是陈总,他也是陈总,而且是现今更有权利的陈总。
对于君凌身后跟随的那两个人,四个人中没有任何一个抬头来理会一下。
“招袂,你在这里等着。”
让少年在外面等待,君凌示意丁翔跟着自己进去。
“加油!”
招袂偷偷在丁翔手心按了一下,表示鼓励。
深吸一口气,是见面的时候了。
病房的布置,是毫不意外的洁白,还有些灰蓝,纯洁而没有生机的颜色。
各种各样丁翔不认得的仪器,贴着墙角堆放着,而在病房的正中,那张病床上躺着的人,便是他此行的目的。
那是个高大却消瘦异常的男人,带着灰蓝色的手术帽,但是依然可以看得出来,头发已经因为化疗而落净,宽大的前额上皱纹满布,眼眶深陷下去,而颧骨却突兀地高耸,面颊则深深地凹陷。
这个人……就是那年那个温柔地摩挲着自己头发的人么?那个高大的人?
记得他是自己小时候见过最好看的人,没有一个小朋友的父亲比他更高大、更神气。虽然从不敢在妈妈面前问些什么,但私底下自己也曾偷偷希望自己的父亲能够长得像这个“人贩子”一样……
而那原来就是自己的父亲!
那是他的父亲,却又不是他的父亲!也许老天不让他拥有任何美好的事物,于是便降下了分离,然后在十多年后的今天,还给自己一个行将就木的家人。
望着那满脸病容的男人,看着那输液的、呼吸的各种各样的管道。一种钻心的酸楚涌了上来。
他知道,今天,自己将被改变。永远地改变。
第二十九章
“他来了。”
一边示意陪护者暂时离开,一边这样说道,君凌走上前去,拿起两个靠垫枕在男人背后。
上午是陈邱凌神志比较清醒的时候,也许是因为对于这一天尤为期待,所以立刻从浅眠中醒转过来。
一双布满了红色血丝的眼睛,不甚灵活,且暗淡无光。
“……”
张大了嘴,却不知道应该说些什么,就这样有些尴尬地停住,其中包含了多少苦涩,也许只有本人才知晓。
“翔……”半天,只吐出这个名字,二儿子的名字,在大儿子送来的报告里提到过很多遍,也被自己反反复复念过。
一定是自己的孩子。鼻子和眼睛有点像自己,而前额和嘴巴……则像她。
那个他这辈子都不曾忘记的女人,不知道应该用爱或者恨来形容的女人。
他和她原本相恋,在故事的最初,后来她嫁作他人妇,而自己也有了妻室,可是多年后的再会,剪不断理还乱,感情的际会,说到底应该怪谁?
想要伸出的左手因为静脉推针的阻碍而痛苦痉挛,于是换成右手,那因为病魔而格外苍老且瘦骨嶙峋的手像是要突破这十数年光阴的封锁,握住自己的孩子,抓住那流失了的成长瞬间。
这瞬间,丁翔潸然泪下。
还有什么可以抱怨的,还有什么不能原谅的?当这双逐渐失去了生命力的手伸向自己的瞬间,一切都变得不再重要。如果说他和她害得自己只能拥有一个残破的童年,可是他同样也付出了苦苦寻找的十数年时光,而现在,正当大多数人依旧身强体健的四十几岁,他却不得不缠绵病榻,甚至注定了将在不久后的某个时刻静默地死去——纵使有万贯家财,纵使求得名医无数,终究要与不舍的一切,作个了断。
伸出手来接住了那只嶙峋的大手,感觉到了粗糙的纹路。丁翔的动作是那么轻柔,就像那掌心的生命线随时都有可能断开一般。
“终于……找到你了。”
周围一片寂静。站在一边的君凌也一直沉默着。空气中混合着消毒剂和酒精的气息,像是一个沉默的预言,升腾在半空中。
“爸爸。”
这是一个奇妙的词语,开始的时候很轻微,,但就是这个连正常人都难以分辨的声响,却在陈邱凌的眼瞳中制造出了异样的光芒。
一粒心火迸裂开来。
“爸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