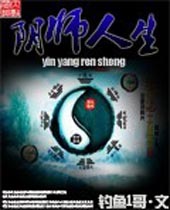醉花阴-第16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东方璾轻松地说道:「是吗?」这半个多月,不知道被人吸走了多少钱。「那东方泰有没有什么动作?」
「暂时没有。」飞轻摇摇头。
虽然东方泰怀疑是有人故意捣鬼,但是神秘客人不但形貌口音各自不同,而且都是来去匆匆,要追查也无从追查起,想要作弊却发现对方更高一筹,这半个月下来他输得难以计数,而且其它输光的族人也满肚子怨气难以摆平,现在族长东方璾又跑到了山馆避暑,难道要叫他们向扬清哭诉吗?打死他们大概也拉不下脸来,东方璾可乐得把扮黑脸交给扬清。
「真是一个赌徒,但是赌技不怎么高明……你可以回去了,记得继续保护寒香馆众人安全便是。」赌性坚强的人要到什么时候才会忍不住呢?还要多久才会向长老们哭诉呢?
「不知道他哪时候才想到是谁做的好事。」东方璾逗弄着飞雪,嘿嘿嘿嘿地恶意笑了,他就是要这些人赌得倾家荡产无路可走,进而狗急跳墙,他现在就在等这些人被逼急了有所动作的一天。
飞轻听见那阵好整以暇的笑声,徐徐皱起一双浓眉:「您到底想做什么?」他实在弄不懂东方璾为什么这阵子以来异于往常的勤奋,表现出一副凡事爱理不理的样子,可是他知道东方璾一定心里正在盘旋着什么计画,因为最近四骑各被交代了不同的机密要务,看来东方璾正在策划大计,表面上却一派轻松自然,这就是所谓气量的差别吗?
东方璾不答反问:「飞轻,如果你手上有一个覆盖坚硬外壳的东西,你要怎么打开它?」
飞轻楞了一下,但是还是回答:「将外壳破坏,拿出里面的东西。」
东方璾漫不经心地玩着飞雪的羽毛:「我没说要里面的东西啊,再说里面的东西也不一定是好的,搞不好全烂光了。」
飞轻又楞了一下,既然如此何必那么执着于破坏外壳呢?
脑中瞬间灵光一闪,他惊异地看向仍在和飞雪玩耍的东方璾,东方璾心里想的东西,他似乎有点触着边了。
东方璾的声音只是淡然地在他耳边响起:「你下去吧。」
飞轻犹豫了一下,转身要走,但是要走之前他还是问了:「您不想知道逝芳公子最近怎么了吗?」
「知道他还活着就好了。」那种没心少肺的家伙不会轻易死掉的。
飞轻走了之后,东方璾轻轻一扬手,将膝上的卷宗全挥落了地。
这么美丽的夜,适合一个人想一个人,孤单地想着一个人,还有渴望一个人。
***************
「喂!你不是应该病歪歪地倒在床上吗?」飞花面向正坐在梳妆台前梳理头发的人影,没好气地碰一声放下餐盘:「哪,药和晚膳端来了。喂~~那是什么鬼脸,不要朝向我,好恶心!」恶,活大半辈子,没看过这等形迹猥琐的丑男!
那个满脸麻子神情呆滞的「丑男」回过头来,露出满口黄牙冲着飞花嘿然一笑:「劳大姊帮我处理那些东西啦,我要出门了。」
「你今晚又要出去玩?可是东方泰要来堵你哪!」
逝芳轻蔑一笑:「由得他来吧,他不在我更好放开。」
飞花插腰:「如果他知道你不在,不就穿帮了?」十几天来用尽各种办法让人赌输那么多银子,又故意摆明了不见东方泰,到时东方泰追杀也要讨回来看逝芳怎么办?
「就劳大姊帮我挡驾啰。」逝芳一派轻松地很。「我是病人啊。」
飞花顿时觉得自己太天真了,竟然相信逝芳不会这样脸不红气不喘地拜托她。一阵头痛,她举酒喝了几口才擦擦嘴:「劳你的福,最近酒是越喝越少了。」要命,最近晚上都轻松不得,主子不在家跑去赌钱,她要照料馆内生意又要防着东方泰,整晚不保持清醒战战兢兢都不行。
「万一他趁我不注意又派人进你屋子搜查怎么办?」前两天其实东方泰已经派人偷进寒香馆打探,结果当然是很惨地回去。
换穿一件不起眼的藏青袍子,「你想他还会吗?真有这样的人的话就杀掉,丢到门外去。」
「喂!我可是弱不禁风的女子啊。」
逝芳笑了一声:「这是今晚我听过最好的笑话。」
飞花一拍桌子,母老虎凶相毕露:「啥?你说啥?有本事你给老娘再说一次!老娘为你流血流汗,你还敢消遣老娘?」这家伙年纪轻轻脸皮这么厚,拜托她一点都不会觉得不好意思,敢情他是没看女人凶过是不是?
没想到眼前那个举世丑男只是无辜地眨着绿豆般的眼睛,像虫一样扭动身子撒娇道:「唉呀大姊~~~别这样嘛,今晚馆里的红利全部给你嘛~~」
好、好恶心,飞花顿时一阵反胃眼冒金星,果然撒娇使泼这种招数还是要美女或美少年来做比较好,看一个脸像被踩过的风干橘子皮的中年男子做这种事真的会让人觉得黑白无常在招手了,好恶心,好恶心,不是普通的恶心,不是恶心两个字可以形容!
她转过身蹲在地上,无力地挥挥手:「停、停、停我认了我认了你给我快点死出去!」
背后只听逝芳轻笑一声:「放心吧,东方泰就算向天借胆,也不敢随便进寒香馆,谁叫咱们寒香馆面子这么大,人脉这么广,走了一个东方璾,又来了一个罗妲儿呢?」除非想让听月翻脸不认人,不然东方泰不敢随便招惹罗妲儿,偏偏罗妲儿这几天都泡在这儿,等于是寒香馆的护身符。
飞花悻悻然地说道:「切!她整天缠着叶怜不放你都不紧张?长云山庄想开妓院,说不定在招叶怜做红牌哪!如果叶怜走了,寒香馆岂不已经倒了一半?」
逝芳无所谓地耸耸肩:「反正做这行没有长久的。」描了飞花一眼,他嘴角突然流露恶意地一笑,笑得飞花浑身毛骨悚然,这才慢条斯理地蹲在飞花面前:「我说飞花呀你也老大不小了,难道没想过找个人嫁了过过平静日子?总不能一辈子这样当小魁的奶娘啊。」
「你还知道他是你的侄儿真是可喜可贺,要出去就快滚。」哪壶不开提哪壶,真能嫁她早嫁了,还会待在这里被这小子消遣,作小鬼的奶娘折自己的寿。
那张丑男面具下,逝芳漂亮的嘴角仿佛扬得更高更不怀好意了:「哦…是吗?」他起身向外走去,仿佛刚刚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那我走啦。」
「慢走啊,不送啦。」
等到逝芳偷偷从后门溜出寒香馆后,这个绝顶艳丽的美女才深深吁了一口气,起身伸伸懒腰。和逝芳对话总让她寿命折了不少,唉唉已经二十几岁见过无数男人的女人啰,还被一个小子耍得团团转,陪他在这漩涡里颠来覆去,也只能说自己傻吧?
「嫁人啊………」飞花走出门外,淅沥淅沥的流水声传进她耳里,夏夜里清柔的凉风吹到她脸上,让她想起了南方多雨湿热的晚上,偶尔也会有这么令人舒爽的夜风。唉,她也很想嫁啊,趁着自己还年轻貌美的时候捞个不错的男人当丈夫,一辈子平平静静的生几个孩子然后孩子们生几个孙子,老的时候晚上和那口子喝两杯,这种日子真的很不错。
她最后苦笑两声,红唇凑上白玉酒壶:「算了,如果我有那种运气的话,也不会被那个男人逼得远走他乡了。」
「哪个男人?」一个声音在她背后响起。
「当然是寒影山庄那个名字像闺秀,长得如美女,个性连毒蛇都自叹弗如的伪君子,宋言轻他爹的大老婆生的儿子宋女萝………」吓!刚刚是谁在同他说话?那声音,好象………。好象………有点耳熟。
「哪个男人?」那声音又重新问了一次,那听过一遍就不会忘记的温柔和气若游丝、宛如痨病鬼一样的语气,离她这么近就在她背后、不、不会吧?
僵硬地转过身,姊妹甲身边跟着的文弱男人伸出一只苍白地近乎透明的手在她面前晃荡,像鬼一样白中泛青的清秀脸孔上,还是如记忆中一样让人想一巴掌挥过去的笑容……。
「宋……。。女萝………」
「好久不见了,飞花,你也真会躲,竟然躲到东方璾的地盘里,如果不是有人邀我来,我还不能光明正大来找你呢。」轻柔语气一如往常,寒影山庄的少主温言细语道,握住她犹抓着酒壶的手,那种冷凉的感觉顿时一阵哆嗦上身。
事已至此,飞花确定,她如果不是被逝芳出卖,就是被带衰了。
一方面,麻脸男子哼着歌儿散步在花街柳巷上,随然知道背后有人跟着他还是慢不在乎在小巷中东拐西弯,不一会儿就消失在人群之中。
负责盯梢的扬烈一惊,他跟丢人了?连忙快步想追上,可是拐过弯角他觉得有人拉住他衣角。
他低头一看,寒香馆一向神龙见首不见尾,外表长得像小狐狸一样可爱,整天躺在摇篮里没在睡觉就是傻笑的怪娃儿竟然爬出摇篮,还神不知鬼不觉的站在他身后,睁着一双大得快要满出来的眼睛,可怜兮兮地抓着他衣角,小声说道:「哥哥,我肚子饿了,吃吃!」
「喂!你赶快回去,你家在哪里,乖~~自己回去好不好?」扬烈努力陪着笑脸,手伸得长长努力指向远处的寒香馆。
「肚子饿了………。。」大眼睛开始蓄满泪水
「你家在那里………」
「肚子饿了………呜呜呜呜呜………」开始发动泪眼攻势,引发路人侧目。
扬烈认命地蹲下来,低声哀求:「小少爷算我求你了,我现在很忙……」他们四个人赌他多久就会跟丢逝芳,现在一炷香时间都没过,他会输得万劫不复一辈子被嘲笑到死啊。
想不到魁抬起半张脸,狐狸一样的眼睛狡黠地看着他:「大哥哥你不带我去吃东西,我就在这里叫你『爹』。」
「……………你果然和那个逝芳有亲戚关系。」
醉花阴第七章之一
在这个世间,每个人有他的走路方式,或如履薄冰,或洋手阔步,当然也有人如蜻蜓点水。
在这世间,总不免相遇与别离。
相遇的时候金风玉露,分别的时候折柳相别,其间和数十年比起来不过一瞬间,为什么对一个人来说,可以抵上庸庸碌碌的一辈子?遇过的人多如繁星,为什么总有人的光芒可以照亮不眠的夜?
是否因为和这滚滚红尘比起来,他像山间的落花,落在肩膀的细雨,又像是插进胸口的一把剑,记忆可以那么轻柔也可以那么沉重,教你刻骨铭心的难忘也不愿将记忆拋弃遗忘,如着魔一样将那个人印在脑中想在心里,怎样也无法遗忘,无法轻易放过?
没有把握能够看着他挥手相送,折柳相别,笑着说再见。
假如还有一次机会,也许一切都还来得及,或者用一切来交换,也许一辈子就这么一次痴狂与执着,那时候,你是否会问他:
「愿不愿意跟我走?」
不管是谁,一辈子若有一次机会,若有一个人,向你问着这句话,或你问了他这句话,该如何去回答?
*************
深夜里,东方璾睁开了眼睛。
他听了细微的雨声,这是数不清第几个雨夜了,山里雨下得很频繁,唏唏唢唢的声音敲在树干上、花朵上、石头上,投进水中化入湖里,声音都不一样。
滴进心里时,泛起一阵阵无声的涟漪。
当人心开始变动的时,谁也看不到这世间将往哪里去,又会怎么变,但天还是会下雨,一年还是会有四季,春水缠绵夏夜蝉鸣秋花零落冬雪纷飞,十数年来无数日子立在河岸边,看遍大江南北的船只,从东方的序日到西方的夕阳,再从夕阳的国度回来的东方璾东方璾比谁都了解东方家赖以维生的大河千年如一日的流动规律。
也许会有沧海桑田的一天,但是东方璾没把握自己能活到那时候。
既然能活的时间那么短,东方璾问自己,他到底想要什么?
**************
快天亮了,趁着这夜里最昏暗的时候,逝芳混在脚步癫狂的人群中打算回寒香馆去。
走在道上,他第一次觉得自己踏足在梦中,不是因为身边的每一个人醉酒装疯的丑态让自己有此感觉,而是自己同他们在这条路行走,看似是醒的那一个,其实一样在不醒的梦里,路始终走得漂浮不定。
脚踩在路上总有一种不真实的感觉,当身边的人只是迷茫地随便有人来陪伴的时候,他环顾四周找不到和自己一样寻找对方的人,只属于彼此的那个人,每一个人闭着眼睛蒙着耳朵四处乱走,企图找到出口。
两个月前,东方璾就这样离开了他,那个该揍一顿的家伙………逝芳想起来还是满腹怨气,凭什么东方璾可以一脸了不起在自己面前说那些话,然后一走了之然后不用负任何责任?
凭什么他可以这样潇洒离开?就因为他不是扬方?
谁要做扬方,做一个永远活在对方阴影下的人?谁要一辈子为人作嫁,最后让生命都赔上?即使亏欠过多少,当扬方死的时候就该还清,即使知道自己是由他的魂魄醒过来的,但是扬方的记忆和爱恋却没有随之一起转生,因为过往的都是模模糊糊的像从水里看着世间,只有东方璾格外清晰,清晰地刺痛了心。
他或许在过去的那一段日子,都是透过东方璾看这个世间的吧?
他或许,是心甘情愿活在那一片阴影里也说不定。
那为什么此生还是要与他相遇?为什么还是不由自主地来到这里?为什么当他再次离去的时候,心会痛呢?为什么当东方璾说「你又不是扬方」时,心中有一种又苦又甜的感觉。
东方璾,你说「我不是扬方」,那「扬方」在你心里,又是怎么样一个人呢?
想着想着,脚下被树根绊着了一下,他抬起头,原来是一棵老树,每天从后门溜出来时总会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