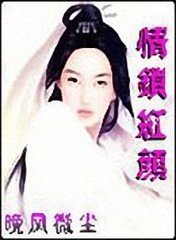回首碧雪情-第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棠珍后面这句话的声调放低了下来,像是喃喃自语;玫君几乎没听见:
“还没完呢!这个徐寿康……徐悲鸿,他在学校里教的是画画,听说才气倒是有那
么一点,可就是怪!是个怪先生!为了挑起养家的责任,他在咱们宜兴县三所学校里教,
除了我爹教的那所之外,另外还有两所在和桥镇上,他们家呢,住在屺亭桥。三所学校
赶着上课,每天天不亮就出门了,单趟就得赶三十里路,人家可是来回都用走的,为的
是省下车钱!经常是过家门而不入。你以为他跟古时候大禹治水学的啊?才不是呢!他
是没空进家门,得拼命赶路!”
玫君愈说愈起劲,也愈说愈得意;棠珍听着听着,终于忍不住笑了。玫君说得没错,
这么个人,是挺怪的。不过,棠珍心里除了觉得怪,也有些好奇;至于好奇些什么,自
己也说不上来。
好不容易,玫君总算下结论了:
“这些都是我在学校里听来的,最有意思的是,我们同学已经给这个怪人取了个绰
号,背地里叫他﹃红蹄子书生﹄,就因为他在白布鞋里穿了双红袜子!棠珍姊,有没有
兴趣去看看那双红蹄子?他这会儿跟我爹聊得正起劲呢!”
经不起玫君的怂恿,也为了自己心里那一点好奇,棠珍真的跟玫君到她家去了一趟;
姊妹俩找了个借口在厅里转了一圈。棠珍刻意悄悄瞄了一眼,只见那个玫君嘴里所说的
“怪人”,跟大伯父谈是谈得很起劲,而姿态却是正襟危坐,像是个有规矩的人;更重
要的是,从表面上,棠珍看不出他有哪一点“怪”。管它的,怪不怪都跟自己无关;玫
君她们爱怎么说,也都跟自己无关……
玫君想说故事的时候可从没放过堂姊;过了没多久,七月里的一天下什,她又带着
一堆马路消息来了:
“棠珍姊!那个‘红蹄子书生’离家出走了!”
“你还真是人小鬼大,小丫头一个,已经学会包打听啦?说吧!”
棠珍知道这个堂妹听来的消息是藏不住的;也知道这个丫头一敝开来,故事准说个
没完。棠珍心里有了准备,阖上正看着的一本古诗词集;果然……
“那个徐悲鸿啊,一下子把三所学校的差事全都辞掉了!人也不知道到哪儿去了,
急得他娘跟他太太到处找、到处托人打听,可就是没消息!”
“他太太?他成亲啦?上回没听你说起嘛……”
“十六岁就当上新郎倌啦!还生了个儿子……都有三岁了吧!当年的亲事是他爹娘
硬要做主的。他不服气,又不满意对方,说是出身农家、没学问,彼此谈不来,结果,
他干脆逃家了事,可是又被找了回来,他没辄,只好硬着头皮跟人家拜了天地。儿子是
第二年出生的,听说就是跟家里赌气,认为这就已经尽到了传宗接代的责任……”
玫君一口气说了这么多,棠珍没有搭腔的份,只能静静地听;但上回感觉到的那一
丝好奇,似乎没来由地又加深了一些。玫君几乎连眼睛都没眨一下,还是说得那么带劲:
“所以说起来,这已经是他第二次逃家了!可是这回是为了什么,连他的亲娘都说
不上来,反正啊!怪人就是怪人!”
棠珍这会儿已经不那么专注听堂妹说故事了,她有了自己的心事。像这个“怪人”
徐悲鸿,因为不满意家里给他安排的亲事,他逃婚、他离家出走;虽然还是给抓了回来,
但他毕竟试着反抗过。而棠珍自己,也是在父母亲安排之下订了终身;尽管是所谓的门
当户对,但那还是一种冒险,自己的未来还是一个未知数。
订了亲之后,多多少少总要关注一下自己将要依附终身的那个男人;而让棠珍不安
的是,查紫含似乎并不像做媒的堂姊当年所形容的那么完美无缺。因此,偶尔在夜深人
静的时候,棠珍会犹疑、会害怕、会难过;她实在想不通,自己有什么理由要为一个全
然的未知去冒那么大的险,那是把自己的一辈子当赌注押上去了啊!她知道父母亲疼她,
知道父母亲是为了她好;但爹娘啊!当年你们这么做是不是太仓促草率了些?你们对那
个“查家二少爷”真的了解吗?
不知怎么的,对于那个又一次逃家的“红蹄子书生”,棠珍心里原先的好奇竟然掺
进了那么一丝同情、一丝关怀。是啊!当年逃家是为了逃婚,那这一次呢?什么理由让
他拋下老母、拋下妻子和幼儿?连一点音讯都不留下?
玫君是什么时候离开的,棠珍没在意。她重新翻开那本古诗词集,想要把自己的心
事丢得远远的;但愈是如此,那一股股的心事愈是乱得厉害。当她读着李清照的“多少
事欲语还休”、当她读着李白的“但见泪痕湿,不知心恨谁。”棠珍竟然发觉自己的眼
角真的有点湿了……。
四年前,姊姊出嫁的那一天,母亲说过一些话;棠珍那时候藏起的少女憧憬,如今
依然得藏着。那时候的憧憬是模模糊糊的,她说不清,只能藏着;而如今,憧憬虽不再
模糊,但她不敢说,还是只能藏着。十六岁的棠珍,已经开始懂得如何去勾勒未来;但
她的未来早在三年前就被人重重画上一笔,那巨大的一笔几乎占据了她整个的生命,哪
有多余的空间让自己去勾勒?
棠珍湿湿的眼角滴下了泪水;第一次,她为命运啜泣……
蒋家有一位远房亲戚朱了洲,虽然是宜兴人,却来到上海谋生,在一所学校里教体
育。蒋梅笙在复旦大学任教,朱了洲经常就近到他家里请益,还称蒋梅笙夫妇为“先生、
师母”。这时候,原来留在家乡的棠珍也已经到了上海和父母团聚,因此常有机会见到
这位同乡。
朱了洲个性爽直、为人风趣,喜欢交朋友;他身上也有着许多轶闻趣事,而这些有
趣的小故事,多半却是从他自己嘴里说出来的。一九一六年三月初。这一天,朱了洲又
到了蒋梅笙家里,还带了一位朋友来拜见蒋梅笙夫妇。楼上房间里的棠珍先是没在意,
可是当她听到朱了洲那大嗓门介绍那位朋友的时候,她结结实实地吓了一大跳!
“先生!师母!这位是咱们宜兴同乡,他叫徐悲鸿!”
“先生!师母!二位好!学生曾经在宜兴女校滥竽充数,教过图画,跟南笙先生同
事过。”
“欢迎!欢迎!请坐呀!徐先生!”
棠珍说什么也不肯相信自己的耳朵!楼下的客人居然就是大半年前在宜兴离家出走、
完全失踪了的那个徐悲鸿?这怎么可能?棠珍整个人呆住了!一颗心也莫名其妙地乱了。
幸好只呆了几秒钟、只乱了一下下,棠珍立刻恢复了正常;而且出奇地冷静。她细心听
着楼下客厅里的谈话……
蒋梅笙夫妇显然很高兴见到这位同乡晚辈;戴清波泡了一壶好茶,徐悲鸿恭恭谨谨
地从座位上站起来,欠欠身子才又坐下:
“不瞒二老,学生去年还曾经到南笙先生府上拜望过,记得那回是老太爷的大丧,
对不起,学生不该提这些。”
“不要紧,都过了那么久了,老人家享年八十一,也算是老天爷眷顾,福寿同归……”
提起老太爷,蒋梅笙当然略有感伤,但很快就不再放在心上。他仔细看着眼前这个
年轻人,觉得他挺有教养、蛮懂礼节的。戴清波也有同感。这些年她在家乡待的时间比
丈夫久,曾经听说过徐悲鸿这个人;当然,也就是街坊邻居口口相传的那些事,包括他
的离家出走。如今亲眼见到徐悲鸿,倒不觉得他有什么异于常人之处;而且人长得很体
面、言谈举止也讨人喜欢。但是,戴清波毕竟也想知道徐悲鸿为什么离家不顾、为什么
杳无踪影……
“徐先生眼前在哪儿高就?”
“说来惭愧,学生学无所长,只不过从小跟着先父学了点作画,没想到后来就以此
维生。”
“他呀!顶着点才气,就想一飞冲天了!先生、师母大概也听说过,悲鸿原来在宜
兴老家待得好好的,兼了三个学校的图画课,虽然累了点,但多少人羡慕他!可是他不
知足,说什么外面的世界大,不出来多看看、多学学,将来准会后悔。于是,他一个人
偷偷跑到上海来,丢下老母亲、体弱的妻子,还有才三岁大的孩子全都不管,家里一句
话都没留下就走了,好端端的偏要背个拋家弃子的罪名!唉!我都懒得说他了!”
朱了洲不仅大嗓门,说起话来更像是放连珠炮,大气都不喘一口;一番挪揄,弄得
徐悲鸿啼笑皆非,脸都红了:
“了洲兄!别损我了,第一次来拜见先生跟师母,你怎么就当面出我洋相?”
“我说的可都是事实呀!先生跟师母是咱们的乡长,而且二老的道德文章谁不敬佩?
我带你来拜见,就是为了让你跟我一起受教,怎么?你害臊啊?还是想把你的丑事都藏
着?不老实!”
徐悲鸿一张脸胀得更红了。蒋梅笙一看就知道这两个年轻人必定是莫逆之交,斗嘴
绝对伤不了和气;但身为主人,又是做长辈的,不得不陪着做做戏,装出一副打圆场的
样子:
“哈哈……了洲!你的脾气我知道,你是心直口快,可是徐先生毕竟第一次见面,
你就饶了他吧!徐先生,恕我直言,你的好学精神很让人感动,只不过做法上恐怕有待
商榷。了洲说的有道理,你不留下只字词组,让家人平白担这么大的心,这就……哦,
我是交浅言深,你别见怪!”
“不!先生教诲得是!所幸学生来到上海,头半年四处碰壁,后来总算找到了差事,
除了生活所需,攒了一点钱寄回老家去,也算是赎罪吧!要紧的是,上海毕竟是个大地
方,学生始终不忘学习,一方面继续在绘画上求长进,上个月还考取震旦大学,专攻法
文。”
“是啊!悲鸿有个心愿,想到法国去钻研艺术,他这方面的志向我一直很钦佩的!”
“谢了,了洲兄!你总算替我说了一句好话!对了!先生!以您多年在学界的声望,
学生将来不论是否出国深造,说不定哪一天还需要您的大力提携呢!”“哈哈!好说、
好说!”
经过这一席闲谈,蒋梅笙对徐悲鸿的印象可以说是相当的好,他兴致勃勃地望着妻
子:
“你去准备些酒菜,咱们留这两个年轻朋友吃饭,……年轻人毕竟有可爱之处,有
些事情、有些看法,咱们得跟他们学学!”
家里一向很安静,房子也不大,楼上的棠珍几乎没有漏掉客厅里的每一句对话。爹
要留客人吃饭,那么待会儿当然见得到徐悲鸿;棠珍心里砰然一跳。不知道是不是因为
在宜兴老家就听说了这个人的那么多故事,棠珍觉得自己好象是要见一个阔别的老朋友;
又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刚才偷听了那一席话,觉得自己好象对这个人起了莫名的好感。总
而言之,棠珍心里好不自在。而母亲在楼下喊她了:
“棠珍!下楼来!家里来客人了!是你了洲大哥,还有一位咱们宜兴同乡徐先
生……”
“知道了!娘!”
棠珍差点没喊出,我知道这位徐先生……
餐桌上的气氛是愉快而温馨的;蒋梅笙跟两个年轻人聊得起劲,师母勤着为他们布
菜。徐悲鸿也许天生就有讨好长辈的本领,他对满桌佳肴赞不绝口:“师母,不是我刻
意奉承,您做的道地宜兴菜,真可以说是天下第一!学生敬您一杯!”
“徐先生过奖了!大概是你好一阵子没吃到家乡菜,想家想的!”
师母嘴里客气,心里却欢喜极了;这孩子的一张嘴可真甜……
“先生!听了洲兄说,您经常吟诗作对,不知道学生有没有耳福听您吟唱一两首大
作?”
“你别听了洲替我瞎吹牛!他那夸张的言词,就跟他的大嗓门一样出名!不过,昨
儿晚上我倒是涂鸦了一首七言绝句;徐先生不嫌弃就多指教!”
蒋梅笙清一清嗓子,稍稍晃动着上身,随口念出了:
春风庭院百花妍,赢得佳人爱惜偏;碧碗银瓶多供养,梦为双蜨藉花眠。
“好诗!好诗!真是绝妙佳句!学生万般佩服!”
徐悲鸿击节赞叹,一旁的朱了洲也跟着鼓掌不已。
“徐先生谬奖了!”
同样的,蒋梅笙也是乐在心里;本来嘛,自己的作品有人激赏夸赞,哪怕是来自晚
辈,也是值得高兴的。唯一不怎么说话的是棠珍,她静静听着,静静看着,静静想着。
心里有感觉,但是说不出;嘴里有话,但是不敢说,她只是偶尔应和着露出浅浅的笑。
直到大嗓门的朱了洲再一次拿自己的糗事当笑料:
“提起吃饭,我这辈子算是遇到邪了!我一向食量很大,一顿饭能吃八碗十碗而面
不改色,而且还常拿这点本事跟人打赌。得!有一回在宜兴到无锡的小火轮上,同行当
中的一个女同学向我挑战,说是她吃一碗,我吃两碗,谁先认输谁付账。你们猜结果怎
么了?她一口气连吃了九碗,我呀!拼了老命吃到第十八碗,躺下了,让人给抬到船舱
里,你们说那多丢人现眼!”
“哈哈……”
这回,连棠珍都笑得几乎流出眼泪;徐悲鸿更是伸长了手臂,直拍着朱了洲。笑声
中,棠珍悄悄瞄了徐悲鸿一眼,就像那一回在大伯父家客厅里;只不过,这一回她看得
仔细了些……
这天夜里,棠珍第一次失眠了。
第二节
上海一条马路的人行道上,徐悲鸿和朱了洲信步走着;同样是享受了一顿难得丰盛
而又温馨愉快的晚餐,两个人的心境却截然不同。朱了洲生性爽朗,看起来大而化之,
但也有他细腻敏锐的一面。一顿饭吃下来,
他几乎注意到了每个人的表情;他发觉了一些事,心里正琢磨着……徐悲鸿则显得
心事重重;饭局中的潇洒自如、能言善道,此刻全不见了,变得眉头深锁、静默无语。
朱了洲像是有意戳破徐悲鸿的心事:
“怎么了?……魂还留在先生家里呀?”
“没什么啦!”
“没什么?你真当我是二楞子啊?告诉你,你心里想的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