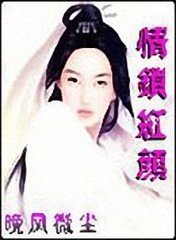回首碧雪情-第2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服务生端来了沙拉,两个人不约而同地垂下眼帘,拿起左手边的叉子……
车子静静地滑进了陵园,道藩把引擎熄了,然后把车头的灯关了。碧微把半开的车
窗摇到底,她想多吸几口秋夜里的清新空气,而道藩却打开了车门:
“下来走走吧!”
离开餐厅的时候,酒瓶是空的;碧微就只是开始的那半杯,而且没喝完。看得出道
藩有点醺醺然,碧微不放心地紧跟在他身边:
“你不该喝那么多的!”
“我说过,难得的苦中作乐……而且,我知道自己的酒量。”
“我晓得你没醉,但是……”
“但是有点飘飘然,我承认!……知道吗?酒是最忠实的朋友,你敬它一分,它绝
对回你一分,不多也不少……我是说,你喝了多少,感觉就有多少;它决不骗你!”
“这是你的喝酒哲学?”
“不!是一个朋友告诉我的;我虽不常喝,却颇能体会个中滋味!”
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的,碧微突然发觉自己的手被道藩牵着;更让她惊讶的是,自
己并没有把手抽回来。道藩长长地吐了一口气:
“我知道酒可以使人壮胆,但我决不认为它可以被当作是乱性的借口或触媒!”碧
微没说话,她静静听着;静静地让道藩继续牵着她的手。
“……让我多说几句吧!反正我总是无法在你面前遁形,……上回我告诉过你,十
一年前我跳不出来,十一年后还是跳不出来!但你知道吗?十一年前你寄到翡冷翠的那
封信,止住了我一颗跃动的心;十一年后你的几句话,则是让我懂得了怎么去升华……”
碧微还是静静地听,她感觉得到自己的手被握得紧了些。
“那天你说,恋爱就像攀登一座山峰,一到了峰顶,无论如何就只能是下坡……你
还说,男女之间最珍贵的爱应该局限于精神的层面。你问我明不明白你的意思,我现在
可以回答你,我明白!不但明白,而且还要自己把你这两段话放在一起品味;你相信
吗?”
碧微怎能不相信!她发觉自己的眼眶湿了……然后,她听见道藩低沉的声音在耳边:
“晚了,该回去了!”
“嗯。”
从刚才到现在,第一次,碧微的手紧紧回握着道藩……
院子里的深夜,秋意特别浓;才九月底,已经有点凉凉的感觉。刚才是几个人一起
聊天,这会儿他们全进去睡了,只剩下碧微和道藩。碧微正吃着水果;道藩端着茶杯,
想了又想才开口:
“真的决定走了?”
“嗯!船票买好了,孩子过两天也就要从宜兴家里接来了。”
“六号,就只剩下一个星期了!”
“像你说的,这是逃难,逃难哪可能从从容容的?”“那你这两天就得开始准备
了!”
“其实也没有太多的东西。上回搬到你这儿来,已经整理过一次,该扔的全已经扔
了,还是那两个字:逃难!”
“人就是这么奇怪,嘴里说的跟心里想的常常要彼此打架!”道藩突然冒出这么一
句,碧微楞了一下:
“我不懂你的意思……”
“我是说我自己。嘴里跟着大伙劝你,而且……也不得不劝你,但心里还真舍不
得!”
碧微警觉地回过头往屋子里看;楼上楼下,灯全熄了,只有空荡荡的客厅还亮着一
盏小灯。院子里的小茶座和屋子之间有着一段距离,但她还是刻意放低了声音:
“别孩子气!”
“我知道!”
道藩苦笑了一下;然后也下意识地回过头,看了看屋子里。
“你允许我写信给你吗?我是说,除了那种客套的、问候的信之外……”
碧微倒是没想到这一层,她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我也不知道……也许,可以吧……不!我真的不知道,这会儿……我的意思是,
看情况再说……也许等我先写给你!”
真的有点不知所措,碧微语无伦次的;但道藩应该懂得她的意思。
道藩也有点语无伦次了:
“……假如我真要写信给你,在必要的时候,我想……我得换个称呼……我是说,
也许你给我你的小名、别名……不!都不好!你得有一个别人不知道的名字……你有没
有?”
碧微想张口说出“棠珍”两个字,但自己哑然失笑了;那怎能算是别人不知道的名
字?低头想了一会儿,有了!
“雪!冬天里下的雪!我曾经幻想用这个字给自己取个别名,但后来用不上,也就
忘了!就是雪这个字吧!雪是我最喜欢的景致!”
“好啊!可是,这雪字,似乎轻了些,也孤单了些,得再加上一个字。”
“既然你这么认为,那就由你想个字吧!”
道藩很认真地想了一会儿,然后他眼睛一亮:
“加个芬字!芬芳的芬!……我喜欢这个字!可是……如果你想出更好的……”
“雪芬……雪芬……”
碧微轻声念着,她笑了:
“就这个字吧!……我也喜欢这两个字连起来的味道,而且这读音……”
这读音也挺顺口的,“雪芬”……
不知怎么的,碧微想起了那一年在瑞士洛桑看到的雪;不知怎么的,她想起了悲鸿
给自己取的这个名字……好遥远、好遥远的岁月了!由于想起了悲鸿,碧微几乎打消念
头,想告诉道藩别再提写信这回事,但她没有。
抬起头,她看见道藩正注视着自己。
“怎么了?……”
“……没什么,该进去了!”
碧微懂得道藩的意思;她站起身,帮忙把茶具收好,端进屋子里。
第二天清晨碧微醒来,从二楼窗口望下去,看见道藩已经在院子里,这么早!仔细
看看,道藩像是在散步,却更像是在凝思;碧微原想挥挥手打个招呼,却又把抬起的手
臂放下了。
从盥洗室回到房里,刚跨进去,一眼瞧见床头柜上躺着一个西式的白色信封,信封
上没有任何字。反手关上房门,正要朝床边走,门上有人敲着:
“徐太太!”
碧微打开房门,是张家的仆人老陈。
“徐太太!……张先生让我把这几朵月季花送来给您!”
“哦,谢谢你啊,老陈!”
“甭客气!”碧微重新关上房门;手里捧着花,心里却在为那个白信封砰然不止。
放下花,拆开信封,她一行一行仔细地看下去。
第十四节
南京的下关码头,一艘轮船烟囱冒着烟;船头漆着三个大字:江靖轮。旅客和送行
的人上上下下,加上船员、茶房、行李工人挤来挤去,一片乱哄哄的,碧微这才真正体
会到什么是“逃难”。甲板上,两个孩子正围着道藩,听张叔叔讲解怎么给照相机换胶
卷:“呶,就这样,把底下这块板子合上……成了!然后再打开上面的盖子,这又可以
照了!”
伯阳笑了;丽丽踮起脚,想要从照相机上面开口的地方看看能看到什么,因为张叔
叔每次都低下头朝里面看了一会儿才拍照的……碧微靠在船弦上,望着这一幕,心里有
说不出的感触;两个孩子已经慢慢开始懂事了,却少了个可以教他们许多许多有趣事情
的父亲。道藩拍了拍两个孩子:
“好了!伯阳!丽丽!快站到妈妈身边,张叔叔也要跟你们合照……欸!子杰!了
然!一起来!……坤生!你过来!”坤生姓史,前些年娶了刘妈的女儿同弟;刘妈回宜
兴去了,女儿女婿就接替着在碧微身边帮忙。
坤生走了过去,很机饯地接过照相机;刚才他已经充当过一次照相师了,难不倒他。
除了坤生和同弟,跟碧微他们同行的还有顾了然;郭有守则是跟道藩一起来送行的。
郭有守站在碧微右边,碧微下意识地把皮包换到左肩上背着;上船之后,她心里一
直惦着这个皮包,因为里面藏着好几个白色的西式信封……从那天开始,道藩没停止过
写信,他像是发了痴似的拼命写;他要把握住碧微上船之前的每一天,把自己心里那么
多那么多的话全写在纸上。
是因为道藩十一年来从未褪色的执着?还是因为他这一封封能让人读出眼泪的信?
碧微不清楚;但有一点她非常清楚,那就是自己无法不被感动,于是她也好几次在灯下
振笔疾书、或是握笔发愣。全天下大概再也没有别人像他们这样。住在同一个屋檐下,
却还需要信来信往的;住在同一个屋檐下,却也只能这么信来信往的……离别的滋味很
不好受;尤其是逃难,尤其是面对那全然不可知的未来,尤是不能在别人面前露出过于
明显的离情,尤其是……太多只属于他们的情境,让这离别的滋味比其它人的更不好受。
碧微看得出道藩的愁绪甚至比自己的更浓。那是可以理解的;他在一封信里写得很
明白:
“……我问苍天,十多年来,我从不敢有任何企求,直到人家侮辱了她、虐待了她、
几乎要拋弃了她的时候,我才向她坦承十多年来我这深深的爱从未断过……而当她似乎
要开始接受的时候,忽然人家又要从我的心坎里把她抢回去了……请问上天,这样公道
吗?”
没错,这回离开南京是悲鸿的意思;这意味着什么?难怪道藩要无奈地质问老天爷!
难怪他那瘦削苍白的面孔在强颜欢笑;表面上像是很洒脱,眼神里却一直在逃避着什
么……
“当当……”
船上敲起了小锣,那是要送行的人赶紧下船,因为船就要开了;碧微催了好几次,
道藩却充耳不闻。
“呜……”
突然,岸上传来警报声,几百个人顿时更乱成一团。送行的往下挤,搭船的呼天抢
地;船员们则急着开船,免得坐以待毙。鬼子飞机就要临空,这艘满载乘客的轮船,自
然是个大目标。
“嫂子!保重!到了汉口写封信报平安……道藩!赶快走吧……”
郭有守边喊边跑下船,到了岸上还朝道藩直招手……说时迟,那时快;一阵锚链拉
起的声音,船身已经在动了!碧微紧张得直发抖:
“道藩!……怎么办?船已经开了!”
道藩冲到船弦的栏杆旁往下一看,轮船果真已经驶离了码头;他回过头,苦笑了一
下:
“这样更好……我就能送你们一程了!”
“那怎么成!了然!快去找船长,就说内政部张次长送朋友,来不及下船,请他想
个办法!”
顾了然应声而去,不久就把船长带过来了:
“张次长!正好我们船公司也有两个职员来不及下船,我们这就安排一条舢板,请
您跟着他们回岸上去。”
内政部次长毕竟是个不小的官,难题就这么解决了;剩下的是舢板的安全问题。碧
微一直盯着那条小舢板,看着它摇摇晃晃地靠了岸,这才松了口气。
舢板上,道藩的手挥个不停;碧微再也忍不住,泪水就那么流了下来……
抗日圣战的火苗点燃之后的第一个双十国庆;汉口璇宫旅馆的房间里。
碧微一早醒来,看见窗外几乎每一栋建筑物门前都已经飘着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
是这战火把中国人煽醒的吧?望着还在熟睡中的伯阳和丽丽,碧微不禁在心里为他们叫
屈;小小年纪,也许不怎么懂得流离失所的那份痛,但却照样得尝着背井离乡的这份苦。
旅馆房间里的这张床,显然要比船上舱房里的舒服,就让他们多睡一会儿吧!
昨天抵达汉口的,前后走了三天;当甲板上有人指着江汉关那座巍峨的钟楼、叫出
声来的那一刻,碧微才真正意识到,自己踏上的也许是一条不知所终的路。
“笃笃……”
有人轻声敲着房门:
“徐太太!……”
是同弟的声音,碧微把门打开;同弟提着一个纸袋,坤生站在她背后。
“徐太太!这是您昨天吩咐的……”
“你们的呢?”
“……我们吃过了。”
纸袋里装的是早点。碧微昨天拿了点零钱给同弟;这趟出门不是旅行,是逃难,钱
得省着用,早点还是到外面买回来吃吧!
“同弟!坤生!你们进来坐一会儿,我有话跟你们说。”“是!”
两张椅子,一人坐一张;碧微就坐在床沿上。
“我直话直说,也不跟你们客气了,出门在外,得互相照应,刘妈一直很照顾我,
两个孩子跟她也亲;留她在家乡,我都有点舍不得。往后的苦日子还长得很,可不能跟
在南京的时候比,所以……你们得拿定主意,假如还愿意跟着我,那以后……”
“徐太太!我们跟着您出来,就是打算伺候您。”
“坤生说得对,是您把我们带出来的!我们当然跟着您!”
“那就好!往后靠你们的地方多着呢!我先谢谢你们!”
碧微衡量自己的经济能力,实在不可能养着两个佣人;坤生和同弟既然这么讲义气,
这件事就暂时搁下吧。
在碧微买好了船票、还没离开南京之前,道藩发痴似地每天写信;碧微走了之后,
他发现自己写信已经写上了瘾。
参加了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分别举行的国庆纪念典礼,下什回到家里,他又提起笔。
信上他告诉碧微,两场纪念典礼,蒋委员长都参加了;他看到蒋委员长态度安详、神采
奕奕,那是民族之幸。信上还说,南京一早就起雾,整座紫金山的上半部都罩在浓雾里;
这种天候,也许敌人的飞机来不了。他告诉碧微,听说上回欧战期间,德国和法国在对
方国庆日当天,都很讲究君子风度,互不攻击;但道藩认为,类似的情形决不能奢望于
最无礼、最野蛮、气度最狭小、最没有人性的日本鬼子!正写得慷慨激昂,客厅的电话
铃声响了;道藩从房里出来接听:
“喂……喂……”
奇怪!听筒里怎么没声音?
“喂……”
“……道藩吗?”
“是你?你在哪儿打的电话?”
“汉口!我们住在璇宫旅馆。”
“一路上都好吧?……孩子呢?他们好吗?”
“都好!你呢?忙不忙?……身体怎么样?”
“很忙!……国庆日也只有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