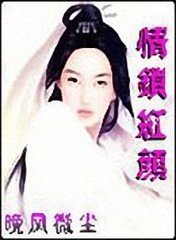回首碧雪情-第27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吕斯百的头垂得更低了,脸上的愧色也更重了。
说来也巧,就在第二天,碧微接到了还留在上海沦陷区的母亲写来的一封信:
“前几天接到悲鸿从新加坡写来的一封信,他虽然埋怨你个性太强、脾气太大,但
分开这么多年,他也体会到你的优点。他说,他愿意把孙韵君送给他的一枚红豆戒指转
送给你,表示他跟孙韵君之间不会再有任何瓜葛。棠珍!假如悲鸿真有诚意回头,你不
妨略加考虑……”
在办公室里看完母亲的信,碧微苦笑了。原来事情并不是真的那么凑巧;吕斯百昨
天才来过,虽然没有提到红豆戒指,但说的也几乎是同样一回事……
至于那枚红豆戒指,碧微倒是在悲鸿上一次回家住了五十天里,天天看到他戴着那
枚戒指。当时碧微听朋友私下提起过,那颗红豆真是孙韵君送的,镶的金边和金指环则
是悲鸿自己在银楼打造的。朋友还说,金子上刻了两个字:慈悲;“慈”是代表孙韵君
的别名“孙多慈”,“悲”当然是指悲鸿自己。
想到这儿,碧微几乎想大笑几声;这算什么?他要把红豆戒指转送给我,难不成要
我天天戴着?随时提醒我、要我记住他跟女学生的一段情?碧微抬起头,看见坐在对面
的同事梁实秋正在看报纸;她终于有了促狭的对象:
“实秋!”
“嗄?什么事?”
“徐悲鸿先生说,他要把纪念他跟他女朋友交往的红豆戒指转送给我。我看这么办
吧,我就毫不客气地收下来,然后把红豆挖出来送给你,至于金子嘛……卖了它,能卖
多少钱,我全部拿来请大家吃顿饭,你看如何?”
“你……你这不是存心作弄我吗?碧微!红豆可是相思之物,你要我跟谁相思呀?”
碧微是不怕梁实秋或任何一位同事取笑的;自从去年七月底那则通告周知的启事在
报上注销来之后,有谁不知道碧微已经片面地被“休”了?真快啊!去年七月底,都过
了一年多了!
碧微把吕斯百来访和母亲来信的事,都写信告诉了道藩;道藩在回信里又不停地自
责了:
“你为了这些事痛苦,让我饭都吃不下!看来这将是个永远解决不了的问题,你又
何必如此自苦……假如你真觉得自己已经陷于不忠不孝不义不贞的泥淖里,那自然都是
我害你的;我因为爱你而害你的!……我绝对服从你的命令,因此还是那句话,请你命
令我吧!你的任何命令,我绝对不分青红皂白地接受;既然爱你,就要懂得如何为了接
受你的命令而活!……”
碧微给道藩的回信里带着几许无奈,但更多的是心疼与抚慰:
“……一想到你那深深的情,我除了愧对你这唯一的知己之外,还有什么不满足
的?……每次提到我们的问题,你总是要我命令你,总是说你是为了接受我的命令而
活……我好心疼的傻子!你明明知道,连你自己都没有办法,你让我怎么命令你?……
你以为我是为你设想才拒绝了人家?你错了!我是为爱你才拒绝人家的!这两者是完全
不同的。……你我相爱之深,已经到了无可奈何的境地,却无论如何要时时刻刻自我克
制……还记得我以前常说的吗?男女之间最珍贵的爱应该局限于精神层次的,……如果
你真的那么爱我,那么我就凭着你的爱要求你……是要求,不是命令……答应我吧!从
此不要再去想那些‘永远不能解决的问题’……要知道,倘若你我之间的爱没有那些阻
挠,也许就平凡了!也许就不那么热烈、不那么坚决、也不那么久久长长了……”
写着写着,碧微猛然把时空拉回到将近三十年前。那个十二岁的小少女棠珍,当她
看着姊姊出嫁的时候,曾经懵懵懂懂地憧憬着什么;如今,将近三十年后,碧微能够把
自己和道藩之间的爱、与当年的憧憬之间画上一个等号吗?
好难的一道题目啊!
一九四一年三月三十一日。第二天是西洋人彼此促狭捉弄的万愚节,一群朋友在中
国文艺社聊天,徐仲年突然冒出一句话:
“各位!上一回悲鸿在桂林的报纸上登了那则广告,咱们明天也乐呵乐呵,替人家
登个启事怎么样?”
上一回?都快三年了!反正人一过了中年,心里明明在感叹时间过得快,嘴里却总
是不肯承认;总想把陈年旧事拉回来近一些,好自己骗自己。碧微着实不想提醒徐仲年,
因为她自己也都已经四十出头了!但碧微觉得挺好奇的:
“替谁登启事啊?”“替你跟悲鸿呀!替你们登个结婚启事,气气他!”
“气他有什么用?他看得到吗?”
“那……就登给自己看!登给你看!”
“随便!你明天登,我后天就否认!”
第二天,中央日报的头版果真有一则广告:
徐悲鸿蒋碧微结婚启事:兹承吴稚晖张道藩两先生之介绍,并征得双方家长同意,
谨订于民国三十年四月一日在重庆磁器口结婚,国难方殷,诸事从简,特此敬告亲友。
万愚节毕竟是西洋人的玩艺儿,广告注销来之后,很少人想到是个玩笑;当天在一
个会议上,张群就跟道藩说起,至少碧微和悲鸿还是相爱的,别人才拿这个开玩笑……
也有些人比较明白碧微和悲鸿的爱恨情仇,他们认为,如果是徐悲鸿和孙韵君结婚,
大家一定相信;而吴稚晖则觉得,也许这个玩笑一开,两个人真会重修旧好也说不定。
在成都的郭有守甚至立刻写信向碧微道贺,并且欢迎她和悲鸿到成都去度蜜月……
但不管怎么说,四月二日中央日报的头版,另一则广告也如期出现:
蒋碧微启事:昨为西俗万愚节,友人徐仲年先生伪借名义,代登结婚启事一则,以
资戏弄,此事既属乌有,诚恐浠乱听闻,特此郑重声明。
至于是不是有人会把这两则启事告诉远在新加坡的悲鸿,以及悲鸿知道了之后会有
什么样的反应,碧微想都不去想,……不!悲鸿这时候不在新加坡。悲鸿在一九三九年
底经由缅甸到了印度,和八十岁的老诗人泰戈尔成了好朋友,泰戈尔还带他去见了甘地;
一年后才又回到新加坡。而这是一九四一年的四月初,悲鸿这时候在马来亚的槟榔屿。
碧微家的客厅里,蒋梅笙的眉头蹙得好深;手里拿着刚读完的一封航空快信,那是
悲鸿从南洋寄回来的。发信的日期是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五日,他在信里向碧微提出一
个请求。
根据悲鸿的说法,林语堂通知他,“美国援华联合会”有意邀请悲鸿前往美国访问,
并且请他在美国举办第一流的中国现代画展。悲鸿信上说,他竭诚希望碧微能够同行……
蒋梅笙望着碧微,谨慎地表示了他的意见:
“由你自己决定吧!不过我得提醒你,还是先打听清楚悲鸿真正的用意是什么。当
然,时间非常紧迫,我也知道你们根本没有联络,因此,还是找那几位老朋友吧!从侧
面了解看看,尤其是他的学生,像吕斯百、顾了然这些人,悲鸿不是经常跟他们有联络
吗?”
蒋梅笙所说的时间紧迫,是因为悲鸿在信上要求碧微在七月二十日以前做出决定,
并且拍电报答复他;而这时候已经是七月初了。其实碧微心里已经做了决定;但面对一
向那么疼爱自己的父亲,碧微不能隐瞒这件事,同时也要听听父亲的看法。
“爹!听您这么说,那我就可以放心地下决定了……我根本不想去,也不可能去!”
“我早就料想到你的决定,但这毕竟是悲鸿很不寻常的一个举动!你跟我提起过吕
斯百送那封信来给你看的事,你娘给你的信我也看过了;虽然这中间隔了将近一年,但
有两点是可以肯定的。第一,悲鸿应该是已经跟那个姓孙的女孩子分手了;第二,这一
年以来,悲鸿确实想着要回这个家。碧微!你同意我的看法吗?”
碧微点了点头。这些状况,她自己也曾经想到过;但想归想,再进一步去分析、乃
至于有什么其它的念头,在碧微来说是不可能的。
碧微也曾经矛盾过;尤其当她想到那两个等于没有父亲的孩子,那股矛盾的感觉特
别强烈。但那是好一阵子之前的事了;最近一两年来,悲鸿那些让她伤心透顶、绝望透
顶、甚至鄙夷透顶、厌恶透顶的举动,像是悲鸿给自己贴上的一张张催命符,一切都绝
不可能起死回生了……
碧微的思绪写在脸部的表情上。蒋梅笙怎会不了解女儿?他从沙发上站起身,把悲
鸿的信交还给碧微,又拍了拍碧微肩膀,进房里去了。
这一天晚上,碧微提起笔给悲鸿写信,这是记不得多久以来的第一次。她先谨慎地
考虑上款该怎么写;考虑了一会儿,她写下“悲鸿先生大师道席”八个字。称呼有了,
内容反而容易得多:
……辱承惠书,荷蒙邀赴新大陆观光,盛意隆情,良可感激。然所以不敢奉命者,
诚因福薄之人,既遭摈弃于前,无论处境如何,难再妄存荣华富贵之想;抑且老父子女,
咸赖侍养,责任所在,固亦不容轻离也。
日昨奉书后,本欲先行覆电,孰意问询之下,一电十字,须耗百金。在此米珠薪桂
之秋,百金本不足言数,无奈在穷人视之,此区区者已足影响生计,故不得已,只有作
罢矣。两儿已渐长成,年来颇少疾病,丽丽下年亦将入中学肄业。此二人者倘有日成立,
则微毕生之责已尽,他无所望矣。
此覆敬叩旅安
蒋碧微拜启
第十七节
重庆歌乐山上的公墓里,一座新坟的墓碑上刻着“画家顾了然之墓”。碧微穿著一
身素服,眼眶红红的;送葬的人原本就不多,这会儿都已经下山了,只剩下碧微和道藩
两个人,周遭显得格外凄凉。碧微看着这般情景,想着这个宜兴的小同乡,眼角的泪水
忍不住又要掉下来;道藩轻轻抚着她的肩膀:
“入土为安,能够有你这位师母替他办好后事,了然应该会瞑目的……”
“可是我难过呀!……这么好的一个人,又那么有天分,年纪轻轻的就走了,连婚
都还没结……又只能葬在这儿,老家都回不得!”
“这就是战争!战争让多少人有家归不得!活着的、死了的,部里几个在南京沦陷
之后才逃出来的同事说,日本鬼子进城后,几十万人死在他们的枪下刀下;那些几十个、
几百个被一起杀掉的,事后靠着乡亲挖个大坑、就地把他们埋了,那有多凄惨!那些人
算是回到家了吗?”
道藩说得激动,眼里布满了血丝,双拳紧握;一点都不像平日那样的温文儒雅。
这是一九四二年的四月底。将近五个月前,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本大批飞机
偷袭珍珠港,太平洋上的战事终于爆发;美国在远东地区牵制了日本的军力,再加上先
前由陈纳德将军率领的飞虎队,这时候已经正式改编为第十三航空队,支持中国作战,
中国战区的情势开始有了正面的逆转,以前三天两头就要来轰炸重庆的日本飞机也不那
么嚣张了。
碧微这会儿想起四年前自己带着伯阳和丽丽逃出南京,一路上照顾他们的就是顾了
然!
碧微清楚地记得,在靖江轮上拍着照,空袭警报响了,轮船匆匆启航,道藩来不及
下船,就是顾了然找了船长来解决的。那副惊险、那种紧张,碧微不相信已经是四年多
以前的事。
道藩望着墓碑上刻的那几个字,苍劲有力,那是碧微请她父亲题的;从字想到画,
道藩很自然地想起这个英年早逝的画家:
“了然在绘画方面的天赋确实让人激赏,去年初的那一次画展,虽然有些人是基于
同情才买了他的画,但也有不少买主是识货的,他们认为花的钱值得!”
“那次画展还多亏了你……”
一年多以前,顾了然的肺病情况恶化,住在疗养院里的费用又高,吕斯百曾经帮他
办了一次画展。画卖得不错,连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都买了一幅;碧微认为那次画展办得
成功,主要是靠着道藩在各方面的深厚关系。
“我是说真的!凭了然三十不到的年纪,又只是中大的助教,哪有本事靠一次画展
就筹到那么一大笔医疗费用!……了然地下有知,对你这份情,他会感激的……”
画展的收入让顾了然在疗养院里又撑了一年多,但他还是走了……碧微突然想起,
这些都应该是另一个人的事!顾了然是那个人最心爱的学生,而那个人在哪儿?
巧的是,道藩这会儿心里也正想着一个类似的问题;像顾了然、吕斯百,他们都是
悲鸿的学生,为什么感觉上他们跟徐师母反而比较亲?不去想了,天底下有很多事,特
别是牵扯到人与人之间感情的事,总是很难用一把尺去量的!
道藩看了看天色,他扶着碧微的手肘:
“该回去了!”
“嗯!”
碧微又低头看了看那座新坟;再见了!了然!你安息吧。
悲鸿回国了;他是因为新加坡局势吃紧,随时会被日本人占领,不得不离开。他在
一九四二年一月底经由滇缅公路先到云南,在那儿待了好一阵子,还在昆明开了一个画
展;回到重庆已经是六月底的事,他住进了中国文艺社。
碧微得到消息;第三天中什,她在磁器口的家里准备了一桌酒菜请悲鸿吃饭,还邀
了几位朋友作陪。为了慎重起见,碧微前一天晚上托人送了张请帖到中国文艺社给悲鸿。
一起受邀的华林和陈晓南陪着悲鸿赴宴;悲鸿手里提着皮包,还带着一幅画轴,一
路上兴奋极了。
大门打开,只见碧微容光焕发,带着一脸爽朗的笑:
“欢迎欢迎!……”
“谢谢!……”
走在最前面的悲鸿嘴里好象还想说些什么,却说不出口;碧微已经把目光移到华林
身上:
“华大哥!爹刚才还在念着你,快请进!”
“他老人家还好吧?”
“很好,谢谢!”
一进到客厅,悲鸿愣住了。他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