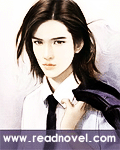岁月留痕-第6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里为他弄吃的时,我忍不住的哭。我不愿意姐姐知道我心痛小波,家里有好菜,我就站在门口悄悄的看他放学没有,看到了就装着碰巧遇上的,把他叫进家吃饭。
和姐姐的反目对我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另外待业人员里我是年龄较大的一个,有些应届毕业生比我要小八九岁,我有自卑感。所以在参加护矿队时我常常带本小说或杂志什么的一人坐在一旁看书,不加入他们打闹,在这些人当中,我没有一个能说知心话的。有一个比我年龄大的女生姓罗,我叫她罗姐,也是下乡知青,回来两年了没有安排工作,没有安排的原因是她在下乡时嫁给了一个农民,在农村生了三个孩子,所有的知识青年都招了工,她因为丈夫是农民没有给她工作,因为上面没有针对这类情况下有文件,她便成了三不管,成了受歧视的知青,她在这帮小年轻当中也感觉孤立和孤独,有时我俩也聊聊天,可是罗姐成天只会说她公婆怎么对她,说她老公当初怎么追她,还有油盐柴米之类的东西,不像我姐那么有思想,所以我与她之间的交流也不是很多。
走出洞口已是下午吃饭时间,书记问我上哪吃饭,我说自己在家煮,他说他上我家和我一起吃。他还说他带了好菜,因为书记家住在矿机关,机关离二坑就是沙木洞有十来里路,所以平日就很少回去。
书记就上他宿舍去把他从家里捎带来的菜拿来了,我烧柴火煮饭,用柴火、铁锅做的饭特别好吃,厚厚的锅巴又香又脆,书记一点架子也没有,非要帮着我来添柴,我很不自在,有些受宠若惊,不让他帮说自己能行,可是他非要抢我手里的火钳(那时烧火都用火钳和竹子用的吹火筒——现在的城里孩子们看都没看到过的工具)。抢火钳时,他的手捏到了我的手,我不知道怎么的,心跳脸红,我想让自己平静些,就是做不到。我感觉十分的尴尬,可是书记的样子很自然,我好盼望有个人来我家,打破这尴尬的场面。这时和平进来了,书记见到和平打了个招呼,然后问和平有事吗?和平说没有事,吃过饭没事出来转转。和平也是个老实人,见了当官的也没话说,也觉尴尬就走了,书记在我家边吃饭边问我一个人睡觉怕吗?我说那有什么怕的嘛,并开玩笑说那时流浪街头在矿长家屋檐下睡都不怕,现在在自己家里怕什么?
书记笑了,又问我一个人寂寞不。我一时答不出来,睁着眼睛看着他,一会才问他,他说的寂寞是什么意思?书记笑笑不答,让我说说我理解的寂寞。现在想想我那时真的很傻,真的和他讲起自己对寂寞的感受,我说我觉得一个人没有人懂,没有人理解,没有人倾诉,就是在人群中也会感觉孤独,在欢声笑语中也会感觉寂寞。书记愣了一下,装着很严肃的样子对我说,你和其他的待业青年不一样,你比他们有思想,以后你把我当知心朋友,有什么困难第一个找我,你有培养前途,什么包袱也不要背,工作会解决的;只要你听党的话,听组织安排,有想不开的地方多找我汇报。我万分感谢的给他沏了一杯茶,不过书记不喝茶,那天晚上我自己把那杯茶喝了,茶太浓,害得我一个晚上没合眼,从那以后我懂得茶喝了睡不着觉。
我特别喜欢孩子,隔壁的邻居黄姐生了个儿子,样子十分可爱,每天晚上我都上她家逗孩子,这天吃完饭不见我出去,黄姐就大声叫我,书记听到就走了,走时做了个鬼脸丢了个眼神,说实话,那时我还不知道什么是媚眼。
书记第二天又下来视察工作了,又说上我家一起吃饭,我有些紧张,因为和当官的在一起放不开。我就想起了知青罗姐,把她也拉上了,一开始书记不高兴,说我怎么和一些结了婚有孩子的人玩到一起,说姑娘家应该天真活泼,可是罗姐对书记非常热情,总有话找书记问。罗姐在时我就不觉得受宠若惊了,也不觉得尴尬了,所以只要书记来我家,我就把罗姐拉上,罗姐也特别愿意。后来书记就不来我家了,改上罗姐家了;再后来罗姐的邻居就说罗姐的坏话了。因为罗姐住的房子最差,原因是她虽然回矿了,但是不是职工,没有分房的权利,只能自己找房,她就只能住在山上一栋破烂没人管的房子里。那房子还住着一户退了休的老俩口,俩老的儿女不在汞矿工作,老人住在山上的房子虽破,但是宽敞一些。房子不隔音,儿媳妇曾告诉过黄姐,说公爹不好,儿子儿媳在家也这样疯,和老太太弄得床嘎嘎响,可那时的我20好几了,还一点不明白这话的意思。
燕书记和罗姐的闲话也就这样传开了,只不过我当时没听到,是后来我的工作没解决,爸爸用这话骂了燕书记,并向矿里反应了这情况。
又到了年底自然减员了,我去找燕书记,请他帮我。燕书记不像原来承诺的那样热情,有些吱吱唔唔的,我又去找郭伯伯郭副矿长,郭伯伯告诉我很困难,按理说这次名额是该给我的了,可是阻力很大,原因是坑口燕书记要保罗姐,因为我们坑在我与罗之间只能解决一个,在当时人们的眼睛里,结婚生子了的知青、特别是嫁给了农民的知青,是知青里社会地位最低的,就是地方上解决工作也是这样,很大一部分这样的知青的工作都是最后所有知青解决完了才解决的。为这事郭副矿长和坑口的燕书记吵了起来,这一吵就在矿里产生了两派,为了平熄争论,矿里来个决定:一个都不解决。
又到了81年自然减员了,名额一下马上就分完了,罗姐工作解决了,因为燕书记还在坑口当书记。按理说罗姐解决工作也是应该的,这是我自己当时的看法,我一直没有因为没得到工作对罗姐本人有意见,我觉得她也是时代的牺牲品。可是为什么我就一定不能有工作呢,跟我一样条件的不是都解决了吗?我哪点也不比别人差呀,有年龄比我小的、家境比我好的、没有在农村生活过的都得到工作了;还有,优先知青,可是我比知青吃的苦头多得多,起码知青不受政治歧视吧?不是为我爸爸平反了吗?那为什么我还要受这不平等的待遇?文革的错误是盖棺定论了吗?为什么我要永远当这个错误的牺牲品?我没想通,我意识到这样等下去是没有止境的,我马上跑到贵州省劳动厅反应情况,省劳动厅人事局让我给冶金局劳资处带了个条子,让冶金局处理此事。到冶金局已经很晚了,人们正好下班了,我堵住了劳资处处长,处长姓董,听说他父亲就是冶金局的局长,董处长比我大不了几岁,他听完我反应的情况,有些同情,他说明天讨论一下再回答我。冶金局离哥家太远,我不想上哥哥家,不想让大哥知道我来贵阳了,不想把自己的情绪带给他们,他们为我愁也帮不了我什么忙,冶金局办公室的火炉烧得很旺,我告诉董处长这晚上我就睡这办公椅了,董处长说不会吧,我说是真的,我说没钱住招待所。他又急着回家,他说那我不管你,你要是说真的,你就在这吧。他走时,说要锁门,我说不用,我就在这里过夜,他说不行,我生气的问他,那我上你家?他无奈的摇头走了。
那晚上我就自己添火,真的在冶金局办公室呆了一晚上,心里越想越气,一个晚上没睡。第二天人们来上班了,有些提前下班没见到我的人,用怀疑的眼光看着我,不知道我是来干什么的,有些见到我和董处长说话的也很吃惊,说妈呀!真行啊!董处长来了,他也大吃一惊冲我说,你真的在这里过夜了,我说是,如果你们不解决我就把被子搬来。董很客气的对我说,我理解你的心情,是不小了,要是有个工作,也该成家了,你在这里坐着等,我们开个会。中午11点左右,董出来告诉我,赶快回去,他们给了两个名额给汞矿,估计矿里会给我的,说他们也打了招呼,还说矿里也来人要名额了,矿里的人已经走了。
那时每天只有一趟火车上大龙,矿里的人有小车,而我只能赶火车,但是火车已经开了,还好当时贵州汞矿有个转运站设在贵阳冶金局,为爸爸落实政策,这些年间我们姐妹早和转运站的人混熟了,这里的每一个人对我家和其它受迫害的人们都很同情,只要是有便车都会帮我们找。下午两点,转运站的赵叔给我找到了便车,其实驾驶员在为爸爸落实政策这些年中我们也都熟了,司机比爸爸年龄小几岁,姓姚,他听说我为工作的事来贵阳,也很生汞矿的气,他说他开快一点,争取天亮赶到万山,可是天气不好,有些地方已经结冰,车只能慢慢的走,等我们赶到矿办公室已经下午了。办公室主任告诉我名额已经分下去了,只有等明年了,我就找他们论理,我说冶金局董处长告诉我的,有我的一个名额。他们说实在没办法名额已经分了,后来才知道,有一个多子女的老实工人,家里生活实在困难,这次本该解决的,却没能解决,而矿里当官的子女大大小小全解决了,这个人一气之下拿了劈柴的虎头,去了矿长办公室,把矿长们吓坏了,这名额就给了他。可是还有个名额啊,我只有找劳资科长,科长只能说好话,还把副矿长叫来一起做我的思想工作,说了很多困难家庭的情况,我也觉得有些家庭的确也困难,可是既然矿领导知道这么多的困难户的孩子需要解决工作,为什么这些领导家的子女却不到年龄就都工作了呢?再说全矿还有一个我这样大的未婚女青年没工作的吗?闹也闹了,说也说了,名额已经分给别人了,只好再等吧,再说我这人一贯吃软不吃硬,他们已经承诺明年解决就算了。但是我变得不爱说话了,在落实政策那些年,在农村那么苦,我们姐妹在一起都常常开怀大笑,现在妹妹读书走了,姐姐走了,我怎么也笑不起来了。
82年的自然减员又到了,那些天天天下雪,每当这时候家家有子女待业的都开始活动,我也找了坑口和矿里,提醒他们去年对我的承诺。可是这些天矿领导很不好找,他们知道找的人多,都不在办公室,听说名额就分完了,还是没有我的,我知道矿里还是因为我为爸爸落实政策的事报复我。那天我上舅舅家,舅舅家就住矿办公室旁边,舅舅告诉我,自然减员马上结束了,明天各单位负责搞这工作的都要来矿里开会,舅舅是福利科科长,开会要就餐,所以舅舅知道消息。
天下着鹅毛大雪,我踩着半尺多深的雪,走到了矿办公室,会议已开了一会了,因为冷,会议室烧着煤火,我推开门,室子里一大股暖气扑面而来。很多人把头转了过来,有些人认识我,因为我们姐妹在万山为爸爸落实政策闹得太凶,知名度很大,走到哪里都有人在背地里介绍我们姐妹的情况,地方小了,有一点事就一下子传开了,认识我们的人一见就知道我是为要工作来的,很快的向旁边人悄悄介绍。这时正在作报告的矿长,也是曾经欺骗过我后来又说我冲击会场的那个矿长,他一直对我们姐妹耿耿于怀。矿长看到我很凶的问我来做什么了?我说为要工作,他说你没看到在开会吗?接着很凶的对我吼叫:“给我滚出去!”我正在气头上,他却给我一个下马威,我不理他,站在他站的地方,对大家说了我的情况,从落实政策说到这些年的自然减员,我说得很快。矿长叫散会,可是没人动,个个都静静的听,矿长多次叫散会,后来矿长说你们不走我走,他自己说着冲出了会场,别的人也开始慢慢的离开,有人从我身边过时悄悄的给我树大姆指,有些人见矿长不在就小声说,本来就不合理,让我们来我们也只是个傀儡,没有一个人当着矿长的面拍马屁训斥我的。
人们都走了,我没走,矿长返回了会议室,他是来拿茶杯的,我堵在了门口把门反锁了,他问我想干什么?我说我什么也没想干,现在只想听他道歉,他冷笑,我拿出了口袋里的牛角刀,一把非常锋利的当时很流行的牛角刀,我拿着刀削指甲,我告诉他,我没工作我感觉活下去没意思,但是我想为人类办件好事,除掉几个混官,让其他像我一样的人们不再受迫害,矿长吓坏了,他开始向我道歉,并不停的说他和我爸爸一样大年龄,让我为我爸爸着想,我出了事我父亲会怎么难过,我告诉他我死了我父亲身上的负担就轻了,因为我不能看到我年迈的父亲养活我,我还问他,他也是为人父的人,为什么看到我时没有一点同情心,他在骂我时为什么不想到我父亲的感受?除非他不是个人,他也不停的承认自己不对,他说他愿意当着大家的面给我认错,说他不该当着大家的面骂我混,伤我的自尊,后来他说他一定解决好我的工作问题,我说我知道你说话和放屁一样,因为我不止一次的领教过他,他说让我放他出去,我说可以,但是我要把你肚子里的饭放出来,我要看看你这么没良心的吃的是什么饭,他吓坏了,说小尤,你陪我死你合不来,我以前做得不对以后我改,你一定要冷静,给我一个机会给自己一个机会,事情弄到这一步不是我一人的错,是社会造成的,我把他关了三小时,人们吃了中饭又来上班了,有些人没去吃饭,不停的在外面叫门,帮说好话,我看他说好话的样子可怜,心里有些软了,他说要撒尿,我说就拉这里吧,命都不要了还要这么多脸?他流泪了,我看他可怜把他放了,矿书记把我叫过去,让我吃了一碗在食堂打来的饭。
第二天星期天,雪更厚了,矿里副矿长和劳资科长,组织部长踏着深雪走路上我家了,10里多路,很难得让他们在这样的天走路,一进我家门问我爸爸,桂兰上哪里了,爸爸说不知道,劳资科长说坏了,老尤啊,你一定把你女儿追回来,别让她干傻事,组织部长还吓我爸爸,我爸爸说我这么大了该让社会管了,这时我回家了,他们三人轮流向我赔礼道歉,还说矿长本来亲自来的,因雪大腿又不好才没来,并答应马上下文把我列入知青名额,(不久真下了个这样的文,但是永久都没有实行。)过了一些日子听和平的弟弟说学校开大会时提到了我,让所有年轻人别向我学,胆子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