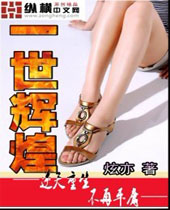大敦煌-第8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曹延禄正让薛宝成举起蜂蜜罐子朝方天佑头上浇下,以引来密麻麻黑压压一片毒蚁,用恐惧折磨方天佑,忽然听到有人高喊:“住手!”曹延禄、薛宝成和众兵丁寻声看去,就猛地看见秋红和无尘法师登上沙丘,迅步跑来。曹延禄一见秋红,吃惊
道:“啊?秋红姑娘怎么来了?”秋红见方天佑遭此惨绝人寰的酷刑,目不忍睹,不由怒火万丈,愤而斥责道:“曹延禄,你真衣冠禽兽,毒蛇心肠,对方学士竟下此毒手!你速速将
人放了,否则姑娘要你狗命!”曹延禄并不怯惧,反而狞笑道:“怎么,秋红姑娘心疼了?你先说你怎么来了?”秋红道:“好人自有天助!你想背着曹大人和夫人,设计陷害,官报私仇,姑娘我便不管么?”秋红说得是,曹延禄刚将方天佑逮去,副监工孙家庆就慌忙去找无尘法师。无尘法师惊得几乎眩晕过去,知此人命关天大事,非节度使曹大人才能挽救。于是马不停蹄,飞也似的赶到节度使府。不料遇见秋红,言及曹大人和夫人去瓜州劳军,先天已经走了。无尘法师失魂落魄地告诉秋红:学士被抓,正受酷刑,命在旦夕,曹大人不在,如何是好?秋红惊得五雷轰顶,两眼发黑。无尘法师催促道:“秋红姑娘,学士此刻处在九死一生的危难关头,阿弥陀佛,得快些设法搭救才是!”秋红到底聪明,危急处见机智,略一思忖道:“法师,学士罹难,姑娘我义不容辞,甘愿冒死相救。你先快去,姑娘我想想办法,随即赶到。此刻,秋红和无尘法师同时赶到,见学士如此惨状,令曹延禄立即放人。曹延禄道:“他是西夏奸细,如何放得?”秋红倏地从怀里拿出一面令牌喝道:“奴婢有大人的虎头令牌,谁敢不放?曹延禄惊疑道:“你个使女,哪里来得虎头令牌?”秋红猛将令牌扔给曹延禄道:“哼!拿去细看!”曹延禄拣起令牌,左看右看,毫无疑点,却依旧不死心道:“这……”秋红威吓道:“已验过令牌,为何还不放人,莫非造反不成?”曹延禄万般无奈,一咬牙恶狠狠地吩咐道:“放人放人放人!”
曹延禄好不容易逮着个报复方天佑的机会,却被一个小小的使女持了虎头令牌救走。他岂能善罢甘休?回到住处,曹延禄挖空心思,满腹狐疑:既是持了虎头令牌,勒令放人,节度使府,文官武将,差官成群,何派一个使女前来?曹延禄想到此,顿生疑窦,立即着薛宝成去城中打探。当晚薛宝成快马归来,曹延禄迫不及待地问及虚实。薛宝成喘着大气禀告道:“曹大人和夫人前日去瓜州劳军,午后才刚刚回到敦煌城中。”曹延禄听了,拍案惊叹道:“果然不出所料!”薛宝成也猜疑道:“莫非秋红拿的虎头令牌是趁曹大人不在偷盗来的?”
曹延禄顾不及回答,就令薛宝成备马,他要连夜赶赴城中,亲见节度使哥哥,问个明白。
曹延禄带着薛宝成,披星戴月,快马加鞭,犹如两个黑色幽灵,飞也似的奔驰在夜色笼罩下的茫茫戈壁,直到月落寅时,才到城里。曹大人及珍娘因白天劳军回城,身体困倦,此刻正沉沉深睡,忽听门卫惊动,说千佛洞监工曹大人有急令交回。曹顺德睡眼惺忪地从梦中惊醒,惶惶惑惑裹衣来到大堂,点燃蜡烛,睁眼看时,竟是弟弟曹延禄双手举着虎头令牌,跪在堂前。曹延禄见哥哥坐定,大声禀报道:“哥哥,小弟特来交令!”曹顺德惊魂未定,急问道:“半夜三更,你交的什么令?”曹延禄遂将令牌送上,回道:“请哥哥查验。”曹顺德接过令牌一看,大惊失色,问道:“啊?虎头令牌!你从何处得来?”曹延禄道:“小弟前日在莫高窟抓到两名西夏奸细,正在审问之时,秋红姑娘手持令牌,命小弟将奸细放走。”曹顺德听得云山雾罩,糊里糊涂,问道:“你说什么?秋红?奸细?”曹延禄道:“是的,小弟捉住西夏奸细,秋红持了虎头令牌,勒令放人。小弟猜想哥哥有甚锦囊妙计,已按旨意,放走奸细。”曹顺德听言大惊,失手将令牌掉落在案,追问道:“这虎头令牌,可真是秋红所持?”曹延禄佯装糊涂道:“秋红莫非不是哥哥派遣?”曹顺德震惊得脸色铁青,驳斥道:“满口胡说八道!此虎头令牌,一直藏在我的房中,岂能随意发出?”曹延禄故作惊讶道:“嗯?那难道是秋红姑娘盗出令牌,假传旨意不成?”曹顺德拍案而起,怒道:“这死丫头真是胆大包天!”曹延禄火上泼油,趁机煽惑:“哥哥,这虎头令牌,非同小可,大可号令三军,小则临阵斩将。如今大敌当前,发生这等事,岂能当做儿戏?”曹顺德火冒三丈,拍案道:“快叫你嫂嫂来!”曹延禄忽想起前次方天佑砸经房一事,硬是叫嫂嫂放过。今秋红犯事,又叫嫂嫂,岂不……于是曹延禄又明知故问:“哥哥,此等大事,叫嫂嫂做甚?”曹顺德道:“按曹府规矩,严加管束。”曹延禄一听,差点儿像猪尿脬撒了气。于是赶忙沉下脸顶道:“哥哥这就不对了!按大宋律条,盗虎头令牌者,罪在当斩。哥哥执法如山,对盗令牌这样的军法大事,岂能使用家规,徇情枉法?”曹顺德一时语塞,又略一思忖,就传令道:“来人,去将秋红给我拿了!”
秋红甘冒生死,盗得令牌,救下方天佑和老田头,虽自知一旦事发,罪在杀头,可她知道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于是,不但自己坦然待之,而且对方天佑和老田头也只字不露。救下方天佑当日,秋红并未急于回城,而是来到方天佑房里,为其煎药看护,悉心照料。方天佑被救;不明内情,又见秋红如此关爱,真是感激涕零,就常常言及感恩戴德,深谢救命之恩等语。而秋红自然回答,奴婢理应如此,学士何必客气,要紧的倒是舒缓心绪,息养身骨。方天佑道:“学生只不过干渴难耐,身子并无大碍。”秋红嗔怪道:“还说没大碍呢,差点
都成了荒漠白骨!”方天佑想起老田头,关切道:“不知恩公如何?”秋红宽心道:“学士放心,无尘法师正给他疗伤哩!”方天佑叹道:“唉!没想到恩公逃出虎口,反进了狼窝,受学生株连,又遭此劫难,实在不幸。”秋红又几番宽慰,方天佑身心渐渐康复。
秋红在莫高窟待了两日,见方天佑和老田头身子均有好转,就辞别无尘法师,飞马回城。原想着到节度使府,对珍娘言明真情,乞请处置,却未料到,在节度府门前,刚翻身下马,正朝里走,就被早埋伏好的兵丁挡住去路,团团围住。秋红姑娘不知曹延禄早已告发,就厉声喝道:“让开!也不看看是谁,竟敢围挡!”守卫头目听罢,讥讽地笑道:“小人奉命,在此正是专门等着捉拿姑娘你呢!”说完便扭头吩咐道:“拿下这个使女!”
中部 发现与劫难(公元第一千九百年,即清光绪26年间的故事)
导言
寰尘烟云,历史无情。中华自周、秦、汉、唐在西北大地几度辉煌,至宋及五代后,社会动荡,国政衰腐,山河破碎,民不聊生。随着自晋开始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中心东移,就把一个千年文明、几度辉煌的华夏西北抛向历史的荒漠。与此同时,在宋仁宗景祐元年,由敦煌节度使曹顺德、学士方天佑及无尘法师等众多爱国人士以身报国,将一大批敦煌宝藏藏于千佛洞藏经洞内,使之在宋初至清末的近一千年里,真正成为扑朔迷离的千古之谜。
到了清末光绪年间,中华大地全然已是满目疮痍,衰败至溃。此期间,随着列强的铁蹄从南到北,由海上踏入中华大地,掠地劫财,欲图殖民,而英、法、俄、德等国所谓的文物考古队,都趁了清政府无力西顾,纷纷经由西藏、新疆潜入中国昔日无比辉煌的西部,以勘察考古为名,到处搜寻,狂挖滥掘,大肆掠抢,根据有关藏经洞的传说,妄图解开这千古之谜,将敦煌宝藏全部窃为己有,掠往他国。
就在这时,爱国志士、清王朝最高画院“如意馆”侍郎秦文玉得知去敦煌采玉的哥哥秦志良无端失踪,于是离京远赴敦煌。在长达半年的荒漠寻觅中,未得哥哥任何线索,倒是引发了一个石破天惊的发现:修复千佛洞壁画的画师王庆祥和道士王圆GB982,因一个偶然的机缘,无意间发现了被称作千古之谜的藏经洞,使近千年前由方天佑、无尘法师等爱国人士密藏的国宝重见天日。但祸因福起,此闻一出,已潜入中国西部的英国考古博士贝克及法国传教士约翰与官府及精通英语的古董商姜师爷勾连一起,挖空心思,千方百计,要将已发现的敦煌宝藏掠为己有。而秦文玉和发现者王庆祥、骆驼客冯大刚及未婚妻杏花等与被官府诬为匪帮、实为揭竿英雄的白莲、刘大魁等精诚为伍,披肝沥胆,出生入死,与贝克、约翰等斗勇斗智,迂回周旋,几经曲折,双方得而失,失而得,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粉身喋血的争斗,在大漠敦煌演绎了一曲惨烈悲壮、千古绝伦的历史悲剧。最终,由于官府口蜜腹剑、两面三刀,与洋人里勾外连,暗中设谋定计,剿内助外,全数剿杀了护宝的爱国志士,并护卫洋人将掠夺的全部国宝越境运往国外。尽管出境前,又因洋人自相分歧,贝克以一个令人恐怖的下场葬身荒漠,但所获宝藏终归还是被洋神父约翰全部掠往他国。
中部 发现与劫难1
发生在公元1900年、即清光绪二十六年间的一起疑案,引发了一个石破天惊的发现,而这个惊世的发现因为华夏大地外强践踏、政体没落、盗贼蜂起,给名城敦煌带来无尽的劫难。
当年秋末一天上午,清王朝最高画院“如意馆”侍郎秦文玉正在与众学士义愤填膺地议论外强侵入,国宝流失,特别是殷墟龙骨被洋人收买的盗墓贼盗走,准备联名上书朝廷之时
,忽闻奉命为造慈禧墓和皇上墓,与其兄秦志良一起远赴新疆和敦煌,征调闻名遐迩的和田玉和祁连玉的工部外郎李政元将回京城。秦文玉喜出望外地听到这个消息,激动得热泪盈眶。因秦文玉自小父母双亡,是其兄秦志良一手含辛茹苦地将他养大成人。其兄征玉已离京两年,因此一听李政元和哥哥回到京城,就恨不得当即相见。
秦文玉匆匆离开如意馆,飞马来至京郊长亭,备下酒菜,要为其兄秦志良和李政元接风洗尘。秦文玉焦急地在长亭前等待、张望,突见一匹坐骑从远处飞奔而至,却只有李政元而不见其兄。李政元翻身下马,道:“秦大人,久违了。”而秦文玉却只简单应一句:“李大人一路辛苦。”就迫不及待地问:“我哥哥呢?”李政元叹气道:“说来话长,进亭慢慢叙说吧。”李政元和秦文玉进了长亭,刚在石鼓上落座,秦文玉又焦灼地问道:“到底出了什么事了?”李政元蹙眉道:“两年前我和令兄奉命前往西域征调玉料,因和田玉、祁连玉分出两地,我俩便兵分两处,令兄驻守敦煌采祁连玉,半年前不知因为何故,突然深夜出城,从此便杳无音信。”秦文玉听了,当即如五雷轰顶,大惊失色道:“什么?你说什么?”李政元道:“传言,令兄在敦煌采玉时,突然采到价值连城的稀世珍玉,一时财迷心窍,连夜逃遁了。”秦文玉心里像被尖刀猛刺了一下,倏地站起来道:“不!家兄绝非此等贪财小人!”李政元点头道:“卑职深知令兄为人,也不相信,于是派人四处寻找,可是大漠无垠,寻人如大海捞针,寻了月余,仍不见星点蛛丝马迹。”秦文玉深追道:“难道哥哥走时没留下片言只语?”李政元这时从怀中掏出一卷纸黄页皱的残卷,道:“只留下这个。”秦文玉打开卷轴,是一卷笔力遒劲的手抄经卷,卷轴里夹着一撮白毛。秦文玉指着白毛,惊疑地问道:“这是什么?”李政元道:“卑职也不明白,只听说令兄一年前偶得此物,从此便忧心忡忡,坐卧不宁,而且行踪诡秘。依此看来,令兄失踪,可能与此有关。”
秦文玉拿起经卷寻思半会儿,最后下了决心回如意馆找侍郎杨文林。杨文林道:“我有事正要找你呢。我们联名给朝廷的奏折给打回来了。老佛爷说,你们这些画画儿的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秦文玉叹道:“古人云,失九鼎,夏周亡,如今国宝流失,怕也是丧国之兆。”杨文林痛心道:“眼下国难当头,我们怎能在此安心作画!”秦文玉道:“文林兄,小弟回馆正是要向你告假去敦煌的。我哥秦志良随工部外郎去敦煌征玉,不幸失踪,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且受不白之冤。文玉自幼父母双亡,多亏哥哥辛劳养育成人,如今不明不白失踪,文玉理当去敦煌弄清真相,为哥哥洗冤。若不幸遇难,也要找到遗骨,扶灵回乡安葬。”杨文林皱眉道:“大漠瀚海,贤弟哪里去找?”秦文玉掏出残经道:“文林兄,你看看这个,可知出自何处?”杨文林接过残经,观看半会儿道:“字是好字,笔力苍劲,深得魏晋真传,至于出处,只有行家里手方可辨认。贤弟不妨去琉璃厂找多宝斋老板咨询。”
秦文玉没停,拿了残经来琉璃厂多宝斋找掌柜打问。多宝斋掌柜与秦文玉是老熟人了,接过经卷,仔细看了半会儿,大惊道:“哎呀,大人从何处获此宝物?这可是六朝之前的稀世墨宝啊!”秦文玉道:“掌柜何以见得?”掌柜道:“一是纸,二是书法。古人书写都用木笔,隋代后才使毛笔,而这字,笔画圆润,蚕头磔尾,不见笔锋,显然为木笔所书,故断定必是六朝之前墨宝。”秦文玉又问:“噢?这么说,掌柜从前还见过同样墨宝?”掌柜点头道:“西什库洋教堂的福里德酷爱书画,想来你也认识。半年前他拿来同样一个残卷,让小人鉴别真伪。小人刚才粗粗一看,还以为是福大人那个哩。至于此宝出至何处,最好还是去问问福里德大人。”
于是,秦文玉又拿着经卷到教堂来找福里德。福里德此时正在祭台上整理圣器,见秦文玉走进教堂,忙迎上来道:“主啊!什么风竟把秦大人吹来了?”秦文玉拱手道:“在下想跟福大人打听件事。”福里德笑道:“秦大人只管说,何必如此客气?”秦文玉道:“听说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