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时期的樱桃 作者:王江-第24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牲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他从医生那得知父亲已到癌症晚期,癌细胞已转移,父亲正经受着病痛的折磨。他用热毛巾擦去父亲头上沁出的汗珠,父亲额上深褐色闪亮的疤痕还历历在目,那是戴铁高帽留下的印记,将伴随他走完自己的人生。鲁岩望着这触目惊心的伤疤寻思着,为什么总让智慧戴上紧箍咒,而让愚昧去横行呢?
在家的几天,他仿佛是在炼狱里度过的。父母亲的工资早已扣发,银行存款也已冻结,一人每月只给十五元的生活费,妈妈想给父亲买些营养品,由于囊中羞涩而力不从心。妈妈尽量节俭,给父亲做点好吃的,可父亲也吃不下,还嫌妈妈乱花钱,叫她节省点用,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在陪伴父亲的日子里,他和母亲一来到父亲身边,父亲总装作轻松的样子,露出亲切的笑容,父亲不愿再让亲人分担他的痛苦。父亲在病痛中没喊过一声疼,叫过一声痛。鲁岩看到父亲因疼痛而渗出的颗颗汗珠,由衷地钦佩父亲的意志力,不为任何困苦所屈服,活得像一个顶天立地的硬汉子。鲁岩耳濡目染了父亲特有的骨气,笑看人生,乐对病痛,从不悲观失望。父亲还劝同房的病友,要鼓起勇气战胜病魔。妈妈送去一点好吃的,他会让病友们一起分享。在病床前,父亲交代他床下木箱里有一些手稿,虽是片断的思考,也许对社会有一定的参考作用,希望他帮着整理一下,等待时机再发表。父亲对中国的发展充满着期望。
鲁岩回到家里,从床下拉出一个破木箱,翻出父亲的文稿。里面什么样的纸片都有,有大字报的边角料,有旧报纸、旧账本、旧信笺,大都用铅笔写在纸的背面,纸长短不齐,折得皱皱巴巴,字迹写得很潦草,有的字迹已模糊不清,这些都是父亲在牛棚和农场里悄悄写就和掩藏的。望着这些乱七八糟的纸片,他感到了智者的悲哀,当智慧变成了贼,人人喊打,见了愚昧而抱头鼠窜之时,也是国家危难之日。他用手轻轻抚平皱巴巴的小纸片,又感到了智者的坚强,智慧的头颅永远是高昂的,智慧之火终将烧开地狱之门。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当和煦的春风吹过,智慧将在烈火中散发出奇异的光彩,生出茂密的枝叶来,国家兴盛,民族振兴之日也为期不远了。
灯光下,母亲也帮着整理父亲的文稿,这些文字有些是藏在她身上带回来的。她认真地把一张张纸片用手展平,手法十分的娴熟,她的手轻轻的,生怕撕破了小纸片,她对纸片的每一次触摸,仿佛在抚摸着自己的至爱。泪在她眼里打转,她在思念着什么,她是否在怀念同父亲一起那些阳光灿烂的日子。她曾是清华的高材生,在校期间,她听父亲的一次讲演,被他机智诙谐的话语所打动,从而深深地爱上了他。在反内战,反饥饿的大游行中,她用稚嫩的臂膀挡住了打向父亲的军棍,她的鲜血染红了父亲的长衫,渐渐走进了父亲的生活。在以后艰难的日子里,她始终不渝地陪伴在父亲身边,给他精神上的抚慰。她坚信父亲的无辜,她期盼过上一段清静团聚的生活,这种生活曾是那么的遥远又近在眼前,变做无言的酸楚,人生之长痛。为了给儿子一些宽慰,她总是那么一句话:“你爸爸的病会好的,肺癌不容易转移,连医生都这么说。”鲁岩望着妈妈头上生出的根根白发,心里不是个滋味,才五十岁的人就这么苍老,想当年校花的风韵已荡然无存。在儿子眼里,妈妈永远是漂亮的,妈妈那么地爱爸爸,今天,她本不想回来整东西,想多陪陪爸爸,照料照料他,可爸爸不同意,她才依依不舍地离开病房。她十分珍惜这段宝贵的时光,在农场她和父亲也难得见一次面,这次回来陪爸爸看病,也是谢晓燕父亲说得情,才有这难得的相聚。可团聚与永别这么近在咫尺,而让人情断衷肠。
鲁岩知晓妈妈一直在建筑设计院工作,这么多年来,她主持的建筑设计多次受到专家好评,其中的一项建筑设计曾获得过全国的设计大奖,妈妈一直因为父亲的问题受到单位的歧视。父亲被打成右派之后,单位领导曾劝她离婚,她断然拒绝了。由于阶级立场不坚定,从此被打入另册。调资调级没她的份,别人干不了的活都堆在她那里,害得她经常加班加点。不过她酷爱自己的专业,她认为建筑是城市的雕塑,是凝固的音乐,是文化的象征,是一门独特的艺术。为了营造新中国都市的风景线,自己多吃点苦也无所谓。由于她过于追求完美,反对火柴盒式的住宅建筑模式,经常跟领导发生争执,结果弄了双挤脚的小鞋穿上了,辛辛苦苦的劳动成果变成了字纸篓里的一堆垃圾不说,连设计的活也不让她干了。让她打杂,扫地、拖地板、倒垃圾,最后糊上了她最讨厌的火柴盒。而那些千篇一律照搬照套的设计人员则红得发紫,连单位的清洁工都说:“这设计的是个啥,这活俺儿子也能干,还没俺儿子搭积木搭得好看呢。”“文革”中,单位的造反派一直逼她揭发父亲的问题,她一个字也不说,最后关进了牛棚,受尽了磨难,可她嘴里从未有一句抱怨父亲的话。他凝望着母亲瘦骨嶙峋的肩膀,在中国知识女性柔韧的身躯里,饱含着多少不屈和坚强,在那花白的头发下,闪烁着睿智的聪慧和永恒的爱情之光。
鲁岩懊恼自己的无力与无助,他不能为父亲减轻一点病痛,也不能帮母亲分担一点忧伤,给家里帮不上什么忙。只能尽力地整理好父亲的这些文稿,宽解一下自己的烦恼,趁着父亲头脑还清晰,让他再看看,审审稿,说不定他还有更多更好的想法呢。可他的身体已不堪重负,说不定会加重父亲的病情,万一有什么三长两短,怎么向母亲交代呢,这使他疑虑重重,而难以解脱。他坐在断了一条腿用砖垫起的桌前,在杂乱的纸堆里拿起一张张纸片,细心地看着,上面写道:
无论怎样的社会形态,与其注重它的称谓,如革命委员会等,不如注重它的实质。看它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人民生活的改善,有利于人们享受到更多的民主与自由,而不是在民主的幌子下步步走向专制。
民主不是一个空泛的概念,而是决策的根本。与其决策的果断与失误,不如决策的稳重与科学,因为前者损失会更大。就像家里买的家具,起码也得征求一下家庭成员的意见吧,如果你买回的椅子根本没人愿意坐,那还买它干啥?既浪费钱,又占地方。因此,国家决策应得到人民的广泛认同才行。民主是对权力的有效制约,能有效防止个人权力膨胀而造成的浪费与腐败。西方人认为任何一个官都会是贪官,要严加防范;中国人认为任何一个官都应该是清官,要多加以歌颂,导致中国历代吏治问题层出不穷。官员利用手中的权力制造的腐败应包括:无辜伤害公众生命和侵害他人人身自由,以及掠夺公共与他人财产,而不仅仅是贪污腐化。绝对的权力造成绝对的腐败,没有民主制约的权力是腐败的温床。因此,我们正经历着一场政治上的大腐败,它对国家的法律、文化、经济,及人们心理造成的伤害是致命的。
解放全人类这句话,作为一个阶级的口号,有一定的价值,作为一个国家的口号,则有着明显的大国沙文主义倾向。与其去解放全人类,不如首先解放自己。
社会制度的优越性,不在于理论的阐述,而在于是否代表广大民众的利益,在于利益分配的合理性及权力相互的制约性。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不是一句空话,而是一场经济发展的实力较量,是制度完善科学的对比,是人民是否能享受到高度的民主自由,以及充裕的物质生活的具体体现。
矛盾的一分为二和合二为一,只不过是分析问题的角度不同,纯属学术之争。一是谈矛盾的分解,二是谈矛盾的聚合,殊途同归,无甚新意。大可不必上纲上线,斗得你死我活,反衬得权力无理性。
利益是永恒的主题,只有永恒的利益,没有永恒的朋友。利益分配的合理性,是社会稳定高速发展的前提。一大二公,谁都是利益的局外人,当然没有出路。利益的核心是成本,国家的管理成本,企业的经营成本,家庭的婚姻成本,不计成本的生活,永远没有好日子过。可发生在我们身边不计成本的事还少吗?像五八年大跃进大炼钢铁,家家砸锅卖铁,伐了那么多树,炼出了一个铁疙瘩,还到处吹嘘。“文革”中让生产停滞,去换取政治上的一点荣耀,还成绩最大最大,损失最小最小。就好比家里飞进了一只蚊子,你说怎么不是只苍蝇呢,我的苍蝇拍就在边上放着呢;你怎么不是只老鼠呢,我家里还准备好了老鼠笼子呢;你怎么不是只狼呢,我柜子里还放着猎枪呢。蚊子嗡嗡在耳边闹着,你一急一枪把蚊子打死了。结果还到处吹嘘你的赫赫战功,谁都会说你傻,把家里打得千疮百孔,用高射炮打蚊子,还吹呢。实际上,关注成本是社会良性有序发展的关键问题,历代任何一个官僚,出自本身的利益,都会将官僚机构无限地扩大化,不断加大国家的管理成本。因此,要想获得最大的国家利益,必须降低国家运行成本;要想降低成本,必须精简机构和提高效率;要想精简实效,必须以法治国;要想以法治国,杜绝腐败,就必须削减政府权力,建立权力制约机制和公正的司法体系,以及有效的民主监督。
鲁岩看到父亲写在废纸上的只言片语,有些一张纸片上只写了一半,估计是怕被人发现而藏匿的,这些支离破碎的语言生动活泼,言简意赅,通俗易懂,针砭时弊,无不闪烁着智慧的光芒。从现在看,许多言论是反动的,是对“文革”的一种反思,不排除矫枉过正的言论。但人之将亡,其言也善。父亲把自己的所思、所虑毫无顾忌地写了下来,供后人评判。他打心眼里佩服父亲的远见卓识和大胆的批判精神,以及面对强权的无畏。他临别时,父亲的身子更虚弱了,父亲躺在病床上,一直拉住他的手,用眼盯着他看,泪盈在眼眶里,没有说话,此处无声胜有声的嘱托,更让他感到自己的责任。父亲的手始终是凉凉的、无力的,却一直不愿松开,深深的父子之情在紧握的掌心中传递。他的泪无声地跌落在白色的床单上,父亲见他伤心的样子,强力地推开他的手,喃喃地说了句:“走吧,男子汉不需要眼泪。”
鲁岩擦干了自己的眼泪,踏上了回来的旅途。为了避免城里抄家的危险,鲁岩把父亲的文稿都带到了樱桃园,他决心完成父亲的心愿。
彩色电影的诱惑。
鲁岩回来的第二天,县里送电影样板戏下乡,在村子打谷场放彩色影片《沙家浜》,主要是慰问知青,要求全部知青到场观看。我中午在小卖铺遇上了鲁岩,告诉他此事,他满不在乎地说:“已接到通知了,样板戏广播里天天播,词都背熟了,不用看都知道。”我说:“这可是政治任务,要求都得参加。”鲁岩没说什么,买完东西就赶回樱桃园去了。
傍晚,打谷场上挤满了黑压压的人,小媳妇抱着个孩子,老大爷由老太太搀扶着,拄着拐杖也来瞧个新鲜,他们还没见过彩色电影是什么样呢。孩子们在银幕下追逐打闹,四周人山人海的。全村的人都来了,连银幕背面也满是人,有的人甚至爬到了树上。知青们每人带一个马扎,整齐地坐在银幕正当间,贵宾似的,我左顾右盼一直未见到鲁岩的身影。大喇叭高唱着革命歌曲,大海航行靠舵手,社员都是向阳花。天已擦黑了,银幕上用幻灯放出了毛主席语录,一位县干部在高音喇叭里激情洋溢地念着县革委会的一封慰问信,当念到“致以无产阶级的革命敬礼”时,我才见到鲁岩弯着个腰从银幕前溜过来,见我向他摆手,就挤在我身边坐下。这家伙总是稀稀拉拉的,集体活动从不准时。鲁岩一见我,盯着我看了半天,我说:“才几天没见,就不认识了。”他说:“怎么一堆乡里人,突然冒出个城里人来了?”我看看自己穿的还是老样子,一件旧军装,没什么变化,感到纳闷:“我又没啥变化呀。”他笑了笑说:“一堆黑炭里,就藏你一个白面儿人。”他一说就把我逗乐了。我轻轻打了他一拳说:“去你的,前几天感冒,在病房里捂的。”
“哦,对不起,咱俩是一根绳上拴的两只蚂蚱,都往病房里钻。”他从口袋里掏出几顆大白兔奶糖,悄悄放在我手心里,算是赔礼道歉。我也没客气,剥开就往嘴里放,又香又甜,好久没吃上奶糖了。记得小时候,我爸经常给我买糖吃,各色各样的,光糖纸我就攒了一大摞,几本书夹得满满的,全班的女生谁也比不过我,让我很得意。我边吃着糖边问他:“一来就没正经的,你爸病得怎么样?人家还为你担心呢。”
“够呛,癌症,难好。”他的话一字字地从嘴里蹦出来,透过放映机的光我看见他的神情很忧郁,刚才油嘴滑舌的劲一下子不见了,脸上挂着淡淡的忧伤。
“也许还会有希望的。”我小声地安慰他。
“难。”他嘴里只吐出了一个字,声音很沉重,接着又长长地叹出了一口气。我趴在他耳朵边,跟他说起队里虚报亩产量的事,他一副无所谓的样子说:“多管闲事多吃屁,少管闲事少拉稀,像这样的事多着呢,你吃饱撑的,管他干啥。”一句话把我噎得够呛,弄了个自讨没趣。我还想跟他说他父亲与爸爸之间的事,见他父亲病成这个样子,怕惹他伤心,也没敢提了。电影放映着,我的胳膊被旁边的女知青捅了一下,她告诫我们别说话。我抬头看起了电影,是智斗的那场戏,阿庆嫂左右逢源,遇事不慌,似乎这样的人物在任何时代都吃得开。如果阿庆嫂在场会怎么样,当个受气的店小二,见阿庆嫂陪胡司令打麻将,他不会吃阿庆嫂的醋呢?样板戏中的女人大都没有爱情,《龙江颂》中的江水英,《海港》中的方海珍,还有《杜鹃山》中的柯湘,女人在热火朝天的革命中得到快乐,在你死我活的斗争中寻找慰藉,个个比男人还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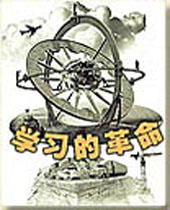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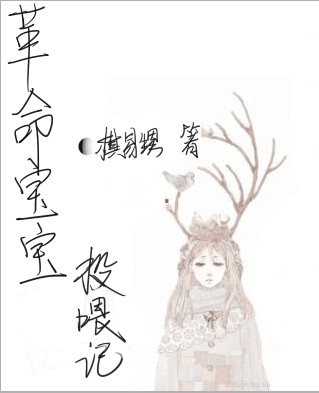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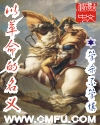
![(火影同人)治愈的樱花[火影]封面](http://www.baxi2.com/cover/18/18651.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