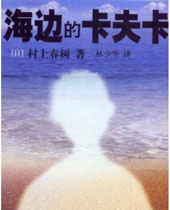卡夫卡集-第14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装帧得很漂亮,”我说,“确实是精致的印刷品。您可以感到满意,博士先生。”
“可我真的不满意,”弗兰茨。卡夫卡说,顺手把书放进抽屉锁上,“每次发表我的拙著都让我感到不安。”
“那您为什么让人发表?”
“事情就在这里!马克斯。勃罗德、费利克斯。韦尔奇,哲学家和政论家韦尔奇(1884…1964 ),是布拉格《复国主义周报》”自卫“的主编。我的这些朋友总能搞到我写的什么东西,然后就拿来谈妥的出版社合同对我突然袭击。我不愿给他们制造麻烦,所以这些完全是私人记录的东西,或者写着玩的东西最终都出版了。我的人生弱点的个人见证材料都印成书出售,因为我的朋友,以马克斯。
勃罗德为首,一定要把我的东西变成文字,而我又没有力量销毁这些孤独的见证材料。”
稍后,他改变语调说:“我刚才的话当然不免夸张,也是对我的朋友们的小小不敬。其实我自己也已经堕落,不知羞耻,亲自参与出版这些东西。为了原谅自己的软弱,我把周围世界写得比实际的强大。这当然是欺骗,我是法学家,因此,我不能摆脱恶。”
8。“那两个乔装的警察一把抓住我。我想喊叫。一只长满黑毛的大手堵住了我的嘴。我一口咬住散发出汗臭的拳头。这时我醒了。我血液上涌,满头大汗。
这是我做过的最大的恶梦。”
卡夫卡用右手背擦了擦下巴。“这我相信您,”他俯身到桌面上,慢慢地把手指交叉到一起,“普通人的世界是地狱,臭气熏天的粪坑,臭虫窝。”他呆呆地看了我几分钟。我急于知道他要对我说什么,可是他却用平谈的语调说:“您现在要去您父亲那里,是吧?可我还要工作。”——他微笑着和我握手告别。
“工作就是把渴望从梦中解脱出来,而梦常常使人眼花缭乱,它把人奉承得美不可言。”
9。弗兰茨。卡夫卡让青年人着迷。他的短篇小说《司炉》《司炉》为卡夫卡长篇小说《美国》的第一章。充满了温厚和感激之情。我们在谈论登载在文学刊物《骨干》上、由密伦娜。耶森斯卡译的捷克文译文密伦娜。耶森斯卡(1895…1944),是一个将卡夫卡小说译成捷克文的译者。关于她和卡夫卡的关系参见《弗兰茨。
卡夫卡致密伦娜书信集》,福兰克福费歇尔出版社,1952年。时,我对他说了上面这些话。
“这篇小说充满阳光,情调开朗,里面充满爱,虽然根本没有谈到爱。”
“爱不在小说里,而在途述的对象里,在青年身上,”卡夫卡严肃地说,“青年充满阳光和爱。青年是幸福的,因为他们能看到美。这种能力一旦失去,毫无慰藉的老年就开始了,衰落和不幸就开始了。”
“难道老年就有排除任何幸福的可能吗?”
“不,幸福排除老年,”他微笑着向前低下头,仿佛他要把头藏到高耸的肩膀之间似的,“谁保持发现美的能力,谁就不会变老。”
他的微笑、姿势和声音表明,他以前是个安静快乐的男孩子。
“那么,在《司炉》里您很年轻,很幸福。”我这句话还没有说完,他的脸就阴沉起来了。
“《司炉》很好,”我赶紧说。但是,弗兰茨。卡夫卡的深灰色大眼睛已经充满了哀伤。
“我们最好谈遥远的事情,遥远的事看得最清楚。《司炉》是梦呓,是对也许永远不会成为现实的什么东西的回忆。卡尔。罗斯曼卡尔。罗斯曼,《司炉》
中的人物。不是犹太人。我们犹太人生下来说是老人。”
10。 讨论他的书总是非常简短。
“我读了《判决》。”
“您喜欢这本书吗?”
“喜欢?这本书太可怕了。”
“您说得对。”
“我想知道,您怎么会写这样一本书。‘献给F。F。为菲莉斯。鲍威尔(1887…1960),弗兰茨。卡夫卡曾两次(1914和1917)与她订婚。题词背景参见《弗兰茨。卡夫卡致菲莉斯书信及订婚期的其他书信》,法兰克福费歇尔出版社,1967年。’的题词肯定不只是形式。您肯定想用这本书告诉某个人什么事。我很想了解这种关联。”
卡夫卡窘迫地笑了笑。
“对不起,我太唐突了。”
“您无须道歉。一个人读书就是为了提问。《判决》是夜晚的幽灵。”
“为什么?”
“它是个幽灵,”他又说了一遍,眼睛直视远方。
“可是您却写下来了。”
“我只是把它固定下来,因而完成了对幽灵的抵御。”
11。 “小说的主人公叫萨姆沙,”我说,“这听起来像隐喻卡夫卡。两个名字都是5 个字母。萨姆沙中S 的位置与卡夫卡中的K 相同。字母A 萨姆沙德文为Samsa ,卡夫卡德文为Kafka。……”
卡夫卡打断我的话:“这不是暗记。萨姆沙不完全是卡夫卡。《变形记》不是自白,虽然它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披露。”
“这我不明白。”
“难道谈论自己家里的臭虫是体面的,明智的?”
“这在体面人家当然不常见。”
“您看,我不体面到什么程度?”
卡夫卡笑了。他不想再谈这个题目了。我却还想谈下去。
“我以为,在这里评价‘体面’或‘不体面’不合适。《变形记》是一个可怕的梦,一种可怕的想象。”
卡夫卡停住了脚步:“梦揭开了现实。而想象隐蔽在现实后面。这是生活的可怕的东西——艺术的震撼人心的东西。现在我可要回家去了。”
他简短地向我告别。我把他赶走了?我感到惭愧。
12。 一次,我给卡夫卡讲了我不知在什么地方读到的中国小故事。“心脏是一座有两间卧室的房子。一间住着痛苦,另一间住着欢乐。人不能笑得太响,否则笑声会吵醒隔壁房间的痛苦。”
“那么欢乐呢?高声诉苦是否也会吵醒欢乐?”
“不会。欢乐耳朵不好。它听不见隔壁房间的痛苦。”
卡夫卡点点头:“这话得对,因此,人们常常做出高兴的样子。人们在耳朵里塞进欢乐的蜡球。比如我。我假装快乐,躲到欢乐的后面。我的笑是一堵水泥墙。”
“防御谁?”
“当然防御我自己。”
“可是墙是朝向外界的,”我说。
“它是朝外的抵御。”
但是卡夫卡立刻非常坚定地驳斥这种看法:“事情就是这样!每种抵御都是后退,都是躲藏,因此,把握世界总是意味着把握自己。每一堵水泥墙都只是一种假象,迟早要坍塌的。内与外属于一体。它们互相分开时是一个秘密的两个令人迷惘的外貌,这个秘密我们只能忍受,而无法解开。”
/* 34 */第四部分:谈话录不押韵的蹩脚货13。 “您在画画?”
卡夫卡歉意地微微一笑:“不,随便乱涂而已。”
“我可以看看吗?您知道,我对图画很感兴趣。”
“这可不是可以让人看的图画。这完全是个人的、别人无法辨认的象形文字。”
说着,他就拿起那张纸,用两只手把它揉成一团,扔到办公桌旁边的废纸篓里。
“我画的人空间比例不对。他们没有自己的视野。我试图画下这些人物的轮廓,但他们的透视是在纸的前面,在铅笔未削尖的那一头上——在我心里!”他伸手到废纸篓里拿出他刚扔进去的纸团,把它展开,撕成碎片,使劲扔进废纸篓。
“您过去学过画画?”
“不。我只是力图用某种非常特殊的方式把观察到的事物固定下来。我的画不是绘画,而只是一种个人的符号文字。”卡夫卡会心地一笑,“我还一直被囚在埃及。我还没有跨过红海《圣经》故事,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上帝选召摩西带领同胞逃离埃及,跨过红海,来到西奈,摆脱奴隶生活。见《圣经。旧约》”
出埃及记“……”
我笑了笑说:“过了红海,首先见到的是沙漠。”
卡夫卡点点头:“是的,《圣经》里是这么写的,而且生活里就是如此。”
他用手顶住桌子边缘,把身体靠回到椅子上,他这样舒展着身子,神情急切地看着天花板。
“虚假的、通过外部措施去争取的假自由是一个错误,是混乱,是除了害怕和绝望的苦草外什么都不长的荒漠。这是自然的事,因为凡是具有真正的、耐久的价值的东西,都是来自内心的礼物。人不是从下往上生长,而是从里向外生长。
这是一切生命自由的根本条件。这个条件不是人为地制造出来的社会气候,而是不断地通过斗争去争取的对自己和对世界的一种态度。有了这个条件,人就能自由。”
“一个条件?”我疑惑地问。
“是的,”卡夫卡点点头,又重复了一遍他的定义。
“这可真是个怪论!”我脱口喊道。
卡夫卡深深吸了一口气,接着他说道:“实际情况就是这样。构成我们有意识的生活的火花一定要跨越矛盾的鸿沟,从一极跳向另一极,以便我们在闪电的火光中看见世界片刻。”
我沉默了片刻,然后,我用手指了指画着画的纸,轻声问道:“那么这些小人,他们在哪里?”
“他们从黑暗中来,又在黑暗中消失,”卡夫卡说。他把画满图画的纸放进桌子抽屉,用听起来很随便的声调说道:“我的乱涂乱画是原始魔力的不断重复而不断失败的尝试。”我不知所云地看着他。当时,我肯定做了一个叫人好笑的怪脸,因为卡夫卡的嘴角抽搐了几下,显然他在克制自己,不让自己笑出来。他抬起手挡住嘴巴,轻轻咳了几声,说:“人类世界的一切东西都是被赋予生命的图画。爱斯基摩人在他们要烧掉的木头上画上几条表示水浪的线条。这是具有魔力的火之画,他们不断用火石摩擦,唤醒它的生命之火。我在做同样的事情。我要通过我的画了解我所看见的那些人物。不过我画的人物形象不会着火。也许是我用的材料不对,也许是我的铅笔性质不对头,也许是我自己不具备必要的性质,只是我一个人不具备必要的性质。”
“这是可能的,”我附和他的看法,力图做出嘲弄的微笑,“况且您到底不是爱斯基摩人,博士先生。”
“这自然不错,我不是爱斯基摩人,但我和大多数人一样,生活在一个奇冷无比的世界,而我们既没有爱斯基摩人的生活基础,也没有他们的裘皮大衣和其他为生存而必备的辅助手段。和他们相比,我们大家都是赤身裸体的。”他撮起嘴巴,“今天穿得最暖和的只有那些穿着羊皮的狼。他们日子很好过。他们穿的衣服正合适。您说呢?”
我说:“谢谢您这番话。我宁可挨冻。”
“我也是,”卡夫卡博士大声说,用手指了指暖气片,上面一只椭圆形铁碗里的水冒着蒸汽,“我们既不要自己的裘皮大衣,也不要借来的。我们宁可保留我们的舒适的冰雪荒漠。”我们两人都笑了:卡夫卡博士为掩盖我的不懂而笑;而我笑,则是为了接受他的不言而喻的好意。
14。 卡夫卡博士摇了摇头说道:“您别这样做!您不知道,沉默包含了多少力量。咄咄逼人的进攻只是一种假象,一种诡计,人们常常用它在自己和世界面前遮掩弱点。真正持久的力量存在于忍受中。只有软骨头才急躁粗暴。他通常因此而丧失了人的尊严。”
卡夫卡打开办公桌的一个抽屉,拿出一本杂志,放到我面前。那是文学刊物《树干》德文版第四年第21期。
“我醉心于书名,”卡夫卡说,“书籍是一种麻醉剂。”
我打开我的公文包,让他看里头装的东西:“那我是吃大麻的人,博士先生。”
卡夫卡很惊讶:“全都是些新书!”
我把书全倒到他的办公桌上,卡夫卡一本接一本地拿起翻看,不时地读一小段,然后把书递给我。
他把书全看了一遍后问我:“我些书你全都要读?”
我点点头。
卡夫卡抿了抿嘴唇:“您何苦读这种昙花一现的东西?大多数现代书籍只不过是对今天的闪烁耀眼的反映。这点光芒很快就熄灭。您应该多读古书。古典文学,如歌德的作品。古的东西把它最内在的价值表露到了外面——持久性。时新东西都是短暂的,今天是美好的,明天就显得可笑。这就是文学的道路。”
“那么创作呢?”
“创作改变生活,有时候比这更糟。”
15。 卡夫卡几次要求我,让他看几篇我的“不押韵的蹩脚货”——这是我对自己写的东西的称呼。于是,我在日记里找出合适的段落,凑成一本小小的散文集,取名为《深不可测的瞬间》,交给了卡夫卡。
几个月以后,当他准备去塔特兰斯克。玛特莱里疗养院疗养时,他才把手搞还给我。
他就此机会对我说:“您的作品非常清新。您谈得更多的是事情在您身上唤起的印象,而不是事件和事物本身。这是抒情诗。您在抚摸世界,而不是去把握世界。”
“那我写的东西没有一点价值?”
卡夫卡抓住我的手:“我没有这样说。这些小故事对您肯定具有某种价值。
写下的每一个字都是个人的文献材料。不过艺术……”
“不过这还不是艺术,”我苦涩地补充道。
“这还不是艺术,”卡夫卡肯定地说,“这种印象和感情的表达不过是对世界的小心翼翼的摸索,犹如还没有睡醒的眼睛。但是这很快就会过去,摸索地伸出去的手也许会缩回来,仿佛它触到了火。您也许会大喊起来,结结巴巴地乱说一通,或者咬紧牙关,睁大眼睛。不过,这一切都只是言论罢了。艺术向来都是要投入整个身心的事情,因此,艺术归根结底是悲剧性的。”
/* 35 */第四部分:谈话录弗朗西斯修道院16。 这是我有一次和卡夫卡博士一起从工伤保险公司去老城环形道的路上,在泰因霍夫斜对面的雅各布教堂停下谈话时得到的认识。
“您知道这个教堂吗?”卡夫卡问我。
“知道。不过很肤浅。我只知道这个教堂属于旁边的弗朗西斯修道院,就这么多。”
“教堂里有一条铁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