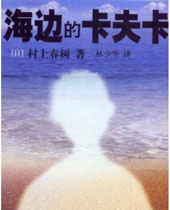卡夫卡集-第19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是这样,”我父亲叹了口气,“这一点在伤寒病隔离房看得非常清楚。谢天谢地,这种可怕的事已经过去了。”
“它还没有过去,”卡夫卡博士一边轻轻地说,一边走向办公桌,在那里站住,低下头,“恐怖在积聚力量,以便东山再起。”
“您估计还会有新的战争?”我父亲瞪大了眼睛问。
卡夫卡博士不语。
“这不可能!”我父亲激动地举起手,大声喊道,“不可能再发生世界大战。”
“为什么不可能?”卡夫卡博士轻声说道,两眼直视我父亲的眼睛,“您表达的只是一种愿望。难道您能坚定地说,这场战争是最后一场战争?”
我父亲不说话。我看见他的眼睑在颤动。
卡夫卡博士坐下,在桌面上交叉起瘦骨嶙峋的手指,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不,我不能这样说,”我父亲终于说,“您说得对,这只是愿望。”
“当人们陷在没到脖子的烂泥坑里时,有这种愿望是很清楚的事,”卡夫卡博士说,却并没有看着我的父亲,“我们生活在人口通货膨胀的时代。人们靠消灭比士兵和大炮便宜的平民百姓而赚钱。”
我父亲说:“尽管如此,我还是不相信会爆发一场新的战争。大多数人都反对。”
“这不起作用,”卡夫卡博士沮丧地说,“多数人不作决定。他们总是做人家命令他们做的事情。起决定作用的是逆流而上的某个个人。不过,现在这样的个人也没有了。他由于追求舒适而消灭了自己。衬衣比上衣离一个人更近。这样,我们将在自己的污垢中毁灭。如果我们不马上扔掉道德脏衣,我们每个人都将可怜地死去。”
“您把什么叫作罪孽?”
“逃避自己的使命是罪孽。误解、不耐烦、懒散是罪孽。作家的任务是把孤立的非永生的东西导入无限的生活,把偶然导入规律。他要完成的是预言性任务。”
/* 44 */第四部分:谈话录我内心的声音55。 我和女友海伦妮。斯拉维切克从赫鲁梅茨来到布拉格。我们去我父亲的办公室,向他报告我们已经到达。我们在楼梯上碰见弗兰茨。卡夫卡。我向他介绍海伦妮。
两天以后他对我说:“女人是陷阱,从各方面窥视着人,想拉他就范。如果人们自愿跳进陷阱,她们就失去任何危险。但是,如果人们慢慢习惯,因而制服了这个陷阱,那么,所有女性的捕兽铁爪又会重新张开。”
56。 “假如家里情况不是这样,我也许不会写作,”我说,“我想摆脱他们的吵闹,不想听见我周围和我内心的声音,于是我就写作。就像有人用钢丝锯做各种小玩意儿,以消磨晚上无聊的时光那样,我拼凑句子,拼凑文章,这样我就有理由一个人躲在一边,与困扰我的环境隔绝。”
“这很对,”卡夫卡说,“许多人都是这样做的。福楼拜在一封信里写道,他的小说是一块岩石,他紧紧抓住它,免得掉进周围世界的旋涡之中。”
“我虽然也叫古斯塔夫,但不是福楼拜福楼拜全名为古斯塔夫。福楼拜。,”
我笑着说。
“灵魂保健的技术不是某几个人的专利。倘若福楼拜的名字您听着不合适,我可以告诉您我自己的情况。我有一段时间也曾像您这样做过。只是我的情况还要复杂一些。我胡写乱涂,以此逃避我自己,而最后又抓住了我自己。我无法逃脱自己。”
57。 卡夫卡博士给我买了查理斯。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保尔。高更高更(1848—1903),法国著名画家。代表作为《雅各及天使》、《塔希堤妇女》等。的《从前和后来》和阿图尔。兰坡兰坡(1854—1891),法国诗人,著有《巴黎战歌》、《醉舟》和《灵光篇》等。的《生活与诗》。
狄更斯的书是我自己选的,这本书是我藏书中缺少的这位作家的少数几本书之一。卡夫卡博士同意我的选择。
他说:“狄更斯是我最喜欢的作家之一。可以说,有一段时间他甚至是我企图效法的榜样。您喜爱的卡尔。罗斯曼是大卫。科波菲尔和奥列佛。特维斯特大卫。科波菲尔和奥列佛。特维斯特是狄更斯同名小说《小卫。科波菲尔》和《奥列佛。特维斯特》中的人物。的远房亲戚。”
“博士先生,狄更斯让您入迷的是什么东西?”
卡夫卡不假思索地回答:“他对事物的掌握,他在外界和内心之间保持的平衡,他对世界和自我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出色而又简单的描写,他的非常自然的匀称。当今大部分画家和作家缺少这些东西。比如说,您在这两位法国人身上就已经可以看到这一点。”
路上,卡夫卡博士谈了他对给我买的那几本书(除了《大卫。科波菲尔》)的作者的看法。他说:“主观的自我世界和客观的外部世界之间的紧张关系,人和时代之间的紧张关系是一切艺术的首要问题。每一个画家、作家、剧作家和诗人都必定要探讨这个问题。其结果自然是现存各因素的不同混合。对于画家保尔。
高更来说,现实只是运用形式与颜色创作独特艺术品的马戏团高架。而兰坡则用语言做同样的事,而且超出了言词本身。”
/* 45 */第五部分:书信甜美的滋味赵登荣译致密伦娜卡夫卡与密伦娜的相爱发生于1920年,当时,一个已是37岁的单身汉,一个还是25岁的少妇,双方都不是初恋,却比初恋更热烈。对于已进入生命晚年的卡夫卡,这是他多年为婚姻所作的努力失败后爱情的最后绝唱。但是好景不长,命运还是不能宽待这位命中注定的单身汉。半年多以后,他俩的关系就开始谈化了,不久就告吹。究竟为什么,读者从这少量的信件中,也许能看出一二。
亲爱的密伦娜夫人:卡夫卡在写给密伦娜的信中说写台头是一种“累赘”,所以在他以后的信里很少有台头。
今天我本想写点别的,可是做不到。这并不是说我真的那么想写别的事;假如我真这么想,我就会写别的了,但是园子里总该有个躺椅放在荫凉处为您准备着,在您的手够得着的地方应该放着十来杯牛奶。在维也纳也可以,尤其是这样的夏日,不过这地方必须是个安静的去处,且饮食不悉。这不能办到吗?难道就没人为您张罗这些事吗?医生是怎么说的呢?
当我从大信封中抽出这个本子时,我几乎失望了。我想听您说话,而不是想听那种从旧沟壑中冒出的我已经熟悉了的声音。这声音为什么要插入我们中间呢?
直到后来我突然想起,这声音曾在我们之间起过媒介作用。此外,您对自己下了那么大的功夫,这使我感到难以理解;而您怀着如此真诚的感情做了这件事,这又使我非常感动。您来回调整句子的顺序,您这真诚的感情显示出的可能性和美妙的、天然的合理性,使我在捷克语中发现了一个新的天地。德语和捷克语竟是如此相近吗?不管怎么说,这总是个坏得不能再坏的故事。亲爱的密伦娜夫人,我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几乎整句整行地给您指出来,只是如果这样做,那就太使我反感了,您喜欢这个故事,这自然赋予它以价值,但却使我眼前的世界稍稍黯淡了一些。不说这些了。《乡村医生》卡夫卡于1919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其中包括《乡村医生》等14篇短篇小说。将由沃尔夫系出版卡夫卡作品的出版商,全名为库尔特。沃尔夫。寄给您,我已写信跟他说了。捷克语我确实懂得。有好几次我曾想问您,您为何不试试用捷克语给我写封信来。我并不是说您的德语不熟练。
在大多数情况下您的德语熟练得令人吃惊,偶尔发生错误的时候,德语会自觉地向您鞠躬赔礼,而后它就显得特别美;就是一个德国人也不敢奢望他的母语会给他这样的待遇,他们不敢无所顾忌地写自己的感受。我想读您用捷克语写的东西,是因为它是您的母语,在那里密伦娜才是完美无缺的(您的翻译已经证实了这点);而在这里,即在您写的德语里,则只有来自维也纳、或者为维也纳准备的那一部分密伦娜。因此用捷克语写吧,我请求您。还有您信中得到的那些小品文,就算它们是些鄙陋的东西吧,您不也通读了这鄙陋的故事了吗?读到哪里为止?我不知道。也许我会这么做的;但如果我不能这么做,我就会抱住我那最好的成见不放。
您问我订婚的事。我曾两次(说具体点是三次,因为两次与同一姑娘卡夫卡曾先后于1914与1917年与菲莉斯。鲍威尔订婚。1919年又与第二位姑娘尤利叶。
沃津切克订婚,后因父亲反对而告吹。)订婚,三次解约时都离婚礼只有几天。
第一门亲事已经完全过去(我听说她现在已结婚,并有个男孩),第二门婚事还存在着,但没有任何成婚的希望,因此实际上并不存在,或者说,它独立存在着,但却要人来为它付出代价。总之,我从这里和别的地方都发现,男人在这种情况下遭罪更多,或者说(如果要这么看的话)比女人更缺乏抗拒的能力;女人都总是无辜地受罪,诚然,不是说她们对此“无能为力”,而是说,从最本质的意义上讲,这显然最终仍要汇入到“无能为力”之中去的。再说,反复思索这些事是没用的。就好比您费尽力气要打烂地狱里的锅炉一样。首先,这是办不到的;其次,即使办到了,砸锅炉者虽然在飞流而出的热气体中焚为灰烬,地狱却仍丝毫不为所动,堂而皇之地照样存在。此事必须另寻途径。
不管怎么说,首先应该在一个花园里躺下,尽可能地享受这疾病(特别是假如这不是真病的话)的甜美。这里面有许多甜美的滋味呢。
您的弗兰茨。K。
/* 46 */第五部分:书信与我的愿望相违亲爱的密伦娜夫人:
首先,我坦白地告诉您,免得您与我的愿望相违,直接从我的信中察觉出来:约两周来,我在日甚一日的失眠之中忍受着折磨。我并不把它看成是完完全全的坏事;这样的日子反反复复,还总有一些原因(可笑的是,照贝德克的说法,连美兰的空气都可能是起因);即使有时那些起因几乎看不见,摸不着,但它们总要叫人目瞪口呆,使你像林中兽一般烦燥不安。
有一点却是很大的安慰:您睡得很好,尽管是“奇怪地”,尽管昨天还有些“失常”,但毕竟是睡了好觉。当夜间睡意从我身边擦过时,我知道它此行何去,也给予默认。对此进行反抗是愚蠢的,睡眠是最无辜的事情,而失眠者则是罪孽深重的。
而您在上封信中恰恰对这么一个失眠者表示感谢。假如一个不知底细的陌生人读到这儿,他一定会想:“这是个什么样的人啊!在这种情况下他竟然像完成了一件移山填海的伟业似的。”其实他在这期间什么也没干,连手指头都没能动一动(握笔的指头除外),靠牛奶和好些吃的东西度日:眼前并不总是放着“茶和苹果”(尽管经常如此)!此外,一任事物自由发展,一任山和海躺在它们的老地方。您知道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一篇成功的短篇小说吗?这是个归纳了很多道理的故事,我在此引用,仅仅因为引用一个伟大人物的故事能使人快乐,而一个发生在周围的,甚至更近处的故事往往可以具有同样的意义。而且这故事我已经记不太清楚了,更别提人物姓名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穷人》时,同一个文人朋友格利戈罗维奇住在一起。这位朋友尽管数月之久一直看到桌上摊着写过的纸,却直到小说写完才得以一读。他读着小说,深深地被感动了,未经陀思妥耶夫斯基同意,他就带着文稿去找当时著名的评论家涅克拉索夫。
夜间3 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门铃响了。那是格利戈罗维奇和涅克拉索夫。他们闯进房间,热烈地拥抱着、吻着陀思妥耶夫斯基。当时还不认识他的涅克拉索夫称他为俄国的希望,他们谈论着,主要谈这部小说,谈了一两个小时,早晨他们才告辞。陀思妥耶夫斯基(他后来总把这一夜称为他一生中最幸福的夜晚)靠在窗旁,看着他们的背影,抑制不住自己,哭了起来。他的基本感觉(我已经想不起来他在什么作品中写到过)大体上是:“多好的人啊!他们是多么善良而高尚!
而我是多么卑贼。假如他们能看透我的内心,他们会怎么想啊!假如我实话告诉他们,他们是不会相信的。”我的故事到此就结束了。至于以后陀思妥耶夫斯基怎么下决心向他们看齐,则是无须赘言的,这只是不可战胜的青年时代必不可少的结束语,而不属于我所想引用的故事。亲爱的密伦娜夫人,您觉察到了这个故事的匪夷所思的神秘之处吗?我想大概是:格利戈罗维奇和涅克拉索夫肯定不比陀思妥耶夫斯基高尚,这是就总的方面而言。现在您不去看总的方面(陀氏在那个夜晚也并没有要求这一点,而且这在具体情况下也没有任何用处),而只听陀思妥耶夫斯基说的话,您就会相信格利戈罗维奇和涅克拉索夫确实了不起,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则不纯洁,卑贼得不得了,这当然使得他即使从远处看格利戈罗维奇和涅克拉索夫也不可企及,永远谈不上报答他们那宏伟的、受之有愧的壮举。
他只能从窗台上看着他们远去,以此喻示他们是不可接近的。——可惜这个故事的含义被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一伟大的名字抹去了。我的失眠将把我引向何处呢?
肯定引向子虚乌有,假如这“子虚乌有”含意不怎么好的话。
您的弗兰茨。K。
亲爱的密伦娜夫人:
只写几句话。明天我一定再写信给您,今天仅仅是为我自己的缘故而写,仅仅为了我为自己所做的某件事情,仅仅是想将您的信造成的日夜压迫着我的印象稍稍减轻一些。您很特别,密伦娜夫人,您住在维也纳那边,要忍受种种痛苦,却有时间对别人(譬如我)这一夜比上一夜睡得差一点表示惊奇。我这儿三位女友(三位妹妹,最大的5 岁)的看法比您理智,只要一有机会,不管我们是否在河边见面,他们就要把我扔到水里去,而这不是因为我干了什么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