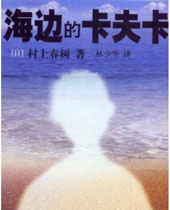卡夫卡集-第6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仅仅由于他的目光。当人们进入他的办公室时(一个世纪前这是我们这儿的长老们的议事厅),他一身戎装坐在写字台后面,手里握着笔。他不喜欢虚文甚或喜剧表演,他不会继续写下去,让来访者干等着,而总是立即中断工作,身子靠回到椅背上去,当然笔仍然攥在手里。于是,他便以这斜倚着的姿势,左手插在口袋里,看着来访者。来访的请求者的印象是,上校看着的不仅仅是他这个短暂地从人群中冒出来的陌生人,否则上校为什么要这样仔细地、长时间地、一声不吭地看着他呢?再说,这也不是一种尖锐的、有穿透力的审视目光,即人们看着某一个人的时候可能会发出的那种目光,而是一种漫不经心的、浮动的、然而却又绝不移开的目光,是人们观察远处一群人移动时的那种目光。不间断地伴随着这种长时间的目光的是一种难以捉摸的微笑,一会儿像是嘲讽,一会儿又像是恍恍惚惚地沉浸在回忆之中。
30。 一个秋日夜晚,天气清朗而微凉。有个人从房子里走了出来,他的动作、服饰和轮廓全都模糊不清,一出来就想向右拐去。女房东穿着一件宽敞的女式旧大衣,倚在一根门柱上,对他悄悄地说了些什么。他考虑了一会儿,然后却摇了摇头,继续向前走去。穿过电车轨道时,他由于没注意而挡住了电车的路,于是电车从他身上压了过去。疼痛使他的脸和浑身的肌肉都抽紧了,以致电车过去后,几乎无法使缩小了的脸和抽紧了肌肉再松开来。他默默地站了一会儿,看见在下一站有个姑娘下了车,转过身来招手,往回跑了几步,又停下了脚步,重新钻入了电车。当他经过一个教堂时,台阶上站着一个牧师,向他伸出手来,身子弯得那么靠前,几乎有一个跟头栽下来的危险。但他没有去握那只手,他对传教士历来反感。那些孩子也使他恼火,他们在台阶上就像在一个游戏场上那样窜来窜去,互相喊着粗话,这些话的意思他们当然并不懂,他们只是吮吸这些粗话,因为没什么更好的东西——他把他上衣的扣子扣得严严实实的,继续走他的路。
31。 这是个平常的日子,它向我露出了牙齿,我也被牙齿给缠住了,无法脱身。我不知道它们是靠什么缠住我的,因为它们并没有咬合;我看到的也不是整齐的两排牙齿,而只是这儿几个,那儿几个。我想要抓住它们,从它们上面翻越出去,可就是办不到。
32。 你说我应该继续往下走,可我已经在很深的深处了,如果非要那样不可,那我宁可留在这儿。这是什么样的空间啊!也许已经是最深的地方。但我愿意待在这里,只求别强迫我继续往下降。
33。 在这个形象面前我一筹莫展:她坐在桌边,看着桌面。我围绕着她转圈,感到被她扼住了脖子。第三个人在围着我转圈,感到被我扼住了脖子。第四个人在围绕着第三个人转圈,感到被他扼住了脖子。就这样一直延伸开去,直到星星的运动,以至更远。一切都感觉到颈部被扼。
34。 那是一个小池塘,我们在那儿饮水,肚子和胸部贴着地,由于狂饮的疲惫,前肢无力地浸泡在水中。可我们必须马上回去,考虑问题最多的那位忽然振作起来,叫道:“回去啦,弟兄们!”于是我们便往回跑。“你们上哪儿去啦?”
他们问我们。“在小树林里。”“不对,你们在小池塘那儿。”“不,我们没在那儿。”“你们身上还滴着水哪,骗子!”
鞭子挥舞起来了。我们在充满月光的长长的走廊里猛跑,不时有一个挨上鞭子,疼得一蹦好高。到了先祖廊那儿,追逐结束了,人们带上了门,把我们单独关在这儿。我们大家依然十分口渴,便互相舔着毛皮上和脸上的水,有时沾上舌尖的不是水,而是血,那是来自鞭挞的伤口。
35。 这抱怨是毫无意义的(他对谁抱怨?),这欢呼是可笑的(窗上的五彩缤纷而已)。显然他只不过想成为第一个祈祷者。但接下来这犹太属性就显得不正派了,接下来他在诉苦时只须终其一生地反复说:“我—狗,我—狗……”便足够了,我们大家都能够理解他。然而沉默足以导致幸福,而且是唯有沉默可能导致幸福。
36。 “这不是光秃秃的墙,而是压成墙状的最甜美的生活,一串又一串紧挨着的葡萄。”“我不信。”“尝尝看。”“由于不相信,我的手无法抬起来。”
“我把葡萄递到你嘴里。”“由于不相信,我不会去尝的。”“那就沉沦吧!”
“我不是说过,面对这堵墙的光秃秃,人们必将沉沦吗?”
37。 我像其他人一样会游泳,只是我的记性比别人好,就是忘不了以前的不会游泳。由于我不能忘记,会游泳对于我来说无济于事,到头来我还是不会游泳。
38。 这就是那个拖着长尾巴的动物,一条长达好几米的尾巴,像狐狸那样的尾巴。我很想把这尾巴抓到手里,可是办不到,这动物老是动个不停,尾巴老是甩来甩去。这动物像一只袋鼠,但它那几乎像人那样扁平的、椭圆形的小脸上无特点可言,只有它的牙齿颇有表达力,无论是遮掩着还是龇咧着。有时我有一种感觉:这个动物想要训练我,不然它为什么总是在我下手去抓的时候把尾巴抽开,然后又静静地等着,直到我再度受到诱惑,然后它又一次跳走呢?
/* 16 */第三部分:杂感迷失方向39。 预感到有人要来,我便瑟缩在一个屋角,把长沙发横在我的前面。现在如果有人进来,一定会认为我神经不正常,可是真的走进来的这个人却没有这样认为。他从他的长统靴中抽出他的驯狗鞭子,在他周身一个劲儿地挥舞。接着,他跳起来,又岔开两腿落在地上,喊着:“从角落里出来!还想躲多久?”
40。 我不断地迷失方向。这是一条林中小路,可是十分容易辨认,只有在它的上空看得见一线天空,其他地方全都是林木茂密,一片昏黑。尽管如此,我仍然不断地、绝望地迷失着方向,而且:一旦我离开这条路一步,便意味着深入林中一千步,并会绝对地感到孤独。于是我真恨不得倒下去,永远不再爬起来。
41。 当野外工人晚上收工回家时,他们在路面斜坡上看到一个缩成一团的老人。他半睁着眼睛在打瞌睡。给人的第一个印象是他喝醉了,可他并没有喝醉,看上去也不像生病了,也不是受着饥饿的折磨,也不是受了伤而精疲力尽,至少他对所有这些问题一概报以摇头。“那么你到底是什么人呢?”人们终于问道。
“我是一个大将军,”他头也不抬地说道。“原来如此,”人们说,“原来这就是你的痛苦。”“不,”他说,“我真的是将军。”“没错,”人们说,“要不然你又能是谁呢?”“你们爱怎么笑就怎么笑吧,”他说,“我不会惩罚你们的。”
“可我们根本就没有笑啊,”人们说,“你想是什么就是什么吧,如果你愿意,你也可以是上将。”“我确实是的,”他说,“我是上将。”“你瞧,我们已经看出来了。但这不关我们的事,我们只是想提醒你,在这儿过夜会冻坏的,所以你应该离开这儿。”“我走不了,再说我也不知道该到哪儿去。”“你为什么走不了?”“我走不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是我能走,我在那一瞬间又将成为我军队中的将军了。”“他们把你扔了出来?”“扔一个将军?不,我是掉了下来。”“从哪儿掉下来?”“从天上。”“从那上面?”“对。”“你的军队在那上面?”“不。可是你们问得太多了。走你们的吧,让我一个人待着。”
42。 他把脑袋转到了一边去,在这样露出的脖子上有个伤口,在火热的血和肉中沸腾着,这是一个闪电击出来的,这个闪电现在仍然持续着。
43。 这不是牢房,因为第四面的墙完全不存在。当然,如果设想一下,这一面的墙也是砌好了的,或者将可能砌好,那将令人毛骨悚然,因为我所处的空间仅一米深,只比我高一点,简直就是个货真价实的石头棺材。只不过它暂时没有被砌死,我可以自由地把双手伸出去。如果我抓住顶上的一个铁钩子,我还能小心地探出头去,当然只能是小心翼翼的,因为我不知道我的小间离地面有多高。
它好像很高很高,至少我目所能及的下方只是灰蒙蒙的雾气,向左,向右,向远方望去,都是这种情景,只有上空雾气似乎不那么浓。这种景观就像在一个阴沉沉的日子里从一个塔上望出去那样。
我感到疲倦,便在边上坐了下来,让双脚自由地下垂。讨厌的是,我偏偏赤裸着身子,要不然我就把内外衣物一件一件地打上结连接起来,一头固定在上面那钩子上,缘着另一头就能在小间外面往下坠落一大段距离,或许能探出点什么名堂来。话又说回来了,幸亏我没有这么干,因为我必然会怀着不安的心情去着手,那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最好还是什么也没有,什么也不干。这个小间空空荡荡,由光秃秃的墙壁围绕着,偏偏后面地上有两个洞。位于一个角上的洞是用于解手的,而在另一个角上的洞前放着一块面包,一个拧上了盖子的盛着水的木桶,我的食物就是从那儿塞进来的。
44。 情况并非是:你被埋在了矿井里,大量的岩石块把你与世界及其光线隔离了开来;而是:你在外面,想要突破到被埋在里面的人那儿去,面对着岩石块你感到晕乎,世界及其光线使你更加晕眩。而你想要救的那个人随时都可能窒息,所以你不得不发疯一样地干,而他实际上永远不会窒息,所以你永远也不能停止工作。
45。 我有一把强有力的锤子,但我没法使用它,因为它的把被烧得火红。
46。 难道他斗争得不够吗?在他工作的时候,他便已经成为了失败者。这点他是知道的,他坦率地说:只要我停止工作,我就完了。那么他开始工作是个错误?几乎谈不上。
47。 鞭挞先生们聚在一起,这是些强壮而不流于肥胖的先生,他们时刻准备着。他们被称为鞭挞先生,他们手中攥着鞭子,站在豪华大厅后壁的许多镜子前面和中间。我携着未婚妻步入大厅,这是婚礼的时辰。亲戚们从我们对面的一扇窄门中走了出来,旋转着走上前来,里边有许多女人,她们的左边走着矮小的男人们,一色身着礼服,扣子扣得高高的,迈着碎步。有些亲戚出于对我的未婚妻的惊讶抬起手来,但大厅里仍然是一片寂静。
48。 他用上牙紧紧地咬住下唇,注视着前方,一动不动。“你这样是毫无意义的。到底出了什么事?你的生意不算太好,可也并不糟糕;再说,即使破了产——这当然是无稽之谈,你也很容易找到新的出路。你又年轻又健康,学过经济学,人很能干,需要你照顾的只有你自己和你的母亲,算我求你了好吗,振作起来,告诉我,你为什么大白天把我叫来,又为什么这个样子坐着?”接着出现了小小的间歇,这时我坐在窗台上,他坐在屋子中央一把椅子上。他终于开口了:
“好吧,我这就都告诉你。你所说的全都没错,可是你想想,从昨天开始雨一直下个不停,大概是从下午5 点开始的吧,”他看了看表,“昨天开始下雨,而今天都4 点了,还一直在下。这本来不是什么值得深思的事。但是平时街上下雨,屋子里不下,这回好像全颠倒了。你看看窗外,看看,下面是干的,对不对?好吧。可这里的水位不断地上涨着。它爱涨就涨吧。这很糟糕,但我能够忍受。只要想开一点,这事还是可以忍受的,我只不过连同我的椅子漂得高一点,整个状况并没有多大改变,所有东西都在漂,只不过我漂得更高一点。可是雨点在我头上的敲打使我无法忍受。这看上去是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但偏偏这件小事是我无法忍受的,或者不如说,这我也许甚至也能够忍受,我所不能忍受的仅仅是我的束手无策。我实在是无计可施了,我戴上一顶帽子,撑开一把雨伞,把一块木板顶在头上,可全都是白费力气,不是这场雨穿透一切,就是在帽子下、雨伞下、木板下又下起了一场新的雨,雨点的敲击力丝毫不减。”
/* 17 */第三部分:杂感生活在暮蔼之中一位骑手驰聘在林中小道上,他的前面跑着一条狗,后面跟着几只鹅,由一个小姑娘用枝条驱赶着。尽管从前面的狗到后面的小姑娘,大家都在尽快地向前赶路,但速度并不是很快,每一位都能轻而易举地跟上。此外,两边的树也在跟着跑,好像总有点不太情愿,疲惫不堪的样子,这些老掉牙的树。一个年轻的运动员撵上了小姑娘,这是个游泳运动员,他以强有力的动作游着,脑袋深深地埋在水里,因为水在他的四周波涛起伏,而且无论他怎么游,水总是跟着他流动。
接着是一个木匠,他得送一张桌子上门,他把桌子扛在背上,前面那两条桌腿牢牢地攥在手中。跟在他后面的是沙皇的信使,他由于在林中碰到这么多人而十分不高兴,不时伸长脖子向前张望,看看前面何处是尽头,为什么大家都行进得这么慢,慢得令人讨厌;可他不得不忍气吞声,他可以超过前面的木匠,可又怎么通过围绕着游泳运动员的那一片水呢。奇怪的是,跟上信使的是沙皇本人,这是个还算年轻的人,蓄着黄色的山羊胡子,长着线条柔和的圆圆的脸,表露出对生活的愉快心情。这种泱泱大国的缺点在此暴露了出来,沙皇认得他的信使,可信使不认得他的沙皇,沙皇正在借此短距离的散步散散心,可向前走的速度并不比他的信使慢,他其实完全可以自己把邮件送去的。
49。 这实在的,我对这整个事情并不在意。我躺在角落里,看着,就像人们躺着能看的那样;听着,能听懂多少就听多少。此外,几个月来我就一直生活在暮蔼之中,等待着夜色降临。而我的狱友就不同了,这是个不屈不挠的人,曾经是个上尉。我能体会到他的思想观念。他认为,他的处境就像一个北极探险家,被冰雪封在了某个地方,可是一定会得救的,其实应该说,已经得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