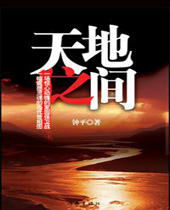在性与爱之间挣扎 作者:[俄]莎乐美-第1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身边,我当即决定替她去卖花。男爵夫人索菲正好跟我在一起,她也同意我的计划——我们穿上那老妇的衣裳。到次日凌晨2点半,我们卖掉了最后一枝花,利润还挺可观的。这些花都卖给了拉丁区里坐咖啡馆的男人们,现在他们都跟我挺熟的。经过这件事,我发现:当那些男人面对两个幽灵一样的新的卖花女郎时,表现出了完美的绅士风度。我跟索菲的个子都很高(她甚至比我还高些),与那些小巧玲珑的法国女人形成鲜明的对照。他们问了我们许多友好的问题。直到第二天,我们才从新闻界的朋友那儿得知,我们没有任何执照而公然卖花,居然没有被当场抓进监狱,是极为幸运的。
在巴黎的俄罗斯人聚居区,我结交了一个朋友,他是个年轻的外科医生。他曾被指控参与谋杀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行动,从而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经过四年的强制劳动,他最终来到了巴黎。他的名字叫萨威利,他强壮得像一棵大树,能用他那闪闪发光的牙齿从墙上把钉子拔出来。他介绍我认识了在巴黎的所有俄罗斯移民。六个月之后,夏天炎热的太阳开始照耀得我们无法忍受,我和萨威利一起匆忙逃到了瑞士,因为在那儿度假比较便宜。我们爬上了苏黎士附近的一座小山,在一间小屋里住了下来。我们在那儿以奶油、奶酪、面包和草莓为生。只有寥寥几次,我们返回到苏黎士,在某家宾馆的饭店里大吃一顿。在那些田园诗般的日子里,发生过一段小小的插曲,我至今记忆犹新:有一天,我们赤足而行——像往常一样走在阿尔卑斯山软绵绵的苔藓上——我们漫步走过一段山坡,进入了一片四处蔓延的黑莓地,一开始我们并没有注意到黑莓。此时天色已暗,我们却再也弄不准回家的路途。我们每走一步、每停一步,都要发出痛苦的呼号。最后,当我们回到那个柔软的草坪上的乐园时,不禁泪流如注。
在那块小小的黑莓地里逗留期间,我心里升起了某个像憧憬又像回忆的东西——就好像我体验到了一个人由洞天福地陷入悲惨世界的过程,体验到了那种被抛弃、被剥夺的感觉。当我们擦着脸上的汗水、脚上的血水时,萨威利高兴地说:“我们应该请求黑莓原谅我们——因为我们没有绕道而行,而是践踏了它们;我们本应该用嘴唇亲吻它们的。”这话使我们忘掉了烦恼。我安慰他说:“是的,难道误解不是整个世界上最糟糕的事吗?”因此,我们一会儿发笑,一会儿发怒,在人生的草莓丛中自由自在地踏上新的大胆的征程。
几个星期之后,我们回到了这个古老而美丽的城市,到处周旋,人们都为我们的晒黑而感到惊讶,那时晒黑还不像现在一样是一种时尚。从那以后,直到晚秋,我又认识了许多新朋友,许多事情都使我感触颇深,我似乎生来必须要遭受这些事情。不过,那时,在夜深时,有个人似乎在呼唤我——我得走了。我从来没有从理性上去弄清这事情每次是为何发生的以及何时发生的——不管我多么喜欢周围的人和事,喜欢到向他们敞开自己的整个身心。他们中总有一些不速之客,到来后却又不耐烦地要提前离开。如果不是一个女作家朋友保留着我当时写给她的一封信,如果这封信不是在不久前又回到我手上,我是不会回忆起我回到德国的那个夜晚的,也不会清楚地描写当时的情景。那封信写于1894年10月22日,地点是施马根多夫。
“自从我由巴黎来到施马根多夫,已经三个多星期了——我是悄悄离开的,没有向任何人告别,为此连我自己都感到惊讶。我是在午夜时分到达的,没有跟任何人打招呼。我把行李箱留在车站,一个人跑了出来,沿着寂静的道路穿过黑暗的田野,到达了这个村庄。这次步行离奇而美妙。尽管由于天黑我什么也看不到,但我在落叶和暴风中感到了秋天的存在,我的心情是愉快的;在巴黎,现在还是“夏天”呢。村子里所有的人都睡了,只有我丈夫用来照亮高高书架的明亮灯盏依然燃烧着。我在街上能清楚地看见他的脑袋。门像往常一样虚掩着,我悄悄进了门。我们的小狗罗德大声吠叫着冲出起居室——它听出是我的脚步。它已经变成了一头高大魁梧的真正的怪物,除了我和我丈夫可能不会再有人认为它是可爱的了。那天晚上,我们彻夜未眠。外面天光渐亮时,我在厨房里生了火,擦亮那盏被煤烟熏黑了的灯,随后出门走进了小树林。早晨的浓雾依然张挂在树林里,一头长满斑点的母鹿静静地穿过松树林。我脱掉了鞋子和袜子(在巴黎,你不可能那么做),感到非常高兴。”
在那些年头里,跟我真正亲近的女性朋友是男爵夫人芙丽达。⑦1908年,她刚刚进入50岁,就过早地离开了人世。在我逗留巴黎期间,她刚刚从德属东非逗留回来,跟我一起呆了一段时间,她妹妹就是跟我一起卖花的索菲。次年,她来俄罗斯看望我、我母亲以及我的兄弟们。后来她跟我哥哥尤金成了关系不一般的亲密朋友。她自己的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都是非正常死亡的。她妹妹叫玛格丽特,死时已经是一位知名作家;⑧她想去抢救一个落水男孩,自己却掉进冰窟窿里淹死了。尽管芙丽达具有男子汉似的坚强意志,尽管生命的冲动使她在年轻时甚至去了东非,但她性情忧郁。她有时显得精力充沛,有时又显得精疲力尽。她喜欢用这样一个事实来解释她的这种精神状态:她是一个老朽家族的一员,由于整个家族崇尚服从和自我牺牲,它终将完蛋。
1895年,我和芙丽达还一起在维也纳呆了几个月——当时我刚刚从彼得堡回到那儿。由于长期混迹于柏林的文学圈,我们跟维也纳的作家席尼茨勒也早已熟识。我在巴黎期间,曾跟他通过几次信。他带着我转了一些地方。除了个人之间的拜访,我们几乎每个晚上都一起呆在咖啡馆里,去了解维也纳文化生活中最具有特征的方面。我住在圣·斯特凡大教堂附近的一家非常高级的宾馆里,用了顶楼的两间装修精美的小房间。在彼得·阿尔腾伯格写的第一本书《如是我见》中,那两个房间的情形以及我和朋友们在里面长达数小时谈话的情形都写到了。如果我不得不把维也纳的气氛跟其他大城市做比较的话,我会说,我觉得它的明显标志是理智和色情的汇流。在其他地方,普通人和专业人士或学术人员是有区别的;而在维也纳,普通人也明显具有吸引人的魅力和优雅的风度。这样的魅力和风度造就了可爱的年轻人,把他们提升到了色情主义的氛围之中;一方面他们以最严肃的态度把自己奉献给了他们的职业,另一方面又呼唤某种情感的冲动,这样的情感和行为往往会磨钝目标远大的雄心的锋芒。不过,这会给男人们留下发展彼此友谊的空间——尽管男人们会为爱情和荣誉竞争,但友谊似乎是非同普遍的。席尼滋勒很适合于这样的环境:也许友谊是我们生活中最明亮的方面,但对于他来说,连友谊也带着忧郁。尽管如此,如果他的内心不那么分散,如果他在知识上的魅力和优雅的风度能更加持续地引导他在一条道上往下走——不管是走向爱情还是走向雄心,他都可能在精神上使自己得到全面的发展。
阿尔腾伯格站在我边上——虽然这并不表示友谊。人们跟他在一起时,既不会想到男人也不会想到女人,只会把他看成另外一种存在。关于他的一个众所周知的说法是:“我的杯子很小,但我得用它喝水(Mon verre est petit,mais je bois dans mon verre)。”⑨只要我们强调的是“小(petit)”,而不是“我的(mon)”,那么这就是一个准确的判断;因为阿尔腾伯格作品中那使人激动的新东西取决于某种神秘的方式,他用那种方式阻碍了两性关系的内在发展,把他们的幼稚病变成了他自己的诗歌特性,他在自己的人格特性中充分表达了这种诗歌特性。
第6章 另外一种存在和其他人在一起(3)
后来,无论我何时来到维也纳,我总是跟玛丽·冯·艾伯内在一起。⑩最后一次是在1913年。几年之后她就去世了。我是从她的侄女金斯姬侯爵夫人那儿得知她去世的消息的。我将永远不会忘记我跟她在一起度过的平和时光——我怎么来表达那种平和呢?它是从她那儿散发出来的。当你看着她的时候,就好像她在故意地把自己尽可能地变小,就好像她抬起了花白的头颅仰望着什么,那双无限智慧的眼睛尽可能流露出谦逊的目光;所以,没有人会意识到那坐在他们前面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就好像保守秘密才是最好的选择。我们从她那儿得到的不仅是一种神秘意识,而且是一种发现意识——这两种意识都保存在她温暖的内心世界,而在她的语调、语言、目光以及手势中,都有不断的、隐秘的表现。维也纳的环境美不胜收,几乎给人以身在乡村之感。在那儿朋友们也可以频繁地见面。我一直希望周围有森林、宽阔的田野以及阳光,让它们把我体验的杯子盛得满满的——甚至还有高山,我很少在山里呆,只有小时候跟父母一起路经瑞士时有过几次短暂的逗留。在1895年的冬天,我再度来到维也纳,而在次年夏天,我第一次来到奥地利的山林里。我曾经跟一个朋友一起,进行过一次步行长途旅行,那是从维也纳出发前往威尼斯,至今想起来还是记忆犹新。那次旅程很缓慢也很悠闲,一路上的印象短暂而强烈,深深地植入了我的记忆之中。我们得在天黑前到达罗特加尔登冰河,但我们耽搁了,因为我们在草地上警觉地发现了野牛的足迹。我们叫来了所有被野牛的消息激动起来的当地居民,大家拿着各式各样、奇形怪状的武器,共同来对付那头野牛。几分钟之后,野牛进入了我们的视野——它就在山的对面,跟我们隔着一道深深的峡谷,它侧着身子警觉地站着——看上去强壮而令人着迷。用以前的话来说,它“像神一样”。尽管它跟我们隔着安全的距离,但我们能观察到它,它给我们留下了深刻而持久的印象。当我们在罗特加尔登冰河上的巨石之间跋涉时,尤其是当我一个人在黑暗中的时候,我一直想着那头野牛。我们俩相互询问,在那些巨石之间,是否隐藏着可以歇息的传说中的小屋。
我对乡村印象最深的记忆是三个转瞬即逝的春天,那是我从意大利往北经过德国旅行时得来的。欧洲南方从来没有像那次那样成功地穿过我的意识。尽管南方的冬天都像北方的五月似的,但我们仍然会感觉到冬天到春天之间的季节交替,其间根本就没有夏天的位置。在所有可见的事物后面,有一种不可穷尽的东西,每一个季节都会招来这种东西。它使我感到:如果人具有更加深刻的接受机制,如果人对细微的差别更加敏感,无穷无尽的世上万物就会有待于我们去发掘。因此,我更喜欢的还是中欧的气候。冷静的天气容易使你变得烦躁不安。你得不断地重新开始,擦去雨水的痕迹,敦促正在发芽的柔荑花迅速开放。我高兴地问候紫罗兰以及其他所有感伤的事物:我的心很安宁,充满了忍耐,甚至有更深的快乐。
我至少可以说说我那时所体验的第三个春夏之交的情形。我从小就喜欢北方的夏天。它既可以说是漫长,又可以说是短暂;它展现得明亮、持久而完美,不容我们忽视它。当我们听见深夜里布谷鸟的叫唤时,听见庄稼汉收工回家的路上所唱的小曲时,我们所想的不是“快点,趁着那太短暂的夏天还没过去,做点事吧”,而是感到自己超越了时间和季节的转换,超越了昼夜之间、早晚之间的争吵。在家里,不管在哪个季节,我都想一个人呆着,我每天得写一篇散文,早先时候我要写的是剧评。有时候,我得漫步穿过要么白雪皑皑、要么绿意稀疏的田野,因为芙丽达住在她的亲戚安娜男爵夫人的房子里。属于她的那两间房子里放满了最漂亮、最与众不同的什物,有的是她的家族留传下来的,更多的是她刚刚从东非带回来的。早在1896年,我们就决定一起在慕尼黑呆一段时间。正是在慕尼黑,我遇到了第二个真正关系亲密的同性朋友。从那一年开始,我们一直保持着亲密的友谊(我们几乎是同龄);我们的友谊还将保持下去,直到离开人世的日子。
海伦来自拉托维亚共和国首都里加,暂时跟她母亲和姐姐一起住在慕尼黑。读了托尔斯泰的《克劳采奏鸣曲》(Kreutzer Sonata)之后,她写了《一个女人》(Eine Frau)。她认识许多德国人。一年后,她跟一个建筑师订了婚。很久以后,海伦离开哥廷根,在柏林呆了几个月,她的家变成了我的家。海伦与芙丽达之间的差别就像是一个金发少女跟一个黑发少年之间的差异。芙丽达渴望冒险,所以她到了遥远的国度,而海伦的座右铭是:“上帝已经帮我安排好了一切”——就好像她的内心已经被爱情的力量决定了:做个贤妻良母。我跟芙丽达也很不一样,所以我们俩常常争论,当然争论之后总是有收获,对于争论我比她感到更加舒服些,因为她本以为我们在所有的事情上都很相像。某种深刻的、隐秘的亲和因素把我跟海伦连在了一起,但这并没有阻止我选择了一条跟她完全不同的道路,也没有在我们之间制造真正的分歧,因为她那富于爱的本性深深吸引着我,她对我毫无保留,甚至在我表现得像个魔鬼的时候,她都能容忍我。
在慕尼黑,人们的公共生活没有像在巴黎或维也纳那样广泛;宽阔而美丽的街道显得更加空旷,就好像它们在召唤人们走出家门,在它们身上聚集。在慕尼黑,人们发现自己不属于土生土长的“慕尼黑人”,而属于所有的德意志民族。社交生活往往在一些文人的家里举行。我成了奥格斯特·恩德尔的一个关系特殊的朋友,此人是一个艺术商人也是一个建筑师,后来当上了布雷斯罗艺术学院的院长,他一直跟我有联系,直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