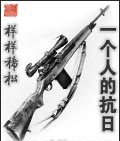中国人的素质-第18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同样的原则,经过明显的变通之后,也适用于小规模地赈济那些随处可见的川流不息的难民。我们从所有这些事例中发现,赈济的目的不是让受惠人获益,而是使行善之人获取回报。中国人行善的目的,好比在掷双骰的赌博中掷出四点一样,凡与行善者有关的人,都要有理由肯定自己会“往前走”。
至于中国慈善事业的缺陷,一定要加上这样一条:任何事情,无论好到哪儿急到哪儿,几乎都不可能逃避中国的压榨系统,它与中国政府的其他部分一样有着良好的组织。要把常备的救济钱粮全部占为己有,那是不容易的。但是,人们完全可以看到,每逢大饥荒的紧要关头,人民的水深火热并不足以阻止各级官员最无耻地侵吞原本应该由他们发放下去的救济款。此时,公众的注意力集中在灾情和重建家园之上,外界又对救济款项的筹措和使用一无所知,在这样的情况下,那些贪官会做出些什么丑行便不难想象了。
当中国人终于开始了解西方文明时,他们时常被迫接受最坏的方面,在他们看来,基督教世界里到处都是慈善机构,基督教世界以外的地方根本无法与之相比。然后,他们或许会想到去探究这个颇有意义的事实的原理。他们或许会注意这样一个引人联想的情况:中文的“仁”字,不像其他与情感有关的字那样有“竖心旁”,它也根本没有“心字底”。中国的善,也是行之而无诚心可言,其普遍后果我们已经注意到了。本能地从事实际的慈善活动,不管何时何地,都自觉地要求有机会展示这个本能——这种心理状态中国人完全没有。这的确不是人类的进步。如果它是中国人的创造,就必须经历曾经出现在西方的过程,使这种本能成为人生的必要成分。
中国人的素质
第二十一章 缺乏同情
我们已经注意到居于“五常”之首的“仁”,它代表着中国人生活的一个侧面。仁是祝福,而同情则是人们互相之间的伙伴之情。我们现在的目的,是在论述中国人行一定的善的前提之下,来表明中国人明显缺乏同情心这个命题。
我们必须时刻记住。中国的人口是密集的。这个帝国几乎所有地区都会周期性地发洪水,闹饥荒。中国人传宗接代的愿望是这么无法遏制,因此能控制人口增长的环境在许多其他国家里都起作用,但在中国效果相对差一些。最穷的人也要继续让孩子们早早地结婚,而这些孩子又要生出许多孩子,似乎他们有糊口的粮食。由于这些或其他原因,结果使得大部分人只能现挣现吃,名副其实的“双手刚挣来的东西,马上就得送进嘴里”。这可以解释为何到处都有按日计酬的务工者,而这种状况也是不可避免的。无论与什么地方的中国人打交道,外国人马上就会觉察到,几乎没有一个中国人有现钱。叫他们做事情,第一个要求就是给现钱,干活就是为了吃饭,前提是他们一无所有。甚至富有的人在碰到急用时,也常常筹不齐最起码的数目。有一句最为意味深长的话,说一个人被迫筹钱去应付官司、安排葬礼等诸如此类的事情,称作“度饥荒”,也就是像一个饥饿的人急迫地寻求帮助。除卞有钱有势的人,谁都无法应付这类事情而不需要帮助。贫困而又役有希望,这是中华帝国最为突出的事实,而这个事实对人际关系所造成的影响,在最粗心的观察者看来也是十分明显的。生计之忧,以及随之而来的各种习惯,即使在生计之忧不那么急切的时候,人们也习惯过最艰苦的生活。在这个层次上只有钱与粮这两个突出的事实。钱与粮是一对焦点,构成中国的椭圆,中国人的全部社会生活都围着它们转。。
中华帝国的芸芸众生陷于深深的贫困之中,他们经常为最基本的生存条件而艰难求生。对于他人所遭受的各种可以想见而又令人同情的苦难,他们都已经司空见惯了。一个中国人,无论怎么具备仁慈之心,实质上都无能为力,哪怕是减轻时时见到的苦难千分之一,他都做不到——而荒年的苦难又要成倍地加重。一个善于思考的中国人肯定会意识到,减轻苦难是绝不可能的,不管是靠个人的善心,还是靠政府的干预。所有这些办法,即使勉力为之,也只是治标而不治本。他们的治理方法,好比治伤寒病人分发一些小冰块——每个病人都分到好几个盎司,但没有医院,没有食品,没有药物,没有护理。因此。毫不奇怪,中国人没有更加仁慈的有效办法。完全缺乏体制、预测和管理,而慈举善行却还能进行下去,则更是令人奇怪了。如果人们一直碰到无法防止也无力救助的苦难,这种现象对哪怕是最有教养的人所产生的结果,我们是并不陌生的。每一场现代战争都足以说明这种现象。第一次看到流血,腹部上的神经会发生痉挛,因而留下了不灭的印象;但这很快就会过去,接着就会对此相对麻木不仁了,但看见一次,就会永生难忘。在中国,总是有一场社会战争,大家对其后果都已见怪不怪、熟视无睹了。
对身体上有任何残疾的人的态度最能说明中国人缺乏同情心。人们普遍认为,破子、盲人(尤其是瞎了一只眼的人)、聋子、秃子、斜眼,都是要避而远之的。似乎身体有缺陷,品质也肯定有缺陷。据我们观察、那样的人在西方非但不会受到残忍的对待,而且还会让人们油然而生一些同情。而他们在中国却被视为因为犯有隐秘的罪恶才受到这样的惩罚的,这种看法与古代犹太人不谋而合。
那些不幸先天残疾或者后天致残的人,不被人提及痛处就没法活下去。最温和的方式是描绘其缺陷,以吸引公众注意。药铺抓药的对一个病人这样说;“麻大哥、你是哪个村的?”一个眼斜的人经常会听见别人说“眼睛斜,心地歪”;头发一根不剩的人则经常受到这样的提醒:“十个秃子九个诈,剩下一个是哑巴。”类似白化病这样的缺陷也会变成无聊的玩笑、似乎永远都不会有停的时候。像这样不幸与众不同的人,必须一辈子逆来顺受,要想有好心情,就得对此毫无脾气,充耳不闻。
对精神上有所缺陷的人,中国人也过分坦率。“这个孩子,”一位旁观者说,“是个傻子。”这个孩子兴许根本就不“傻”,但这样不断当面说他没心眼儿,他那尚未发展起来的心智会很容易就此枯萎。这样对待一切精神病人或者完全是别的病症的病人是很普遍的。,他们的与众不同之处,行为举止上的细节。发病的原因、病情加剧的症状,都是公有财产,都当着病人的面一一抖搂出来,而病人必须完全习惯于别人称他为“疯子”、“呆子”、“笨蛋”等等,等等。
一个民族把生男孩视为头等大事,无怪乎家里没孩子会不断遭人嘲骂,就像传说在古代,先知撒母耳的母亲的“对头,大大激动她,要使她生气”。'注'如果为了什么原因。或者根本不为什么,一个母亲悄悄地闷死了自己的孩子,这样的事情让人知道之后,大家也不会感到奇怪。
中国人缺乏同情心,在对待迎亲那天新嫁娘时也是如此,其方式很有特点。新娘子总是很年轻,很胆怯,突然置身于陌生人群之中,自然不胜恐惧。尽管各地风俗有很大差别,但这个可怜的孩于突然暴露在众人注视之下,却没人在乎她的感受。有些地方还允许掀起轿帘瞪大眼睛看新娘。另外一些地方,不少尚未出嫁的姑娘在新娘子必经之路旁占好一个有利地形,满手捧着草屑或者米糠,撒在新娘子费时费力地油过的头发上。当新娘子到达公婆家起身出轿之时,她得像一匹刚买来的马一样,接受评头品足,不难想象她会是什么感觉。
中国人十分看重繁文缛节,但他们显然看不到会让人不快的事情,因而也就想不到去避免。笔者有一个中国朋友,他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在讲失礼的话,说他第一次看到外国人,最感惊奇的是外国人脸上长满了胡子,像猴子一样,他接着保证说:“现在我已经很习惯了!”有人当着学生的面,要一位老师评论一下这些学生的能力,老师回答说,在他们面前离门最近的学生最聪明,二十岁就会学业有成,但旁边那张桌子的两个孩子是他见过最笨的。人们从没有想过,这样的评论会给学生带来什么。
中国人缺乏同情,也体现在他们的全部家庭生活之中。不同家庭虽有很大不同,但究其本质都关系不好,很容易看到大多数中国家庭根本就不幸福。之所以不幸福,是因为缺乏感情上的联合,而这在我们看来是现实的家庭生活中最基本的。中国家庭通常是个人的联合,永远不变地联系在一起,有着相同利益,也有不少不同之处。最终结果,中国家庭不是我们所想象的家庭,中国家庭里不存在同情。
中国的女孩,一生下来就多多少少不受欢迎。这一现实对她们之后的全部经历,都有很重要的影响,并且为缺乏同情这一点提供不少发人深省的事例。
母亲与女儿在狭窄的院落这种中国生活条件下过日子,不免会发生口角,随口乱骂是日常生活中随心所欲养成的自由。有一句特别的俗话,了解中国家庭的人会觉得意味深长;妈妈骂女儿,仍是亲闺女。女儿一旦出嫁,除了无法脱离的血缘关系,就不再与娘家有什么关系了。所有家谱都略去女儿的名字,其理由根深蒂固:她已经不再是我们的女儿,而是人家的儿媳妇了。人的本性会使她有回娘家的要求,各地风俗不同,有的走得勤,有的走得懒。有的地方回娘家走得勤住得久,还有的地方则回得越少越好,如果婆家有丧事在身,则倾向于完全中止回娘家。但是,不管是哪种具体做法,儿媳妇属于婆家的一份子,这个原则都是正确的。想要回娘家,就得带上不少活儿去干,可能是大量的针线活,娘家人还得帮着干。每次都尽可能多地带上孩子一起去,这样做既是为了管教孩子,以免他们变坏,最主要是让这些孩子尽可能在姥姥家多吃、住些日子。在女儿经常这样回娘家的地方,在女儿多的家庭,这种不断的侵扰是让娘家全家都感到害怕,也加重日常生活资源的开销。因此,这类访问经常会受父亲和兄弟的阻止,母亲则暗暗高兴。不过,由于各地风俗定下了某些回娘家的时节,比如在新年之后的特定日子以及特殊的节日等等,这类访问不受限制。
妇女回到婆家,用句俗话来说就是“贼不空跑”。她必须带点礼物什么的给婆婆,一般总是吃的东西。如果忽略这一老法,或者没有能力带回礼物,不久就会招来一些戏剧性的场面。如果女儿是下嫁到穷人家,或者嫁去之后变穷了,如果她又有几位已经成家的兄弟,她就会发现自己回娘家,用医生的话来说,就是“禁忌”。娘家的几个儿媳与已经出嫁的几个女儿,她们之间准会有一场打斗,比如腓力斯人与以色列人的子孙,各自把某个地方当做自己的特殊领地,而把对方当做侵略者。如果几个儿媳占据了领地,他们会像腓力斯人那样,对无法彻底消灭和驱逐的敌人征税。一个儿媳妇,被视为婆家全家的仆人,这是她恰如其分的地位。而要找仆人,显然要找健壮和成年的,而且已经学会烧饭缝补这类家政技术,以及该地区可以勤劳谋生的一切手段,而不愿要力气与能力都很小的孩子。我们知道有一个二十岁的姑娘,丰满而年轻,却嫁给了一个年龄只有她一半的瘦弱男孩,他们成亲之后的头几年,她得乐于照顾这个男孩出天花,而天花是一种幼儿疾病。
中国儿媳妇的苦难,可以写成一章,而不是简单地写一段。所有的中国女子都要出嫁,通常在很年轻的时候出嫁,她们一生中很长一段时间完全受婆婆控制,而当我们想到这一点,我们只是隐约地知道她们生活在受虐待的家庭中会遭受许许多多难以忍受的苦难。自家父母对已经出嫁的女儿鞭长莫及,除非对婆家进行一些劝解,或者女儿真的被迫自杀之后索要一大笔丧葬费。如果丈夫把妻子打成重伤甚至杀了她,只要能举证她对公婆“不孝”,便可以逍遥法外。我们需要重复一下,年轻妻子的自杀十分常见,有的地区几乎就找不到几个最近没有发生这种事情的村庄。一个母亲斥责已经出嫁的女儿自杀未遂:“你有机会,为啥没死成?”没有什么话比这句话更让人同情了。
《京报》几年前发表了河南巡抚的一份奏折,偶然披露说,父母杀死孩子,按法律观点来看有罪,但有一条规定却使法律成为一纸空文:一个婆婆恶意谋杀了她年轻的儿媳,凶手付一笔钱就能赎罪。他上报的案例中,一个妇女先用点着的香烫她的童养媳,再用烧红的铁钳烙她的脸颊,最后用沸腾的热水把她煮死。这份奏折里还提到几个相似的案例,由于写进奏折,肯定确实无疑。这种极端野蛮的事或许罕见,但虐待严重到导致自杀或企图自杀,这样的事情却经常发生,以至于人们当时都懒得去议论一番。与笔者熟识的不少家庭,都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给人作妾的中国妇女,其命运也十分辛酸。她们所在的家庭——幸福实在屈指可数——情形总是不断争吵与公开打斗。“我住的城市的长官”,一位久住中国的外国居民写道,“他十分富有,并且学识渊博,擅长舞文弄墨,为官干练,能引经据典。但他经常欺骗、咒骂、抢掠,甚至折磨他人,以满足他的兽欲。他的一个妾逃跑抓回来,被剥光衣服,两脚倒吊在屋梁上,往死里打。”
在中国这样的国家,穷人没时间生病。男人们根本不把妇女、儿童的病痛当回事儿,时常任其发展到无法治疗的地步,这或是因为没时间去管,或是因为男人“看不起病”。
在谈及孝心的时候,我们已经注意到,孝心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就是年幼的人无足轻重。年幼的人,其价值主要取决于他们可能成为什么,而不是他们现在是什么。大多数西方国家的做法,中国正与之相反。三个出门人中最年轻的人,总是首当其冲地去承受劳苦。最年轻的仆人,总是干最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