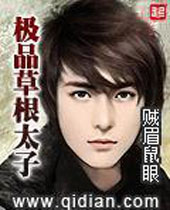野草根-第9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她简直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八、
无论到什么时候,于小庄都能清楚记得,她跟解放军排长高积云的见面,是在一个冬天的午后。
那是她回城后的一个特别无聊的冬天。过完大年不久,初中老同学谢卫东张罗聚一聚。谢卫东自从在新宾打架被开
瓢后,就一直借口回城看病修养,赖在城里不走。等他伤好应该归队时,于小庄他们那帮人已经忽啦啦张罗着回城,四
处走散得差不多,新宾青年点里没剩下什么人了。谢卫东也立即紧随形势,张罗着从乡下往回调,他想拿着队里给他定
的“公伤”诊断,以病退为理由,一步到位回到沈阳。事情的结果毫无疑问,当然要被搁浅在半路。当初队上为了不扩
大打架斗殴的影响,给他争取了“公伤”这个名目掩盖知青们的罪行。但是日后谢卫东这小子竞拿这个假招子来争取真
待遇,却是让诚实的广大贫下中农万万没有想到。他们想这城里人可真是翻手为云覆手雨,没个信义。当初感激得痛哭
流涕,哪承想翻脸不认人。
这套病退手续闹得够呛,最后也没折腾成。谢卫东一气之下,也不办了,索性留在城里当啷着,在他爹的厂子里打
打临时工。新宾那边也没人来问没人管,他也乐得在家里头逍遥自在。这回听说有好几个一起下乡的同学都回沈阳过年,
谢卫东又拿出了学生干部爱张罗的劲儿,把几个人都请到家里来玩。
那天下午来的有于小庄、郭子辑、金玉姬、朴长顺等几个人。谢卫东爹娘全到别处走亲戚,家里就成了他们一帮年
轻人的天下:大家就着炸花生米小咸菜,嚼着一点猪头肉和明太鱼,喝着酒,叙着旧,渐渐就高涨了情绪,说起话来没
边没沿的。谢卫东那个家伙竟然还有点伤感,说没想到一起从学校门出去的,如今却都变得各不一样。于小庄已经正式
回城,成了国营工人,郭子辑绕道抽调回抚顺煤矿,当了矿上一所学校教师。另外几个同学也全逃出了新宾,就近在阜
新、鞍钢等地方落脚。就他谢卫东一个人混得惨,当年的学生主席,现在落得个什么也不是,整天像个盲流一样。大家
忙就拿话安慰他,说你小子够不错的了,老爹是厂长,有户口没户口一样在厂里上班拿工资,这样的美事,咱们平民老
百姓,谁敢想?
谢卫东抹擦一把脸说,行了行了,咱们不说了,来,喝酒喝酒。又转头对于小庄道:哎,听说你朝鲜舞跳得炉火纯
青啊,还是盘锦地区毛泽东文艺思想宣传队骨干,方圆几百里地都有名?
于小庄拿手遮着喝得红扑扑的小脸,忙说:谁说的谁说的?哪有的事儿!
谢卫东说,这还谦虚啥!还不乘着酒兴,给咱来一段?
郭子辑、金玉姬、朴长顺他们几个人一听,也跟着起哄说:行啊于小庄!干得这么冲,怎么都没让咱们知道?白跟
你是一个战壕的战友了!不够意思,不够意思!
于小庄还扭扭捏捏:啥呀啥呀!你们别听谢卫东他瞎说。
谢卫东红头涨脸说:都到这份儿了,你还揣着兜着的干哈!
说着,起身,从隔壁屋里拿出他那架破旧的手风琴。他把琴抱在身上,按响了一个长音,屋里的人全都激动起来了!
这架琴,他们全都熟识、认得啊!那是后来谢卫东回城探亲时带回新宾去的,它曾陪伴过他们那个青年点的同学度过多
少乡村欢乐的日日夜夜!
于小庄矜持不住了。她是那种节奏感乐感特好、一听见乐音就禁不住要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的人。外加喝了点酒,
酒劲一上来,就有点把握不住,没了矜持。她也不再推让,站起身来,红着小脸脱掉外套小棉袄,露出里面一件粉红色
的薄薄的高领套头衫,还有精细的一把小腰。几个人一看她拉了架势,赶紧七手八脚把碍事儿的桌子板凳推到一边。于
小庄窈窕地站在地当央,一只柔软的手臂弯过头顶,一只手背到身后,足跟站稳,做了一个预备起舞的姿势。等到谢卫
东的过门一拉响,她就小腰一扭,开始翩翩起舞了!
金达莱,金达莱,金达莱哟,漫山遍野把花儿开遍……
在座的初中同学都好几年没见过于小庄唱歌跳舞了,在乡下见时,还完全是初学,有点生涩,没想到她现在竟然跳
得这么熟练,专业,这么出神入化,有声有色!尤其是跳舞时她脸上带的那种表情,完全是沉醉的,神圣的,天地洪荒,
物我两忘!他们都情不自禁,被她感染,被她带到舞蹈的情境里去,最后竞不自觉地一起拍手,一起唱将起来。歌声在
这个冬天的午后沉郁悠扬地传到窗外,直到最后一个乐音终止,于小庄连着做了几个旋之后猛地站定,一手在前,一手
在后,优雅地伸开,做出深情谢幕姿势。
就听一个声音在众人背后响起:好!接着是“啪啪”几声响亮的击掌声。
众人寻声望去,于小庄也寻声望去。他们的记忆,她的记忆,都在那一瞬间定格!
只见一个鲜红领章、红帽徽、穿着四个兜草绿军装的年轻解放军战士,正带着微笑迎面站着,从窗口射进来的午后
阳光正打在他的脸上、身上、领章上、帽徽上,红的越发鲜红,绿的越发嫩绿!那真叫一个威武英俊,高大威猛,唇红
齿白!
于小庄像被电打了一下,当时就傻眼了!她还站着丁字步,手臂还在半空扬着,半天没有放下来。解放军排长同志
十分促狭而又顽皮地近前几步,转回身面对几个同学,双脚后跟儿一磕,立定,“啪——”地来了个标准军礼:报告同
学们,初三二班高积云前来报道!
等他的手一放下,谢卫东第一个反应过来,手风琴都没来得及放下,上去“当啷”就给他一拳:高积云!你这个家
伙!说好一起过来吃饭,怎么才来?
高积云笑眯眯地说:家里有点事,临时耽搁了。等我走到这里,就听见你们家传出来的琴声和歌声。好家伙!我一
看,连门都没关,我就寻声推门进来。同志们,对敌斗争警惕性要加强啊!
这下大家叽叽喳喳重新活跃起来。想起来了,高积云,不是那个初三还没念完就被他爹整去当后门兵的那个吗?那
时他的个头也就不到一米七,怎么看都不起眼儿,怎么突然间在部队出息了,不光已经混出四个兜,还蹿成了一米八的
大个子?听说他们家老爷子颇有点本事,是一个解放战争扛过枪、抗美援朝打过江的老干部,一听说城里知青要下乡,
二话没说,先下手为强,一股脑把三个儿子全送部队当兵去了。高积云好像走的时候比较匆忙,也没跟学校打招呼,连
毕业证书都没有拿,还惹得老师背后没少说他们家长的坏话。
毕业几年过去,当年不起眼的淘气小子,转眼就变成了解放军英俊排长。于小庄的心呐,止不住咚咚狂跳!那一刻
她只能是假装谢幕还没谢完似的,手抽回来,捂在胸口,将激动的心情使劲按捺了一下。高积云接受完同学们的欢呼雀
跃、肩打背捶之后,又径直走到于小庄面前,伸出手来,欲跟她握,同时目光含笑,定定瞅着她说:于小庄,你跳得真
好!
攥住她的手之后,又悄悄说了句:你真美!
他用的是喉头发出的、经由鼻腔、颅腔共鸣过后产生的嗡嗡嗡的发音,陌生的略带天津味的北京普通话,那声音的
音量,控制在只有于小庄和他自己才能听得见的范围内。
于小庄又呆呆地傻掉了,一双小手,无辜无奈地任人握着,暗暗希望永远都不要松开。
九、
大桥上,小河旁,是他们约会的好地方。
沈阳城从来没像现在这样神秘层出不穷,这样七彩灿烂,漠然滞重的生活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新鲜轻盈。于小庄的
眼睛像是猛地被人撕开一层翳子,突然之间,眼前金光闪亮起来,所有的景物都在闪闪发光,带着明媚动人的色彩。结
满晶莹雪挂的冬天的树似乎已经春芽绽出。北陵湖水冬季的冰面似乎也荡漾出春天的涟漪。
他们先是以暧昧的老同学身份,相邀一起出行,一块儿走遍沈阳大街小巷。她陪他一起回到中学读书的地方,去找
曾经念过书的教室,还央求学校看大门的老头打开当年初三二班的教室门,让他们进去找找当年自己的座位。高积云指
着后边那扇窗户说,你记得不,我那时候经常把书包挂脑门上,不爱走正门,总是喜欢从窗户里进进出出?于小庄就低
头含羞,扑哧扑哧咬着嘴唇笑。来到黑板前边,于小庄指着墙角里的一块地儿说:你记得不?当年我曾撺腾学习委员郭
子辑,把咱班考试卷子埋到这儿的地底下,说是将来可以永垂不朽,留给后人看。要不,咱们挖一挖看看还有没有?高
积云就哈哈大笑,说你真傻,卷子那东西没几天就烂掉了,哪还能留下来!
于小庄像忽然想起来似的,问高积云:后来你的毕业证书拿了没有?
高积云鼻子一哼,满不在乎地说:拿什么拿!后来等到我爹坐着吉普车来学校替我取毕业证时,校长还很有骨气,
想拿一把,说必须让我回来参加完学校的毕业考试、履行完正常手续才能给。我家老头子一听,二话没说,扭头就走,
扬长而去。他们真是给脸不要脸,回来管他们要毕业证,是瞧得起他们,把他们当回事。谁想到他们还想拿一把,搞搞
牛逼。我爹一听,得,去他娘的,谁要那个破毕业证书。
不知为什么,听到这里,于小庄却不由得心里一慌。他这故意粗俗、粗鄙的语气里,带着多少特权阶级的自傲、得
意和霸气!那是跟她这种底气不足的平民阶级格格不入的一套话语。
慌归慌,却仍然管不住自己的脚,整天跟在高积云的身后跑。
等到把共同熟悉的地方转得差不多了,高积云邀于小庄到他家里去玩。其实他是留着心眼,把小庄领给他爹妈看看。
于小庄第一次走进沈空大院,走进那个干休所的二层小楼。天!她简直惊呆了!这里简直如同天堂,是她毕生都难以达
到的地方。她战战兢兢,又羞羞答答,接受了高积云全家人的检阅和考察。高积云的爸爸是个和蔼的小老头,个儿不高,
说话慢声慢气的,跟电影里演的我军高级将领咄咄逼人、身板挺直、硬骨铮铮的形象完全不一样。他妈妈是个慈祥的胖
老太太,脸圆乎乎长得像个弥勒佛。他们家还有一个女儿留在父母身边,长得四方大脸,比高积云小好几岁,也在军区
后勤当兵。对于于小庄的到来,他们家人表示出了友好而礼貌的欢迎。于小庄这样一个含情脉脉、亭亭玉立、颔首羞涩
的姑娘,初一见面,的确是很打动人,容易给人留下好印象。
从高积云家出来,于小庄还是莫名紧张,像等着一场审判,一晚上都没睡好。她不记得头一次去大下巴家时是否有
过这种情绪。躺在家里那个热腾腾的火炕上,翻来覆去烙饼子。老娘那空洞的打呼噜声,两个弟妹睡着放屁的臭气也充
耳不闻,充鼻不闻。
好不容易熬到第二天天亮。下午,约好时间他们到小河沿湖边树林再见面时,于小庄一句话都不敢说,紧张地盯着
高积云。高积云开口只说了句:我爹我妈……我们全家人都挺喜欢你……
于小庄的心呐,一下子就“忽悠”飞走了!幸福、喜悦夹杂着莫名紧张后的松弛,让她的脚后跟猛地发软、发飘,
身体摇摇欲坠地向下、向地面的方向倒下去。高积云趋前一把抱住她。
这一抱,就是山呼海啸!
久旱的禾苗逢雨露。没几天的时间里,他们就已经是如胶似漆,难舍难分了。
没等他们遍尝恋爱的甜蜜,高积云归队的时间却已经到了,两人不得不忍受痛苦的分离。一直无知无畏、没心没肺
的于小庄,从来没有感受到相思是这般苦,相恋是这般煎熬人。高积云离家走后,她整天茶饭不思,魂不守舍,把全部
工夫,都用到想他念他、不断给他写信上头去。等到攒到第六十一封信的时候,深秋已经来临,该说的情话已经说够,
再在纸上写下去,只有初中文化的他们两人都已经笔墨用尽、言空词穷。接下来必须要用身体书写才会来劲。
再也忍受不住相思之苦的于小庄,瞒着家人,趁着一个星期天,自己跑到天津一趟,到天津小站南那个山沟沟里去
会情人。赶上星期天,高积云就可以跟部队请一天假出来见见她。那天她是坐夜车去的,先坐火车到天津,然后又倒长
途汽车,直到中午才到达他们部队所在那个小镇。高积云早已等待在那个长途车站上。一见面,看见双方都瘦了,但眼
睛里都冒火,像是要把对方一口吃掉,或者一把烧干。正逢集市,在那条不大的人来人往的大街上,两人无奈,又急切,
不敢有任何身体接触,稍有亲呢,随时都有可能被当兵的战友出来碰上。他们只能一本正经、一前一后地在深秋的集市
上散步,走过来,走过去。于小庄脖子上那条砖红色的三角围巾,水红色的小碎花外罩,简直跳跃缭绕得高积云要流鼻
血。高积云尽管穿着便装,与她隔着一个身段的距离,于小庄还是闻到了他那湿漉漉的咻咻鼻息,和雄性动物发情时的
浓重体味。她知道,这体味只对她一个人有效,只因她而分泌,只分泌出来诱捕她的。她的眼睛,她的心,全在高积云
身上,眼睁睁看着,一会儿也舍不得离开。
满怀激动和不安,他们两人走啊走,直到把能见面的有效时间都走完。他带着于小庄进了一家小馆,每人要了一碗
爆肚,两个芝麻火烧填填肚子,但却谁也没有吃进去,只是相对无言,饭食都难以下咽。直到最后不得不走了,高积云
才恋恋不舍,送她上长途车站。她还要自己一个人坐火车返回沈阳去。分离是那样苦,那样难,但仍然留不下,还得分。
他们透过车窗那样定定地互相看着,盯着,直到车子开动。她木木的,一点知觉都没有了,好像身体的全部、心的全部,
全都留在他那里,留在那个天津小站南。
这次悄悄的天津之行,将他们的恋爱火苗子燎得冲天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