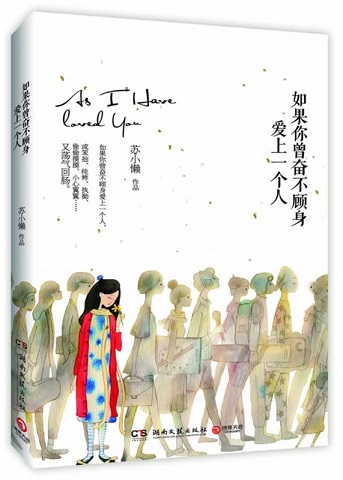如果可以这样爱-第20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那么不值一文?不,这决不可以,我不会被他模糊自己的意志,哪怕此刻被他捏死在手中,就像捏死一只蚂蚁,我也要保持清醒!
可是……我怎么了,我怎么两眼发黑,他还在说着什么我一句也听不清,只是本能地抗拒着在他手中滑坐在地上,像是一个垂死的病者被扔进了冰窖,没命地抽紧身体,就快要停止呼吸。
耿墨池大叫起来,拼命地摇着我的脑袋,拍我的脸,我意识模糊地看着他,觉得他那张脸竟比我梦中见到的还要缥缈而遥远……
我又昏过去了。
“对不起,都是我不好……”
这是醒来后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
我发现自己又躺在了床上,他坐在床边的一张椅子上,握着我的手,默默地看着我,表情分外孤独。他原来也这么孤独,深刻的孤独!我半睁着眼,有些怜惜地看着他,发现他居然有些苍老了,那么瘦……
唉,我在心里叹着气,他这个人啊,真是无可救药,固执得不可理喻,以为拿性命来跟我搏杀就能得到他期望的爱,就算是把两个人一起拖入坟墓他也全然不顾。也不知道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他忽然吻了我,坐在床边两只手箍紧了我的双肩,目光炯炯地盯着我的脸,我听见他说:“别再跟我斗了,妥协吧,我们都妥协,既然彼此都相爱,为什么一定要斗个你死我活的呢?”
//
…
NO。5他送我进精神病院(8)
…
我的意识很模糊,不是很理解他说的话,只感觉他眼中太阳一样的光芒徐徐进入我心中,好温暖啊,我任由着他,仿佛顷刻间就要融化般无力抵抗。
他进入我身体时的感觉很熟悉,跟我们的第一次一样,有种说不清的归属感,此时此刻,只要是一个归宿,哪怕是即刻让我躺进坟墓我也会在所不惜。我忽然理解了他的固执,原来他也跟我一样,焦虑了这么多年,就是等待着这样一个归宿!
“墨池,墨池……”
我含糊地叫着他的名字,任凭自己就这么融化,我居然很享受这种感觉,仿佛我们从未分开过,一切又回到了从前,还是那么的疯狂,他的声音,他的身体,他的气息,让我无法停止,只有他才能这么让我陶醉!
激情愈演愈烈,他喘息着,急不可耐,好像极力要找回什么似的,恨不得把我揉进他的生命,我静静地随着他,心里在想啊,即便这激情过后是一杯毒酒,我也会喝下去的,心甘情愿就这么死去,死在他的怀里……可是这么想着,我已经是气若游丝了,浑身像浸在沸水里煮一样的滚烫,这算是真的融化了吧。朦胧中他好像抱起了我的身体,焦急地说:“天哪,你这是怎么了,考儿,考儿,看着我呀……不行,你在发烧,我得赶紧把你送医院……”
我病了,从身体到心。
住了半个多月医院后,耿墨池把我接回家,请了两个人照顾我,一个是保姆,一个是从医院请来的小护士,白天他忙工作的时候,就是这两个人在公寓里陪着我呼吸。经过这场大病,我变得更加寡言少语,即使是跟耿墨池,我都没什么话讲。我还是不能原谅他!
其实这两年他过得并不轻松,表面是风光,但他从未在我这里赢得胜利,即使当初一脚踹开我,也没有表明他就是赢了,两年来我从未主动找过他或给过他只字片语就很让他的自尊心受挫。现在是多好的机会啊,他必须要彻底地控制我从而挽回曾经受挫的自尊,在他的概念里,我不能有自己的思想和见解,不能保持尖锐的个性,只要能拔掉我身上所有的刺,哪怕是我遍体麟伤血流不止他都在所不惜。他是不会容许自己失败的,尤其是在我身上!
这期间从长沙传来消息,我们录的那部广播剧大获成功,上海戏剧演艺中心已经开始在排练舞台剧了,预计年底就可以与观众见面。而冯客做完这一切后果然如他事先说的那样,从电台辞职了,现在在北京电影学院进修,为他的理想奋斗。出乎意料的是,老崔并没有强行挽留他,老崔给我打电话询问我的病情时说:“我早知道他想走了,以前很舍不得,但后来一想,他还年轻,我没有理由阻碍他的前程。”
“那麦子呢?”
“别提那死丫头,真没出息,算我白养她了,”老崔一提到他那叛逆的女儿就来气,“冯客走了不到半个月,她也跟着去了北京,也进了电影学院,说是学编剧,你说她的专业是金融,跟编剧八杆子都打不着,她学那玩意干什么!”
“这就是爱情的力量,你应该理解。”我由衷地说。老崔嘿嘿的笑,感叹道,“是啊,这丫头身上那股子劲跟我当年真是如出一辙。”
“要不她怎么是你女儿呢。”
我了解老崔,嘴上说得那么狠,其实内心很欣赏女儿,更欣赏拐走他女儿的冯客。我给冯客打电话,说起这事,他在电话里哈哈大笑,“有什么办法呢,你说,老崔的闺女这么大岁数都嫁不出去,他对我有恩啊,于情于理我都得帮他卸下这个包袱吧……”
这个臭小子,得了好还卖乖!
“我说考儿,你等着啊,等我在电影学院学有所成了,咱再好好合作一次,”冯客很是煽情地说,“所以你一定要好好保重身体,活得健健康康,快快乐乐,到时候咱不搞什么广播剧了,咱拍电影,你是编剧,我是导演……”
我没有说话,赶紧捂住话筒,生怕冯客在那边听到我的哽咽声。冯客他哪里知道,我现在哪还有什么健康可言,我的健康和信念全被一份无望的爱情吞噬绞碎,抑郁症卷土重来,失眠如恶魔般缠上我,厌食让我面容消瘦、精神萎靡,我常常几天不梳头,不敢梳,一梳就是大把大把的头发脱落……
//
…
NO。5他送我进精神病院(9)
…
而耿墨池对这一切毫无所知,他太忙了,每天早出晚归,只是偶尔抱怨:“你晚上怎么老是不睡啊,在阳台上晃来晃去的吓死人。”或者也会说,“怎么回事,家里怎么到处都是头发,你不知道叫保姆收拾干净?”
因为很少回家吃饭,他当然也不知道我每天的进食少得可怜,有时候甚至是几天不沾米。他连跟我吵架的时间都没有!
“别吵好不好,我会给你想要的一切,你想怎么着尽管跟我说,你都跟我吵了这么多年,现在不还是在我身边吗?”每次我想冲他发火的时候他总这么说。他的意思我懂,孙悟空本事再大也逃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我再怎么折腾肯定也逃不过他对我精神和情感的桎梏,除了接受,我别无选择。
我是可以接受,毕竟内心我是爱着他的,可是天知道他是个多么难相处的人,挑剔、苛刻、古怪、多疑……从前能容忍他,是因为我被爱迷失了方向,他的所有缺点我都看不到了,被淡化了,爱情让人盲目啊!可是经历了这么多事,我还敢谈什么爱情,什么“给你想要的一切”,我要的他永远给不了,而他要的我也没有!
他想要什么呢?
他想要自己的女人精致得体,最不喜欢女人乱糟糟的样子,我偏偏就是,头发像鸡窝,身上的衣服从没穿利索过,更别说穿上柜子里那些他给我买的名牌衣物;他喜欢女人坐有坐相站有站相,举止优雅谈吐含蓄,我偏偏是那种一站就要倒一坐就要靠的没型没款的女人,丢三落四,迷迷糊糊,一天到晚神经质……每次他都恨得牙根直痒,特别是那次带我出去应酬给他丢了脸后,他更是咆哮如雷,回来就大骂:“你白长了一张好脸蛋一副好身材,你看看你的样子,看看你的样子,像个从棺材里拖出来的千年女尸,你怎么就不能争口气……”
回头再看他自己的生活,真让我望尘莫及,早餐几点,煎蛋还是三明治,蛋要几分熟,火腿切成什么形状。午饭吃什么,下午茶又是几点,几点去健身房,做完健身要喝什么补充能量,洗澡水要调到什么温度等等都有十分苛刻的要求。最叹为观止的是换衣服,早上起床换下睡衣穿家居服,出去锻炼回来换正装,中午下班回来又换休闲服,午休时再换上睡衣,出去喝下午茶再换一套洋装,做健身又是另外专门的服装,做完健身去上班或是约见朋友又换一套,晚上去酒吧或去应酬也要换衣服,一天下来,他最少也得换七八套衣服。他的衣服在他身上停留超过十分钟就表示穿过了,必须干洗或熨烫,他的那个足有六十平米的巨大换衣间全是他的衣服。真是难为他的管家,衬衣必须和衬衣挂在一起,颜色也必须是由浅到深,领带、西服、鞋子等等,全都有各自的位置,一点儿也不能乱。这还不算,他睡过的床单和被套也必须每天更换,用过的毛巾也是,洗脸台和地毯上更不允许有一根头发丝,家具和音响必须纤尘不染,玻璃上不允许有一丁点的污印……跟这样一个奇怪的家伙生活在一起,我无论如何也轻松不起来,这哪是过日子!
所以无论他怎么指责我,我就是麻木不仁,死不悔改,他不会为我改变,我也不会迁就他,两个人的冷战常常让偌大的房子冷得结冰。后来他待在家里的时间更少了,除了睡觉,他几乎不再跟我正面接触,省得见了烦,我是死是活跟他不相干。我就是死在他面前,他也会以为我是发疯闹着玩的,他根本不知道长久的冷战已经让我的精神游离在崩溃的边缘。我真的快发疯了!
“你不理我可以,觉还是要陪我睡的,”可是他居然还这么跟我说,甚至还颇为不解地表示了自己的疑惑,“真是奇怪,我什么都可以换,就是换不了女人,除了你,我对别的女人怎么就没有激情呢?我还就喜欢你这鬼样子,难道这就是爱?”
亏他说得出口,他对我的爱?!
“算了,算了,你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只要我回来在床上找得到你就可以了。”那天他无奈地摆手说。
//
…
NO。5他送我进精神病院(10)
…
但是他还是感觉到了我异常的沉默,特别是一连几天没有说过一句话后,他开始意识到问题严重了,一种深层的恐惧在他英俊的脸上突现出来。“怎么了,考儿,”他的声音都开始发抖,“你别吓我,你没事吧?”
第二天,他就带了个人回来,姓聂,是个心理医生,在霞飞路开了家诊所。我见到那个人立即像见了魔鬼,因为那人一眼就看到了我的心底,他跟我作心理问答的时候,第一个问题就是:“你做噩梦的吗?”
我瞪着他,点点头,那锯子一样的目光顿时让我惊惧万分。多少年来,从没有谁问过这样的问题,小时候,母亲倒是为我晚上老做噩梦的事求过符,长大后她也就把这事给忘了,可是噩梦却总是在不经意的时候光顾我的梦境,甩都甩不掉。
“你知道你为什么做这样的梦吗?”聂医生在我道出梦境后问我。
“不知道。”
“只有一个原因。”
“什么?”
“你害怕,或者说你总在逃避着什么,可能这跟你曾经经历过的人和事有关,”聂医生眼睛死死盯着我,目光直穿入我的胸膛,“你一定被周围的人和事伤害过,所以你害怕跟周围的人接触,跟他们接触你会比单独待着更孤独,会觉得窒息,觉得无所适从,觉得恐惧,其实你心里很希望别人来关心你,接近你,但你的潜意识又在排斥这些……从心理学的角度上讲,你患有社交恐惧症,至于程度,还要观察一段时间……”
“我没病!”
“病人从来不说自己有病。”
“我不是病人,我没病!”
“你看,你的这种表现就是典型的心理障碍,”聂医生微笑着说,“你应该配合我,这样才能医好你的病……”
“我说了我没病!没病!”我跳起来,挥着手跺着脚,好像身上有千万只蚂蚁在爬一样,“你才有病,你们都有病……”
聂医生以一种同情的目光看看我,对旁边的耿墨池说:“耿先生,白小姐的情况很严重啊,你应该跟她多沟通,否则以她现在这种状态只有恶化的可能。”
耿墨池以沉默代替了回答,显然他相信了医生的话。
无论我如何地据理力争,他就是宁愿信医生的话也不信我的话,他那么聪明的一个人,我有没有病他居然看不出来,我承认我的精神状态是有些问题,但这就是病吗?如果这是病,那我岂不病了很多年,从祁树杰去世我就病了?或者更远,大学那场恋爱失败后我就病了?天哪,原来我一直是“病”着的!
我真是气疯了,整天在家里摔东砸西,我越这样他们越以为我有病,他们越以为我有病我越要证明给他们看我没有病。结果是恶性循环,当有一天我从厨房里摸刀要砍那个该死的护士时(是她建议耿墨池给我看心理医生的),我在他们的眼里已经是个货真价实的病人了,当天我就被送到了上海市郊的一家精神病院进行短期的治疗。
耿墨池亲自送我去的,当他给我办完入院手续送我进病房时,我眼睁睁地看着那扇铁门将我和他彻底地隔开了,他被隔在天上,我被堵在了地狱,我想我活不了了,连最爱的男人也把我当病人整,我不死也休想好好地活着,这么想着,心中的伤口又沽沽地涌出血来,眼中的泪水也止不住地流。
“不,别丢下我,求你别丢下我……”我抓住铁门拼尽全身的力气悲嚎着,半个身子都悬在了铁门上,唯恐一撒手,就要坠下万丈深渊。
“不要这样,考儿,我会经常来看你的……”
耿墨池再也没了先前的冷漠,呻吟着叫出声,隔着铁门,我看到了他的痛楚,同时也看到了他铁一样冰冷的决心。这就是我抗争的结果吗?难道我无畏的抵抗最后只能是被当做病人关在了这里?或者是我们的爱生不逢时,今生今世注定不能两情相依只能隔岸相望?为了守望这份爱,我把自己站成了岸,他也是!我们怎会如此不幸?早知如此,还不如让我病死在长沙,起码那是自己的故乡,身边有亲人陪着,我不想客死他乡成为游荡无所依靠的孤魂野鬼啊!
//
…
NO。5他送我进精神病院(11)
…
可是我只能泪眼朦胧地目送着他离开,一步步地消失在走廊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