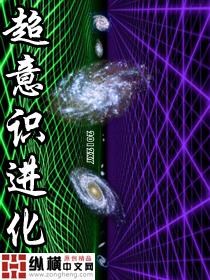常识与通识-第14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集)不够排第二和第三,那《乱世佳人》就是第一了。评选的结果一出来,美国的录相带店又铺天盖地地贴出《乱世佳人》的那张著名的接吻海报,我经过的时候看到,想,导演为什么还不喊“停”?幸亏电影没有味儿。
艺术没有味儿,于是艺术只好利用视觉和听觉引发情感。
我们需要再回忆点常识。上一期讲到“情感中枢的嗅脑那一部分,里面还有两个部分极为重要,一个命名为海马回,一个命名为杏仁核,都是因为它们的形状,而非其功能。
“……当负责思考的大脑皮层对刺激还没有形成决定的时候,杏仁核已经指挥了我们的行为。我们有很多悔之莫及的行为,就是因为杏仁核的反应先于大脑皮层的思考,不免失之草率。
“……这样,杏仁核抢先于大脑皮层的处理过程,激发出情绪反应与相应的行为反应方式,先斩了再说。……至于海马回,则是一个情境记忆库,用来进行信息的对比,例如,关着的狼与荒野中的狼,意义不一样。海马回管的是客观事实,杏仁核则负责情绪意义,同时也是掌管恐惧感的中枢。如果只留下海马回而切掉杏仁核,我们在荒野中遇到一只狼不会感到恐惧,只是明白它没有被关着而已。又如果有人用一把枪顶在你脑袋上,你会思考出这是一件危险的事,但就是无法感到恐惧,做不出恐惧的反应和表情,同时也不能辨认别人的恐惧表情,于是枪响了。这是不是很危险?”
“杏仁核主管情绪记忆与意义。切除了杏仁核,我们也就没有所谓的情绪了,会对人失去兴趣,甚至会不认识自己的母亲,所谓‘绝情’,也没有恐惧与愤怒,所谓‘绝义’,甚至不会情绪性地流泪。虽然对话能力并不会失去,但生命可以说已经失去意义。”
“……杏仁核储存情绪记忆,当新的刺激出现,它就将之比对过去的记忆,新的刺激里只要有一项要素与过去相仿佛便算符合,它就开始按照记忆了的情绪经验启动行为。例如我们讨厌过一个人,以后只要这个人出现,我们不必思考就讨厌他或她,勒杜克斯称此为‘认识前的情绪’。”
“……我们的童年时期,是杏仁核开始大量储存情绪记忆的时期,这也就是一个人的童年经验会影响一个人一生的原因。一个成人,在事件发生时,最先出现的情绪常常就是他的杏仁核里童年就储存下来的情绪模式。”
造型艺术里的“真”,所谓“写实”,就是要引起与海马回里的情境记忆的比对,再引起杏仁核里的情绪记忆的比对,之后引发情绪,这是—瞬间的事。
我们可以由此讨论一下八十年代后期举办的一些人体画的展出。据学院派的意见,人体画是艺术,不是色情。但同样是艺术,静物画展不会引起人潮涌动的效果吧?所以,前提是裸体是引起同类异性性冲动的形象记忆,引发的情绪就是色情,不少国家的法律只规定生殖器部位的裸露程度来判定色情与艺术的分界线。
使裸体成为艺术,是在于大脑部分的判断,而这是需要训练的,而训练,不是人人都可以得到的。即使是美术学院这样的训练单位,模特也是不许当众除衣的,而是先在屏幕后除衣,摆好姿势,再除去屏幕。除衣是情境记忆,它会引发色情的情绪。
裸体模特隐避除衣,是本世纪初从欧洲引进的。当学生有过一定的训练之后,模特的进入程序就不严格了,最后达到可以走动,和学生聊天。美术学院的学生一定还记得第一次人体课开始时的死寂气氛吧?还记得多少年后仍在讲述的笑话吧?怎么会当了教授之后就误会凡人百姓都受过训练呢?
凡人百姓的训练是生活中的见惯不怪。我姥姥家的冀中,女人结婚后日常天热可不着上衣,观者见惯不怪,常常是新调来的县上的干部吓了一跳。所以不妨视冀中人为裸体艺术家,将县上新干部视为参观裸体艺术展的观众。一般来说,愈是乡下,裸体艺术家愈多,愈是城里,训练反而愈少。
知青初去云南,口中常传递的是女人在河里当众洗澡,绘声绘色,添油加醋,情绪涌动。几年之后,知青们如十年的老狗,视之茫茫。
这就是同样的形象反复之后,海马回都懒得比对了,也就引不起杏仁核的情绪比对了,也就没情绪了。我怀疑如果给畜生穿上衣服,一万年之后,它们也会有关于色情与艺术的争论。
人体艺术,真实可贵在你还爱人体。通过画笔见到的人体,会滋生出包括性欲但比性欲更微妙的情感。这不是升华,是丰富,说升华是暴殄夭物。
音乐,我在《爱情与化学》里说过了,此不赘。
文学有点麻烦。麻烦在字是符号。识得符号是训练的结果,我们中国人应该记得小学识字之苦。训练意味着大脑在工作,所以人类的大脑里有一个专门的语言区。嗅叶,海马回,杏仁核都不会因符号而直接反应,它们的反应是语言区在接受训练时主动造成与它们的联系,联系久了,就条件反射了。例如先训练“红灯要停住”,之后见到红灯,就引起大脑的警觉,指挥停住。红灯这一图像符号经过反复训练,可以储存到海马回里归为危险情境,但当我们想事情的时候,还是会视而不见闯红灯。我小的时候常看到公共汽车司机座旁有个警告“行车时请勿与司机交谈”,就是这个道理。
上个月,我的车被人从后面撞了两次。一次是后面的驾驶人在打手机,一次是后面的驾驶人在骂她的孩子。我现在从后视镜里不但要看后面车的情况,还要看驾驶人的情况,我觉得他们的海马回随时会有问题。
所以当我们阅读的时候,所谓引起了兴趣,就是大脑判断符号时引起了我们训练过的反应,引起了情感。文学当中的写实,就是在模拟一个符号联结系统,这个联结系统可以刺激我们最原始的本能,由这些本能再构成一个虚拟情境,引发情绪。所谓“典型”,相对于海马回和杏仁核,就是它们储存过的记忆;相对于情感中枢,就是它储存过的关系整合,如此而已。 “典型人物”大约属于海马回,“典型性格”大约属于情感中枢。
而先锋文学,是破坏一个既成的符号联结系统,所以它引起的上述的一系列反应就都有些乱,这个乱,也可称之为“新”。对于这个新,有的人引起的情感反应是例如“恶心”,有的人引起的情感反应是“真过瘾”,这些都潜藏着一系列的生理本能反应和情感中枢的既成系统整合的比对的反应。巧妙的先锋,是只偏离既成系统一点合适的距离,偏离得太多了,反应就会是“看不懂”。《麦田守望者》是一个偏离合适的例子,所以振振有词的反感者最多;《尤利西斯》是一个偏离得较远的例子,所以得到敬而远之的待遇。不过两本书摆在书架上,海马回是同等对待它们的。
电影,则是直接刺激听觉和视觉,只要海马回和杏仁核有足够的记忆储存,情感中枢有足够的记忆,不需训练,就直接进入了。引起的情绪反应,我们只能说幸亏电影不刺激嗅觉,还算安全。实在说来,现代人的海马回里,杏仁核里,由电影得来的记忆储存得越来越多,所以才会有“那件事比电影还离奇”的感叹。
我建议研究美学的人修一下有关脑的知识,研究社会学和批评的人也修一下有关脑的知识,于事甚有补益。我不建议艺术创作的人修这方面的知识,因为无甚补益,只会疑神疑鬼,真实状态反而会被破坏了。写侦探小说的除外。
修艺术例如绘画学分的美国学生,你若问他你学到了什么,他会很严肃地说thinking,也就是思想。这是不是太暴殄天物呢?因为学别的也可以学到思想呀,为什么偏要从艺术里学思想?读《诗经》而明白“后妃之德”,吾深恶之,因为它就是thinking之一种。
IQ弄好了,可以导致思想,但仅有智商会将思想导致于思想化,化到索然无味,心地狭小,于是将思想视为权力,门面,资本。如此无趣的人我们看到不少了。
EQ也可以搞到不可收拾,但我还是看重情商。情商是调动、平衡我们所有与生俱来的一切,也许它们作为单项都不够优秀,但调和的结果应该是一加一大于二的状态。
身外之物,也许可以看淡,但身内之物不必看淡。佛家的禁欲,多是禁身内之物对身外之物的欲,办法是否定身内之物这个前题。少数人可以生前做到,多数人只能死后做到。这么难的事,实在是太难为一般人了。但一般人调和身内之物之间的平衡,则是自觉经验多一些就大体可以做到,不难的。平衡了,对外的索求,不是不要,而是有个度。有度的人多了,社会所需就大体有个数了,生产竞争的盲目性就缓解多了。盲目都是对于自身不了解。
这像不像痴人说梦?我觉得像,因为我们对自身的了解几乎还没有开始,无从开始情商的累积。我们大讲特讲智商的匮乏,将仅有的情商也作智商看待,麻烦事儿还在后头呢。
不过说到情商这一节,也就可以回答《爱情与化学》那一节的疑问了。假如爱情的早期性冲动在情感中枢中留下记忆,此记忆建立了情感中枢里的一个相应的既成系统,当化学作用消失了之后,这个系统还会主动运行的话(主动运行的意思是不受盲目的支配),原配的爱情就还有。否则,就是另外的爱情了。记住,爱情是双方的,任何一方都有可能败坏对方的记忆,而因为基因的程序设计,双方都面临基因利益的诱惑。
我们可以想想原配爱情是多高的情商结果,只有人才会向基因挑战,干这么累的活儿。
一九九八年七月 洛杉矶
《再见篇》常识写了有两年了,这是最后一篇。“最后”常常是个概念,概念有时会压迫人,例如,例如“世纪末”好了。度和量是人为规定的,时间可度量,所以世纪末是一种人为的规定,这个规定搞得不少人惶惶不可终日。
按说人们应该已经习惯年终与年初相接的那一刹那,但为什么还会对第一百个或第一千个同样的一刹那忧喜叠加?愈是临近人为的这一刻,愈是荒诞百出?相信未来的一年,会愈演愈烈。
这是人类在一种自己制造的度量面前,因为催眠与自我催眠而呈现的焦虑。没有办法,我们人类的脑有这样的功能,现在是这种功能的集体发作,但愿这种焦虑引起的不是集体的攻击,世纪之钟敲响之后,但愿焦虑缓解。两千多年前那个担忧天会塌下来的杞国人,显然有受迫害狂的倾向,当时的人做寓言来嘲笑,自有彼时“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的强悍之气。可是本世纪,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对人类某些价值观的怀疑,逐渐解构我们的一些盲目,也逐渐酿成我们的许多焦虑,而且,愈临近世纪末,由科学数据支持的焦虑愈强烈,例如,例如“环境保护”渐获共识。
刚过去不久的洪患,终于迫使中国朝良性焦虑迈进一步。水土保持,按理说是个常识,何需由上百亿的损失换得?交常识的学费何需要交到肉痛?荷兰近年决定退地还海,以荷兰这样一个与海争地的国家来说,向海退地有一点“卖国”的意思,但为了“买”生态环境,这个“国”是要卖的。美国赌城拉斯维加斯附近的胡佛水库也要拆坝了,以当地的沙漠环境来说,积蓄水再合理没有了,但为了生态环境,拆。美国是很早就明白水库对生态环境的改变效果,而且很早就不再兴建水库了。虽然可以提出一千条水库的正面证据。但是严密监测的结果是,小不忍则乱大谋,谋什么?谋更大更长远的生态环境,忍则是不再建和拆。
前不久我忽然被邀请讲一下我的小说《树王》,理由是其中涉及到砍伐森林导致生态失衡。于是找来十多年前发表的这篇东西,翻看之下,深为自己当年的焦虑吓了一跳,同时也为自己当年的粗陋脸红不已。九二年还是九三年的时候,意大利有制片人执意要将《树王》拍成电影,此事我在《威尼斯日记》记录过,结果是亚洲的朋友们认为这是发达国家的阴谋,他们通过糟蹋生态发达了,现在为了他们的利益,让不发达国家保持生态环境,“你的小说改编成电影,是他们用一个不发达国家的作品来说‘看,你们自己的人也说了嘛’。”我一向对这种政治交集表现得智力不够,于是婉言谢绝了制片人。现在看来,是坚持常识的能力不够。
今年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三十周年,看来看去,主题是放在人生得失上。但就我个人的经历,起码东北、内蒙古和云南,知青参与了破坏生态。当然,当年的知青的知识里,没有生态这一项,只有战天斗地,而且表现得近乎疯狂。只是由于这种疯狂,让我起了一些焦虑,觉得事情哪里有些不对头。我不讳言我是参与破坏者,也因此我倒有了说出我的焦虑的资格。三十年了,知青不年轻了,但是我一直没有找到承认自己是破坏者的知音。近年回去插队地点看看的知青们,意识到破坏的后果了吗?黑土地,北大荒,处女地,意思应该是原始生态,破坏它为什么成了“人生得到锻炼”这种只对一代人生效的欣慰呢?蒙古草原是世界上剩下的惟一一块原始草原,我们从世纪初一直挖到世纪末。红土地的亚热带原始森林,不是一刀一刀被我们砍掉,放把火烧得昏天黑地吗?黄土地,曾经是汉武帝与匈奴强力争夺的牧草场,谁占有它,等于现代的坦克有了汽油。卫青与霍去病,替汉王朝夺到了这项“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战略资源,可是两位将军,料得到今天的这般景象吗?
绝非大哉问,只是常识之问。
当然可以反诘我目前的情况就是如此,百姓要吃饭,社会要发展,这是发展的必然之径。但是,“竭泽而渔”的道理不难明白吧?我诘问当年的知青,也是不公平。还记得当年陈永贵视察云南,质问为何不大开梯田?还记得当年云南省革命委员会策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