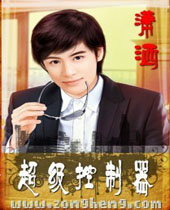永别了武器-第30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人兴奋。凯瑟琳对我笑笑,还和我谈话,我因为人很兴奋,话音有点口齿不清。卷发的铁钳发出悦耳的嗒嗒声,我可以从三面镜子里看到凯瑟琳,而我那小间又温暖又舒服。接着理发师把凯瑟琳的头发向上梳好,凯瑟琳照照镜子,修改了一下,在有些地方抽掉发针,有些地方插上发针;然后站起身来。“对不起,累你等得这么久。”
“先生很感兴趣。不是吗,先生?”女人笑着问。
“是的,”我回答。
我们出门走上街头。街上又寒冷又冷落,又刮起了风。“哦,亲爱的,我太爱你了,”我说。
“我们不是过着快活的日子吗?”凯瑟琳说。“喂,我们找个地方去喝啤酒,不要喝茶。这对小凯瑟琳很有好处。能叫她长得细小。”
“小凯瑟琳,”我说。“那个小浪荡鬼。”
“她一直很乖,”凯瑟琳说。“她简直没给你什么麻烦。医生说啤酒对我有益,同时能叫她长得细小。”“你这么叫她长得细小,倘若是个男孩的话,将来也许可以当骑师。”“我们果真要把这孩子生下来的话,总得结婚吧,”凯瑟琳说。我们坐在啤酒店角落里的桌子边。外边天在黑下来。其实时间还早,只是天本来阴暗,暮色又降临得早。
“我们现在就结婚去,”我说。
“不,”凯瑟琳说。“现在太窘了。我这样子太明显了。我这样子站在谁面前结婚都太难堪了。”
“我倒希望我们已经结了婚。”
“结了婚也许是好一点吧。但是我们什么时候可以结婚呢,亲爱的?”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一件事。在这像奶奶太太般的大腹便便的情况下,我不结婚。”
“你哪里像个奶奶太太。”
“哦,我像得很,亲爱的。理发师问我这是不是我的头胎。我撒谎说不是,我说我们已经有了两个男孩和两个女孩。”
“我们什么时候结婚呢?”
“等我身体瘦下来,随时都行。我们来个好好的婚礼,叫人人称赞你我是一对多么漂亮的少年夫妻。”
“你不忧愁吗?”
“亲爱的,我为什么要忧愁?我只有一次不好过,那是在米兰,我觉得自己像是个妓女,不过那难受也只有七八分钟,还都是因为旅馆房间内的陈设的关系。难道我不是你的好妻子吗?”
“你是个可爱的妻子。”
“那就不要太拘泥形式了,亲爱的。我一瘦下来就和你结婚。”“好的。”
“你想我应该再喝一杯啤酒吗?医生说我的臀部太窄,所以最好叫我们的小凯瑟琳长得细小。”
“他还说什么啊?”我担心起来。
“没什么。我的血压很奇妙,亲爱的。他非常称赞我的血压。”“关于你的臀部太窄,他说了什么?”
“没什么。什么都没说。他说我不可以滑雪。”
“很对。”
“他说我滑雪没学过的话。现在来学可太晚了。他说我可以滑雪,只要我不摔跤。”
“他真会开玩笑。”
“他人倒是挺好的。我们将来就请他接生吧。”
“你可曾问他我们该不该结婚?”
“没有。我告诉他我们已结婚四年了。你瞧,亲爱的,我要是嫁给你,我便成为美国人,所以我们随便什么时候根据美国法律结婚,孩子就是合法的。”
“你从哪儿打听出来的啊?”
“从图书馆里的一部纽约的《世界年鉴》上。”
“你真行。”
“我很喜欢做美国人,我们以后到美国去,好吗,亲爱的?我要去看看尼阿加拉瀑布②。”“你是个好姑娘。”
“还有一件东西我要看,但我一时想不起来了。”
“屠场③?”
“不是。我记不得了。”
“伍尔沃思大厦①?”“不是。”
“大峡谷②?”
“不是。不过这我也想看看。”
“那么是什么呢?”
“金门③!这就是我要看的。金门在哪儿?”“旧金山。”
“那我们就上那儿去吧。我本来就想观光旧金山的。”
“好。我们就上那儿去。”
“现在我们就回山上去。好吧?我们赶得上登山缆车吗?”
“五点过一点有一班车子。”
“我们就赶这一班车子。”
“好的。等我再喝一杯啤酒。”
我们出了酒店,走上街,爬上到车站去的台阶,天气异常寒冷,一股寒风从罗纳河河谷直刮下来。街上的店窗里点着灯,我们爬上陡峭的石阶到了上边一条街,又爬了一段石阶,才到车站。电气火车在那儿等着,车里的灯都开着。那里有个钟面,指明开车的时间。钟面上的长短针指着五点十分。我再看看车站里的时钟,五点零五分。我们上车时,我看见司机和卖票员正从车站酒店里出来。我们坐下了,打开窗子。火车上用电气设备取暖,很是气闷,不过窗子外有新鲜的冷空气送进来。
“你疲倦吗,凯特?”我问。
“不。我感觉良好。”
“路程并不远。”
“我喜欢乘这车子,”她说。“你不必替我操心,亲爱的。我感觉良好。”
雪到圣诞节前三天才落下来。有一天早晨,我们醒来才知道在下雪。房间里的炉子火光熊熊,我们呆在床上,看着外边在纷纷下雪。戈丁根太太端走了早餐的托盘,在炉子里添了些木柴。那是一场大风雪。她说雪是半夜左右开始下的。我走到窗边望出去,看不清楚路对面。风刮得呼呼响,雪花乱舞。我回到床上,我们躺下来交谈。
“我很希望能够滑雪,”凯瑟琳说。“不能滑雪真太糟了。”“我们找部连橇到路上走走去吧。那就像乘普通车子一般,没什么危险。”
“颠动得厉害吗?”
“我们等着瞧吧。”
“希望不要颠动得太厉害。”
“等一会儿我们到雪上溜溜去。”
② 瑞士高山,在蒙特勒南,高达10,690 英尺。
③ 苏黎世是瑞士北部主要工业城市。
① 尼阿加拉瀑布在纽约州西北端和加拿大接壤的尼阿加拉河上,是美国男女的蜜月胜地。
② 指芝加哥市的宰牛场。美国作家厄普顿·辛克莱曾根据这地方的内幕写成长篇小说《屠场》,于1906 年出版,轰动一时。
③ 纽约市的一家百货公司,当时是世界上最高的建筑物。
“中饭前去吧,”凯瑟琳说,“散步可以开开胃口。”
“我总是肚子饿。”
“我也是。”
我们到外面去踏雪,但是风刮着积雪,我们没能走多远。我在前头走,打开一条路来,一直走到车站就再也走不下去了。雪花乱舞,我们看不见前面的东西,只好走进车站旁边的一家小酒店,拿把刷帚,彼此扫去身上的雪,坐在一条长凳上喝味美思。
“这是场大风雪,”女招待说。
“是的。”
“今年雪下得很晚。”
“是的。”
“我可以吃条巧克力吗?”凯瑟琳问。“也许太近午饭时间了吧?我总是肚子饿。”
“吃一条好啦,”我说。
“我要吃一条有榛子的,”凯瑟琳说。
“是很好吃的,”女招待说。“我最喜欢吃这一种。”
“我再来杯味美思,”我说。
我们出了酒店往回走,方才用脚踩出来的那条小径现在又被雪遮没了。原来踩出的脚印只有微凹的痕迹了。雪扑打着我们的脸,我们几乎什么都看不见。我们掸掉身上的雪,进屋去吃中饭。戈丁根先生端上中饭。“明天可以滑雪,”他说。“你滑雪吗,亨利先生?”
“我不会。倒是想学学。”
“学起来很便当。我儿子回来过圣诞节,由他来教你吧。”“好极了。他什么时候来?”
“明天夜晚。”
饭后我们坐在小房间的炉子边,望着窗外的飞雪,凯瑟琳说,“亲爱的,你不想一个人到什么地方去跑一趟,跟男人们一起滑滑雪吗?”“不。我为什么要去?”
“我想你有时候,除了我以外,也会想见见其他人。”
“你可想见见其他人?”
“不想。”
“我也是。”
“我知道。但你是不同的。我因为怀着孩子,所以不做什么事也心安理得。我知道我现在十分笨拙,话又噜苏,你应当到外面溜达溜达去,才不至于讨厌我。”
“你要我走开吗?”
“不。我不要你走。”
“我本来就不想走。”
“上这儿来,”她说。“我要摸摸你头上那块肿块。这是个大肿块。”
她用手指在上边抚摸了一下。“亲爱的,你喜欢留胡子吗?”
“你要我留吗?”
“也许很有趣。我喜欢看看留起胡子来的你。”
“好的。我就留。现在就开始。这是个好主意。可以给我点事情做做。”
“你在愁着没事做吗?”
“不。我喜欢这种生活。这是一种很好的生活。你呢?”
“我觉得这生活太可爱了。我只是怕我现在肚子大了,也许会惹你厌烦。”
“哦,凯特。你就是不晓得我爱你爱得发疯了。”
“是爱着这样子的我吗?”
“就爱着这样子的你。我生活得很好。我们岂不是过着一种很好的生活吗?”
“我过得很好,不过就怕你有时想动动。”
“不。我有时也想知道前线和朋友们的消息,但是我不操心。我现在什么都不大想。”
“你想知道谁的消息呢?”
“雷那蒂,教士,还有好些我认得的人。但是我也不大想他们。我不愿想起战争。我和它没有关系了。”
“现在你在想什么?”
“没什么。”
“你正在想。告诉我。”
“我正在想,不晓得雷那蒂有没有得梅毒。”
“只是这件事吗?”
“是的。”
“他得了梅毒吗?”
“不晓得。”
“幸喜你没有得。你得过这一类的病没有?”
“我患过淋病。”
“我不喜欢听。很痛吗,亲爱的?”
“很痛。”
“我倒希望也得。”
“不,别胡说。”
“我讲真话。我希望像你一式一样。我希望你玩过的姐儿我都玩过,我就可以拿她们来笑话你。”
“这倒是一幅好看的图画。”
“你患淋病可不是一幅好看的图画。”
“我知道。你瞧现在在下雪了。”
“我宁愿看你。亲爱的,你为什么不把头发留起来?”
“怎么个留法?”
“留得稍为长一些。”
“现在已经够长了。”
“不,还要长一些,这样我可以把我的剪短,你我就一式一样了,只是一个黄头发一个黑头发。”
“我不让你剪短。”
“这一定有趣。长头发我已经厌烦了。夜里在床上时非常讨厌。”“我喜欢你的长头发。”
“短的你就不喜欢吗?”
“也许也喜欢。你现在这样子正好。”
“剪短也许很好。这样你我就一式一样了。哦,亲爱的,我这样的需要你,希望自己也就是你。”
“你就是我。我们是一个人。”
“我知道。夜里我们是的。”
“夜里真好。”
“我要我们的一切都混合为一体。我不要你走。我只是说说罢了。你要去,就去好了。不过要赶快回来。嘿,亲爱的,我一不和你在一起,就活得没有劲。”
“我永远不会走开的,”我说。“你不在的时候我就不行啦。我再也没有任何生活了。”
“我要你有生活。我要你有美好的生活。但是我们要一同过这生活,不是吗?”
“现在你要我不留胡子还是留胡子?”
“留。留起来。一定会叫人高兴的。也许新年时就留好了。”“你现在想下棋玩玩吗?”
“我宁愿玩玩你。”
“不。我们还是下棋吧。”
“下了棋我们再玩。”
“是的。”
“那么好吧。”
我把棋盘拿出来,摆好棋子。外边还在落着漫天大雪。
有一次我夜里醒来,知道凯瑟琳也醒了。月亮照在窗户上,窗玻璃上的框子在床上投下黑影。
“你醒了吗?亲爱的?”
“是的。你睡不着吗?”
“我刚刚醒来,想到我第一次见你时,人差不多疯了。你还记得吗?”
“当初你是稍微有一点疯。”
“我现在再也不是那样子了。我现在挺好。你说挺好说得真好听啊。说挺好。”
“挺好。”
“哦,你真可爱。而我现在已经不疯了。我只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快乐幸福。”
“睡去吧,”我说。
“好的。我们同时同刻睡去。”
“好的。”
但是我们并没有同时同刻睡去。我还醒了好久,东想西想,看着凯瑟琳,月光照在她脸上。后来我也睡着了。
到了正月中旬,我的胡子留成了,这时冬季气候已很稳定,天天是明亮寒冷的白昼和凛冽的寒夜。我们又可以在山道上行走了。路上的积雪被运草的雪橇、装柴的雪车和从山上拖运下来的木材压挤得又结实又光滑。山野四下全给白雪遮盖,几乎一直遮盖到了蒙特勒。湖对面的高山一片雪白,罗纳河河谷的平原也给雪罩住了。我们到山的另一边去长途散步,直走到阿利亚兹温泉。凯瑟琳穿上有铁钉的靴子,披着披肩,拄着一根尾端有尖尖的钢包头的拐杖。她披着披肩,肚子看上去并不大,不过我们并不走得太快,她一疲乏,就在路边木材堆上休息休息。
阿利亚兹温泉的树丛间有家小酒店,是樵夫们歇脚喝酒的地方,我们也去坐在里边,一边烤炉子一边喝热的红葡萄酒,酒里面放有香料和柠檬。他们管这种酒叫格鲁怀因,拿这酒来取暖和庆祝取乐,那是再好也没有了。酒店里很暗,烟雾弥漫,后来一出门,冷空气猛然钻入胸腔,鼻尖冻得发麻。我们回头一望,看见酒店窗口射出来的灯光和樵夫们的马匹,那些牲口正在外边蹬脚摆头,抵御寒冷。马的口鼻部的汗毛结了霜,它们呼出的空气变成了一缕缕白气。回家上山的道路先是平整而滑溜,冰雪给马匹践踏成为橙黄色,这样一直到拖运木材的路与山道相交的地方。然后走到了盖着干干净净的白雪的山道上,穿过一些树林。傍晚回家的途上,我们两次见到了狐狸。
山居的景致很好,我们每次出去,都是尽兴而归。
“你现在胡子长得相当好看了,”凯瑟琳说。“跟樵夫们一式一样。你看到那个戴着小小的金耳环的男子没有?”
“他是个打小羚羊的猎人,”我说。“他们戴耳环,据说可以听得清楚一点。”
“真的?我不相信。依我看,戴耳环的目的只在于要人家知道他们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