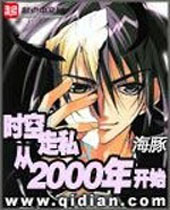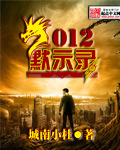2005年第22期-第6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成为 悲伤或欢乐的 短暂或隐秘的
一个人的全部记忆和遗忘
泥土的记忆不等于书写在纸上的历史
却等于并且越过每个人的一生
龙山所:一座童年的城
一座城,记录石头,泥土和雨水的光荣
泥土是曾被石头遮蔽的肉体
石头是支撑泥土的灵魂
而雨水是历经击打与磨损的石头
和泥土的交融或呼吸
移动:一束镜子的光爱上了坐在九岁的门槛和形象
在老宅的内墙上
把童年的快乐或孤单推向深渊
空空的城
石头早已被发掘,敲裂或抬走
泥土从雨水的间歇里开始走出自身的重量和阴暗
被岁月挖走了堞,壕沟和历史的外件
只留下一个曾寄养于农家的孩子
被围在城外的童年
只留下雨水通过檐与水缸的自言自语
只留下空空的正方形的泥土
十指抓住时
黏糊糊的 冰冷抑或温热的触觉
石头的城
变成了泥土的王国:
潮声连同马蹄和金属的撞击
继续被泥土填塞
锈蚀的刀戈,裂缝的器皿与无名骸骨的纠纷
继续被虚无瘗埋
在夕阳,炊烟或鸡狗的扑腾中
寂寞长出比烽火更高
比童年的记忆更深的青草:
拆散的石头变成了住户的墙脚
墙脚变成了门前的石凳
石凳变成了被拖拉机和岁月碾过的路基
裸露的泥土又开始悸动
疯长的青草和雨滴占据石缝或遗址的正方形
空空。开裂的板壁上粉笔写下的句子
15瓦摇晃的灯和台风中倾斜的电线杆
空空。只是一个人童年的城和九岁没有回音的叫喊
在镜子纵深的记忆里
向小巷的东南方 眺望
三北大街:人与物的记忆
汹涌的人流与物流
在高楼大厦的空隙 各种递升或膨胀的混凝土与金属的意志之间
倾泄而出
拆迁之前 草根 残留砖缝里的记忆:一个悠长的片断还没有被浮华之芒触及:
多年前这里是鸡鹅争鸣的家禽小集市羽毛乱飞的青石板。窄巷。壁藤。
已绝无仅有的几位老人还记得碗飞蛋碎的一天是一队武装的日本人闯入曾杀死7个农民
再多年前这里是石彻的城垛 抗倭的遗址 泥筑的海塘 塘南有灌溉稻棉的
河,河面上掠过5只燕子,河边的两个拉纤者绕过3头嚼草的水牛哞哞地叫着的寂静
再多年前这里是白花花的碱地 墩上疯长的咸蓬草 一群军丁和盐户正在为抢田界而打架
再多年前这里是冲毁的堤口 如盐税的苛征暴敛 成为流离失舍的百姓四处逃命的背景
再多年前这里是原始的海水 挟裹着还没有串网与樯桅扎根的浑浊的潜流汇入尚未命名的喇叭型湾口
欲望的引擎推动着新生的城市各个部件能量的释放,转换与交汇
从鱼类般穿梭的各式车辆中牵引出个体的记忆:
但坐在这辆红色“宝马”后座的中年男士不会知道
他的记忆是一篮土豆般干瘪的饥饿岁月店铺门口张贴大字报时的另一种嘈杂
从一个执泥刀的农民成为一家电子企业老板的传奇履历
随他开门而出的这位穿着时髦的美貌女郎不会知道
她的记忆是山区老家的闭塞与贫穷 租赁和打烊前 几个临时的化名或昵称婚前与3个恋人的罗曼史 几天前麻将桌上的输赢与插曲
从她身后拿着塑料枪冲上来的顽皮小男孩更不会知道
他的记忆是在这里度过的童年弄堂的简陋与弯曲 姥姥家被油气熏黑的门牌 姑与叔的溺爱以及矮脚小狗的欢叫
立体几何虚拟的形象与力量
失去的存在 在时间的目光里重获形体:
所有意识相互之间的隔绝与各自过程的淡忘
就像大潮退去之后 这片滩涂 淤泥之上覆盖的淤泥 黑暗内部囤积的黑暗
最后全部被锁入钢骨水泥与喧嚣的基石之下黑黝黝的土地 那座因孤独而得以永存的记忆数据库
抽象的复数淹没了具体的单数
但是 是谁听到了
记忆深处
另一个孩子
在时沉时浮的岛屿上
绝望的叫喊?
朱家桥:友人旧宅
蓦然回首,在搬迁的间隙
驻足片刻
登门拜访的情景
如同平常的泥土
透出釉的光泽:
一手持壶,一手摇篮,对饮畅谈
记忆,随着衍生的藤蔓植物,伸着茎,吐出叶
一绺绺一溜溜地
弥补了墙的裂缝 雨雪的痕迹
几乎爬上了白铁皮遮漏的屋顶
襁褓中的儿子早已在远方的城市长大成人
逝去的日子
把艰辛和淡然牵到了阳光的高度之上
小窗 向南敞开
显得有些陈旧和简陋但被新绿簇拥
一个健壮的少妇弯腰
晾晒被婴儿尿湿的床单
这沉溺其中的姿态似曾相识
还有一个房东和租户都不知道的秘密
在日益老去的场地
夯下了青春的纪念:
拐弯处 锈蚀的桥栏依偎着往昔的身影
变得轻盈,锃亮
远方,升起的桅指向充满清晨的工地和海湾
在五磊寺
太阳升起,没有谁去关注:
阶前的雾霭一滴滴的退尽
萦绕在古松、塔影和石径间的天籁
叶落纷纷,消失,如同弘一大师驻锡时书写的卷帙
出家前的风流逸闻
比诵唱的经文易于世俗的流传
远去的钟声 留下了一路青青的芋叶
在承受了时间里太多的辎重,兵燹
和荒芜之后
溪边的石头已把空寂交还给空寂
一簇新绿
悄悄从四季的根部
爬上后院的墙角
千年不涸的
是一潭洗涤青菜,萝卜和心事的清水
滋养着壑前随朝暮沸腾起伏的鸟声,岚光
一个小和尚还俗前
挑着担在半途,驻足,抬头
向山外或一朵云探望时眯起双眼
俞强印象
■ 柯 平
去年四月我在宁波,《诗刊》社策划的大型文化公益活动“春天送你一首诗”在当地搞得热火朝天。到处是摄像机和闪光灯,城市上空飘满各色气球和题有诗句的彩带。连幼儿园的孩子与拄杖的古稀老人也尝试以诗歌交谈。那种令人迷醉的节奏和气氛,仿佛是这座城市的自来水管里哗哗流淌出来的,也已经不再是经过净化的甬江的春水,而是通感与想象力了。但有一个人始终站在春天之外,温厚、孤寂、寡言少语。包括当天晚上在房间里的闲话,那么轻松、炽热的氛围中,就因为缺少他那夹杂着浓重慈溪土话的声音加入,显得多少有点儿遗憾。临走前他笑了笑站起来,做了一个无声而温馨的动作——把一册灰色封皮的诗集放在我的枕下。
这对当晚的睡眠显然不是什么好事。客人散后我开始阅读,从最初的漫不经心,到后来的身心投入。这本题为《大地之舷》的集子收集了他十年艺术生活的精粹部分,这位世俗与矫情的失语者在诗中突然显得雄辩而滔滔不绝,就像罗伯特·勃莱所形容的“哑巴开始说话”一样让人吃惊。车站、古镇、一个用三种姿势跑来的女孩、烟雨里的城市一角、赛马会、窑工、月光下的墓地、小情人与断电之夜的一次秉烛夜读,这些原来只不过属于他日常生活一部分的普通场景,此刻在语言和灵感的投影下却似真似幻,呈现出一种朴素而别致的魅力。他像一个精神世界的代言人面对现实大声说话。任何不熟悉他的读者和同行,只要听到他乡音深情吟唱的像“生活是粗糙的/像地里刚挖出的马铃薯”或“一个跛腿的少女/正在追赶梦中飞驰的车厢”这样质朴的诗句,相信都不会再对他的才华和出色的语言技巧有所怀疑。
我回忆起生平与他为数不多的几次接触。一九九○年初秋在慈溪,那次虽说是去讲课,客观上只不过是为我们的有幸结识提供后个不用自掏腰包的机会。在县城的小酒馆里初次见面,读着从口袋里小心掏出的、尚带着几分体温与烟味的手稿,我很快被他纯情的、自言自语的声音吸引。还有一次是在什么会上,同样的沉默寡语。那时他已离开原先的棉纱厂去报社工作了,诗名在省内外也早已传播开来。评论家沈泽宜先生曾猜想他体内是否藏有一座动物园,“单纯中寄寓着深厚,细微处回应着主题”,并认为他“已是一位全国性的评说对象。幽居江北小城的诗人庞培在写给他的信里无法掩饰内心的激动,并为诗中“真正和中国南方土地相称的晴朗大气”而心存感激。当我试探性地向他提起这些,如想象中一样,他显得略有些不安,并很快用别的话题扯了开去。也许,对于这个谦卑而低调的年轻人来说,朋友和前辈诗人的喝彩只是类似田径场上掌声那样的激励声响,而他要做的事情是如何让自己跑得更快更远。
也有人向我提及他诗中对现实生活的缺席,这些年来,他似乎更喜欢采用跟自身进行精神对话的方式子同时也只对自己心灵能够包容和烛照的事物感兴趣。但从这本诗集以及稍后发表的《行为艺术或声音》《敦煌》《城市和五只鸟》等近作的倾向来看,一种更开阔的视野看来已经水到渠成。何况这本身并不能说明什么,怎么写永远是最重要的,而写什么?说到底只是—个个大习惯问题。聂鲁达可以为一枝枯萎的玫瑰献上二十首情歌和一首绝望的歌,但同样也可以在马楚比楚高峰上热爱自己的祖国。我想,如果他愿意用写《我想一个人听听夜晚的声音》那样的精致深情笔调来写一写长城或大雁塔,说不定还能让杨炼江河们相形见绌呢?
今年四月依然在宁波,依然是春天与诗歌的短暂狂欢,但他没有来。电话一头的声音略显喑哑,说自己一连几个通宵整理诗稿,说即将要动身去北方参加一个笔会,说希望我能为他的新诗集说点什么。这当然是一个让人无法拒绝的要求,无论是作为读者还是朋友。因为我深知这个人的生活中,艺术、谦逊和友情是他的全部家当,即使他的手中穷得只剩下一行诗歌,也会用它当作拐杖,以支持自己的身躯在现实中的艰难行走。“我在暮色中辨认远方的屋顶和灯火”,他说。而我们,我想,我们只是伫立路边,等他走过时为他鼓掌,向他投以充满敬意的一瞥的那一群人。
马克.斯特兰德诗歌十首
■ 许 枫译
马克·斯特兰德(Mark Strand),诗人、散文家、艺术评论家。1934年生于加拿大的爱德华王子岛,但其成长与受教育主要在美国与南美。年轻时辗转多所大学学习文学与艺术(曾在耶鲁大学学习绘画,获美术学士学位),自衣阿华大学读完文学硕士后,在美国及巴西多所大学讲学至今。
他著有10本诗集,其中包括获普利策奖的《一个人的暴风雪》(1998)、《黑暗的海港》(1993)、《绵绵不绝的生命》(1990)、《诗选》(1980)、《我们生活的故事》(1973)、以及《移动的理由》(1968)等。他还出版了两本散文集,若干译作,几部关于当代艺术的论著,还有3本写给孩子的书。另外,他还编选了多卷诗文集。自《移动的理由》广受好评后,斯特兰德的创作获奖频频,1990年当选为第二任美国桂冠诗人。
虽然他也曾致力于小说创作,但主要还是以诗闻名。对斯特兰德的诗歌构成影响的诗人很多,其中包括华莱士·史蒂文生、博尔赫斯等。他的诗歌冷静明朗,又不乏深度和对语言的穿透力,许多作品富有超现实特点,一方面致力于对梦境的仿造,另一方面又热衷于将日常的图景引入。如同置于虚实之间的多棱镜,其诗歌透明而复杂。
残 留
我清空挤满别人名字的自我。我清空我的口袋。
我清空我的鞋子,把它们丢在路边。
到了夜晚我倒拨时钟。
我打开家庭相册,像个男孩似的看着自己。
那有什么好?“钟点”做完了它们的工作。
我念叨我自己的名字。我说再见。
词与词相互跟从着随风而去。
我爱我的妻子,却又将她送走。
我的父母从他们的王座中升起
进入云朵的幢幢“奶屋”。我怎么能歌唱?
时间告诉我,我是什么。我改变了而我还
是同一个。
我清空生话中的自我,而我的生活残留着。
房 间
这是个老故事,有时候
它发生在冬天,有时候不。
听故事的人倒头睡了,
通往他那烦忧之室的门开了。
不幸走进了他的房间——
清晨的死亡,黄昏的死亡,
它们的木翅膀殴打着空气,
它们的阴影,那世界哀泣的流溢的牛奶。
为那令人惊异的结局有一样必需;
一片绿野,那儿母牛晒得像新闻纸,
那儿农夫坐下来凝望,
那儿空空如也,当它发生时,绝对不会太恐怖。
光的到来
纵然这一切姗姗来迟:
爱的到来,光的到来。
你醒了,蜡烛也仿佛不点自明,
星星集聚,美梦涌入你的枕头,
升起一束束温馨的花香。
纵然迟到,周身的骨头照样光彩熠熠,
而明日的尘埃闪耀着进入呼吸。
邮 差
那是午夜。
他从人行道上走来,
敲响了门。
我冲过去欢迎他。
他站在那儿哭泣,
向我挥动一封信。
他告诉我那里面装着
私人的坏消息。
他屈膝跪了下来。
“原谅我!原谅我!”他恳求道。
我请他进屋。
他擦着泪眼。
他那暗蓝制服
像块墨水污渍
在我深红的睡椅上。
无助,不安,渺小,
他蜷起身子像个球
睡着了,与此同时
我以同样的笔触
为自己编织更多的书信:
“你要活下去
靠着制造痛苦。
你要�